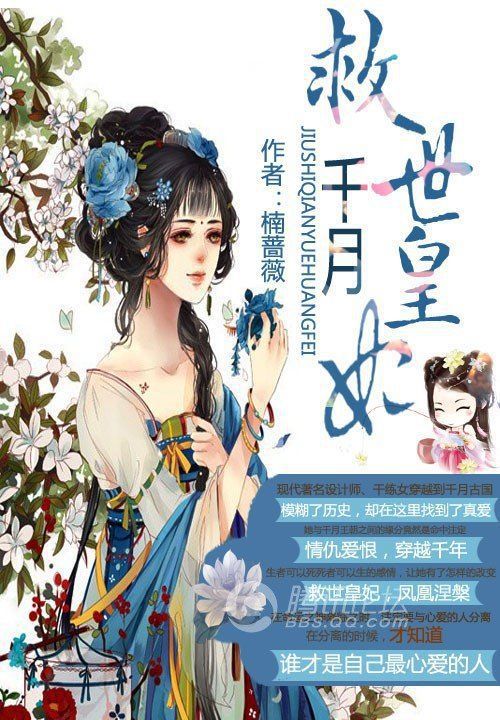时间是早上三四点,牛奋回到了陶正平租住的房子,没想到陶正平到现在都还没有睡,一直在担心他的安危。陶正平见牛奋现在才回来,本来是有些生气的,可是看到牛奋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样子,都一晚上了脸上还有个没有消肿的巴掌印,可见牛奋当时的多么的凄惨。他赶紧找来消炎药水和伤药,用棉签给他涂抹药水。
“那帮人也太不是东西了,居然把你打成这样,恶有恶报,那些人迟早会招报应的!”陶正平愤愤不平的说。
处理好了伤后,确定牛奋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他捏拳在牛奋肩膀捶了一拳抱怨道:“你小子一晚上跑哪儿去了?我在外面等你这混蛋等了半个多小时都不见你,我还以为你被那些人给乱刀砍死了呢,后来我回酒吧找你,才听佳佳说你跟着俩妹子早就离开了。老实交代,是不是跟妹子玩耍去了?做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龌龊事!?”
牛奋神情不自然的说:“小弟我纯洁的就像是一朵小花,胖哥你想多了。”
“我信你个鬼,你这家伙坏得很。”陶正平眼睛也太毒了,他抓住牛奋的领子往下拉,露出他脖颈胸口上大片的吻痕,他不依不饶的质问道:“那你说这是什么?该不会也是被打的吧?”
“这个,那个,”牛奋无言以对。
“你个重色轻友的混蛋,哼!亏我还把你当兄弟,把妹也不叫上哥哥我,亏我等了你两三个小时。我告诉你,咱俩友尽了。”陶正平义愤填膺,酸溜溜的说完继续做早饭去了。
刚还说只等了半个小时,怎么转眼又成了两三个小时了?胖哥,你能再善变点不!牛奋远远的冲他竖起了中指,其实心里已经感动的一塌糊涂。
牛奋身上有些许小伤,今天也就不去影视城墙根脚下蹲着了,补了四五个小时的觉,起床洗漱过后,他决定还是去萧碧池两姐妹家去看看,就怕发生意外。
牛奋边走便摆弄着手机,想着发条短信问问萧碧莲的情况。走着走着,牛奋突然往路边的小巷子里躲。
“是昨天那帮人。”
牛奋探头往外看去,看到十几个人正或蹲或站的等在路边,为首的就是金哥。
牛奋现在可不怕他们,是那些人该怕牛奋才对。可牛奋为什么要躲呢,原因是他居然在人群中看到了朱波。
朱波唯唯诺诺的蹲在金哥身边说着什么,金哥抽出香烟叼在嘴上,朱波立马识趣的掏出火机恭敬的帮他点火。
这时路边停下了一辆金杯面包车,金哥拉着朱波坐进了副驾驶室,其他众人也纷纷钻进了车里。十几个人全都挤上了车后,车子朝城南的方向疾驰而去。
牛奋感觉大事不好,朱波一定是领着金哥这帮人去秦兰家要债去了。
不行,一定要阻止他们,不然秦兰的爷爷又会跟上辈子一样被打的进重症病房的。秦兰也一定会重蹈覆辙冒险去望月庄园的,不行,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再次发生。
来不及多想,牛奋在路边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师傅往依山县而去。
坐在车里,牛奋才有时间考虑这件事该怎么解决。犹豫了好一会,最终还是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他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的号码。
不大一会儿,电话被接通,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传来。
“喂!你好。”
牛奋之前一直按耐着不让自己打这个电话,他希望再跟她见面的时候,能够亲自从她那里要到电话号码,还得是她自己自愿的。可是现在情况紧急,牛奋的这种情怀也就不再坚持了。
听到这久违的声音,牛奋的心莫名的轻轻颤抖。深吸了口气,再缓缓吐出,调整好心情,“你好,是秦兰吗?”
“是我,你是?”电话里传来秦兰疑惑的话语。
“我是牛奋。”
“牛奋?我不认识你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这边还有工作要忙。”
牛奋听出了她话里拒人千里之外的意思,于是也顾不上跟她拉家常了,直奔主题说:“我刚刚看到朱波带着一群二流子去找你爷爷去了,你赶快回去看看吧,我看那
帮人不像是好人,要是动起手来的话咱爷爷就危险了。”
牛奋觉得只要她回去了的话,以她的身手,金哥那帮人再要动手的话,应该是自讨苦吃才对。
“朱波,你是说朱叔叔?他带人去我家了?”
“对,你赶紧回去,晚了就来不及了。”牛奋焦急的说。
“好。”秦兰说完果断挂断。
牛奋坐在出租车里也是急得不行,几次开口催促司机师傅开快点。
一个小时后,到了依山县。然后牛奋凭着记忆给司机指路,弯弯绕绕的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转了大半个小时。
转过一个山坳,就看见一辆金杯面包车停在了那里。大路已经到了尽头,想来金哥他们已经弃车步行爬山了。
牛奋付了车资下了车,出租车掉头走了,牛奋沿着陡峭的山路往山上爬去。
这条路牛奋依稀还记得,当初小舅子秦峰就是带着他走的这条出来的。
竹林下,土胚屋前,秦贤武正和朱波带来的一帮人对峙着。
秦贤武悲愤喊道:“朱波,你还想怎么样!?我儿子已经进班房了。我们家已经家徒四壁了,真的暂时拿不出钱了。但凡是有了点钱,我还不都是立马就让我孙女给你送过去了吗。你带这些人来逼债也是没有用的。我现在真的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老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没钱你可以去卖血卖肝卖/肾卖/眼角/膜啊,正好我有这方面的门路。我还听说你孙女长得不赖,你可以让她去卖嘛,保准来钱快得很。”金哥嘴上叼着烟,皮笑肉不笑的说道。
“你!”秦贤武怒极攻心,他捂着胸口对金哥怒目而视,然后转头看向朱波说:“朱波,你非要逼死我你才甘心吗!”
“你儿子害得我家破人亡,至今我那老婆还躺床上半死不活,我找谁说理去!我只不过讨要我应得的,我这样做有错吗!啊!我问你有错吗!”朱波想到自己的境遇,还有老婆女儿这一年多来所受的苦难,情绪不由得有些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