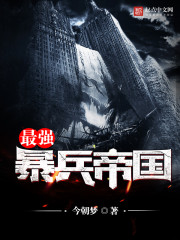事情没有什么进展,我也放下了,该吃吃,该睡睡。和蒋鸣也少了联系。这样过了半年,也就是06年夏天刚开始,知了在树上拼命的叫着。
对着风扇在吹的我,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是个陌生号码。短信说,他被炒了,补结了半年的工资,然后去了深圳,后面署名是蒋鸣。
原来这家伙换了号码啊?他就这样放下了吗?我看着短信,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复。老爸在旁边看我对着手机发呆,叹了口气,说爷爷有东西给你。
我回头看着老爸,爷爷去世二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东西给我。然后爸进了房间,从床底拉出一个满是灰尘的纸箱,从里面拿出一个黑色的小木箱,周围用铜皮包着角。
看到这做工精美的小木箱,我有那么一点怦然心动,那个心动就像看到初恋一样。
我心想这不会藏着什么武功秘籍吧?降龙十八掌?葵花宝典?还是如来神掌?随便一样让我来学,学会了都能天下无敌了,哈哈。
想到这里我内心一阵狂跳。而老爸好像是有意的样子,拿出木箱子,对着我往箱子面吹了一口气。灰尘把我呛得直咳嗽。老爸见了就哈哈大笑起来。
很多年没有看到老爸这么开怀大笑了。这些年他为了生活而奔波,皱纹早早就爬上了他的脸。整天蹬三轮车风吹日晒,五十多岁的人就像一个小老头,古铜色的皮肤看着就显老。
这些年难得老爸会开这样的玩笑,我当然得配合一下。他把木箱子交给我,就出门蹬三轮车了。
望着他有点驼背的身影,还有我住院那几个月,他内心的沉重从他那一声叹息就能感觉出来。泪水不由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了下来。
擦掉眼泪,我打开箱子,里面并没有什么武功秘籍。都是一些印章啊,残破的相书啊,还有用毛笔写的十几封信以及一些杂物。
我逐一的翻看着,这是爷爷的东西。很多都是解放前的繁体字,格式都是竖着写的,最底下有一本薄薄的族谱。
翻看完这些东西,还有那个带着香气的黑檀木箱子,我终于对自己的家世有了那么一点了解。
原来爷爷并非粤西这个小县城的人。而是广西人,是在一个叫做东兴的县城,刚好和越南相接。
而爷爷有两个哥哥,大哥叫做陈济华,二哥陈济棠,爷爷自己叫做陈济富。这个大爷爷陈济华又叫做陈维周,是个星相学家,从小下肢残疾。
二爷爷陈济棠就不得了了,是民国时期的广东“南天王”,很多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人。而我的爷爷就是个技术工人,不过一直都和两个哥哥有联系,建国之后才逐渐断了联系。
原来这样啊,我摸着下巴想了想。爷爷是个民国的技术工人,所以老爸是轴承厂的工人,而我是钢铁厂的工人,这样看来,我家三代都是工人啊。
信上有地址,建国前后的,东兴那边还有很多亲人。就是那些破书看不懂,虽然我高中毕业,但是也是偏理科,这样的东西又不是武功秘籍。我翻了一下那些书,看不懂就放下了。
老爸说是爷爷给我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有什么帮助?对了,大爷爷是星相学家,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风水先生。而我遭遇的这些事本身就玄乎,算是专业对口了,可是书我看不懂啊。
二爷爷嘛,建国后不久就去世了。不过生了一大堆的儿子,现在都在海外,可是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啊。
我在客厅走来走去,不知道这层关系对我来说有什么用。求助大爷爷那边的亲戚?这个容易点,怎么说我也是陈家的人,骨肉相连嘛。
可是那个白影子又不是伤害我,虽然我也是这次事故的受害者,不过现在不是没事吗。找二爷爷的儿子?十多个都在海外呢,我护照都没有,怎么出去啊?
外面知了不停的叫,风扇好像电力不足一样,慢悠悠的转。对了,不是还有蒋鸣吗?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他不是脑筋活络吗,找他,让他帮我想。
我兴奋的掏出手机,马上就回了信息给他,说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他,问他详细的地址。然后找出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把檀木箱子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倒了进去。
出门找到树荫下带孩子的妈,说我去一趟深圳,找一个朋友。就坐摩的去了车站。上午十点还有一趟车,去的福田,刚好赶上。这福田车站离蒋鸣工作的那个酒店不远。
下午四点下了车,我打的去了那个酒店,叫做花园酒店。这酒店门口很富丽堂皇,中式的结构,虽然只有一层,但是占了十几亩的地皮。
大厅边上有很多回廊,还有小桥流水通向各个包房,小水池养着很多金鱼乌龟什么的。几个小孩在掰着面包喂金鱼,保安过来赶,不让喂。
现在快五点,还不到饭点,所以大厅里只有几桌客人。我找门口前台的领班问了一下:“你好,我找蒋鸣,他是你们这里后勤的电工。”
漂亮的领班穿着灰色的职业装,涂着猩红的口红,拿着一个对讲机,旁边还站着两个穿红旗袍的迎宾。
领班很惊讶的说:“他啊?应该在呢!他在后面停车场旁边的电工班!你顺着这个走廊一直走,出了门就能看到了。”
领班喜滋滋的样子,好像跟蒋鸣很熟。然后就听到她拿着对讲机叫话:“电工班的阿鸣在吗?有人找!”
对讲机响起了蒋鸣的声音;“敏姐姐啊?谁找我啊?不是富婆的话,就说我不在啊!
”呃.......。这个蒋鸣,我无语。听着领班用对讲机和蒋鸣逗着笑,我走向了长廊。
长廊尽头右边是厨房,有人在抬着整筐的蔬菜进出,还听到砧板工在噔噔噔噔的切菜。
走出长廊的大门,停车场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太阳真大。走廊里面和外面,真是冰火两重天哪。
停车场对面有一排房子,有一个小门顶上的牌子写着“电工班”字样。我越过停车场走了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三台大牛角扇,在使劲的吹着。然后闻到很浓的烟草味,非常的呛人。
从大太阳下走进没有开灯的房子,还没有适应,所以只看到中间桌子上一对鞋底在晃。
我眯了一会眼睛,就看到抛过来一根烟。接住之后,才看清楚是蒋鸣坐在椅子上,双腿在桌面上乱晃。真悠闲啊!
蒋鸣笑眯眯的说:“大恒来了啊?这还没有到饭点呢!我六点下班,你坐那边,等我一下。”
我回头看到一张烂椅子,靠背都没有了,只剩下两个柱子。坐下之后,蒋鸣扔过来一个打火机,我把烟给点着。吸了几口之后,环顾四周,这真他妈的乱,也不怕老板看到。估计老板也不会来这种地方吧。
地上凌乱的扔着各种电线还有工具。满地的烟头,墙上还贴着“库房重地,严禁吸烟”的牌子呢。
蒋鸣前面的八宝粥罐子早就装满了烟头,也没有倒,那烟屁股没有灭,大股的青烟被风扇吹得是浓烟滚滚。有趣的是,三台牛角扇三个方向对着他吹。
活了二十三年,还真没有见过这样吹风扇的。而蒋鸣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在这里的地位。
偶尔进来的那些工友,也是向他请示的多,然后拿上线材又出去了。而蒋鸣的那双脚就没有放下来过。
这是升主管啦?他不是来深圳才半年吗?别人不知道的以为老板是他亲戚呢。
一根烟抽完,蒋鸣终于把脚放下了。伸了个懒腰,把对讲机放上衣口袋里。伸手抓了个万用表,两条线随便缠几下,又找了个电工包挂在肩膀。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着的烟说:
“走,大恒,本大王带你去巡山!”
巡山?我不明所以,跟着他出去,越过停车场走向那个长廊大门。看到两个地哩在抬着一筐盘子从厨房出来,蒋鸣摸了一下人家小姑娘的屁股说:“哎呀,小慧啊,昨晚我约你,你怎么关机了?”
小姑娘单手抬着塑料筐,回手笑着打了一下蒋鸣,红着脸说:“哪有啊,人家昨晚没有关机啦。”
蒋鸣边走过去边回头指着她说:“你看,撒谎了吧,都脸红了。”
我跟在后面笑得肚子都痛了,就是不敢笑出声,使劲憋着,这吃豆腐还能这样啊?
往前走几米就是传菜窗口,一个服务员拿着对讲机背对着蒋鸣,蒋鸣笑嘻嘻的指着人家说:“阿红,不是我说你,你的罩罩太紧了,后面都勒出印来了,赶紧换一个。什么时候又变大了?”
那个服务员脸一下红了,回头细声的说:“哪有大?你乱说!”
蒋鸣就用一只手在人家胸前比划了一下:“你看,你看,还说不大,比上次大多了。”
服务员赶紧闪开。我在后面实在忍不住了,哈哈大笑了起来。妈的,老子眼泪都笑出来了,肚子还疼。这蒋鸣,以前不是忧伤王子吗?难道这个本尊是他失散多年的孪生弟弟?
再往前走,是通向大厅的小门,一个领班站在那里。蒋鸣上前盯着她,领班警惕地退了一步。
蒋鸣就大声的说:“阿丽啊,我早告诉你了,我不喜欢这个颜色的口红。你看,上次那衣服的口红印就没有洗掉。下次记得换水果味的啊,我喜欢哈密瓜的。”
领班年纪快三十了,也是见过世面的。可是架不住蒋鸣大声啊,那边投过来几注好奇的目光。领班有点慌张的说:“阿鸣,上班时间呢,不要乱说哦。”
蒋鸣说:“是吗?可是我下班了呀!今晚一起看电影好吗?”
“没空!”领班给蒋鸣甩面子,我以为蒋鸣会下不了台。结果人家蒋鸣根本不在乎这些,指着领班上下打量了一下就笑眯眯说:“你是不方便吧?没关系,我可以等几天的。”
领班红着脸低头说:“才没有呢!”
蒋鸣:“没有就好,今晚老地方啊,不见不散!”
领班像吞了一个苍蝇一样愕然看着他。
哎呦!我受不了了,这个蒋鸣,什么人哪。想笑死人不用偿命啊?怎么看着这些女的个个和他有一腿呀,这都快把我笑趴下了。
我边捂着肚子笑,边擦着眼泪,跟着蒋鸣走向大门那边。
这还十几米没有到呢,两个迎宾和那个叫做阿敏的领班,就赶紧慌张的跑进大厅了。就好像躲瘟疫一样。蒋鸣指着后面跑得慢的一个迎宾,举起手里的万用表说:
“秀儿,来!拿朕的玉玺去砸个核桃吃。”那迎宾捂着嘴吃吃的笑,躲到大门后面去。
就这样跟着蒋鸣绕了酒店一圈,我在后面一路笑着跟他回到电工班,他放下东西就算下班了。东西放好,把嘴里的烟给点着,就领着我去了他的宿舍。
回到宿舍,他给我扔了一支矿泉水,然后就问我找他干嘛。现在严肃的样子,才像以前的蒋鸣嘛。不过刚才调戏那些服务员,看着还真是佩服,我都佩服得五个身体都掉地上了。
我把背包拉链拉开,给他看。他漫不经心扫了一眼,被这些古旧的东西吸引住了。把烟叼在嘴里,从我背包掏出那本星相的书来翻看。我把背包放在桌面,拧开水咕咚咕咚的喝。
翻了几页之后,他把我背包整个倒提起来,全部东西铺在桌面上,逐一打量。那认真的态度,就像他拿放大镜看那些碎片一样。
看了十几分钟,我水刚喝完,蒋鸣就说:“有戏,这回有戏了。原来你祖上有大能人啊。星相家,南天王,这些个个都是把炮的人物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