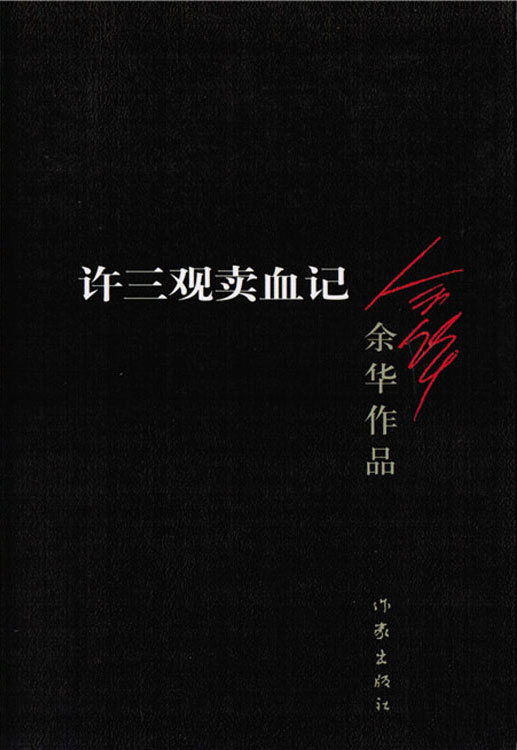许三观是城里丝厂的送茧工,这一天他回到村里来看望他的爷爷。他爷爷年老以后眼睛昏花,看不见许三观在门口的脸,就把他叫到面前,看了一会后问他:
“我儿,你的脸在哪里?”
许三观说:“爷爷,我不是你儿,我是你孙子,我的脸在这里……”
许三观把他爷爷的手拿过来,往自己脸上碰了碰,又马上把爷爷的手送了回去。爷爷的手掌就像他们工厂的砂纸。
他爷爷问:“你爹为什么不来看我?”
“我爹早死啦。”
他爷爷点了点头,口水从嘴角流了出来,那张嘴就歪起来吸了两下,将口水吸回去了一些,爷爷说:
“我儿,你身子骨结实吗?”
“结实。”许三观说,“爷爷,我不是你儿……”
他爷爷继续说:“我儿,你也常去卖血?”
许三观摇摇头:“没有,我从来不卖血。”
“我儿……”爷爷说,“你没有卖血,你还说身子骨结实?我儿,你是在骗我。”
“爷爷,你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懂,爷爷,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许三观的爷爷摇起了头,许三观说:
“爷爷,我不是你儿,我是你的孙子。”
“我儿……”他爷爷说,“你爹不肯听我的话,他看上了城里那个什么花……”
“金花,那是我妈。”
“你爹来对我说,说他到年纪了,他要到城里去和那个什么花结婚,我说你两个哥哥都还没有结婚,大的没有把女人娶回家,先让小的去娶,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
坐在叔叔的屋顶上,许三观举目四望,天空是从很远处的泥土里升起来的,天空红彤彤的越来越高,把远处的田野也映亮了,使庄稼变得像西红柿那样通红一片,还有横在那里的河流和爬过去的小路,那些树木,那些茅屋和池塘,那些从屋顶歪歪曲曲升上去的炊烟,它们都红了。
许三观的四叔正在下面瓜地里浇粪,有两个女人走过来,一个年纪大了,一个还年轻,许三观的叔叔说:
“桂花越长越像妈了。”
年轻的女人笑了笑,年长的女人看到了屋顶上的许三观,她问:
“你家屋顶上有一个人,他是谁?”
许三观的叔叔说:“是我三哥的儿子。”
下面三个人都抬着头看许三观,许三观嘿嘿笑着去看那个名叫桂花的年轻女人,看得桂花低下了头,年长的女人说:
“和他爹长得一个样子。”
许三观的四叔说:“桂花下个月就要出嫁了吧?”
年长的女人摇着头:“桂花下个月不出嫁,我们退婚了。”
“退婚了?”许三观的四叔放下了手里的粪勺。
年长的女人压低声音说:“那男的身体败掉了,吃饭只能吃这么一碗,我们桂花都能吃两碗……”
许三观的叔叔也压低了声音问:“他身体怎么败的?”
“不知道是怎么败的……”年长的女人说,“我先是听人说,说他快有一年没去城里医院卖血了,我心里就打起了锣鼓,想着他的身体是不是不行了,就托人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看他能吃多少,他要是吃两大碗,我就会放心些,他要是吃了三碗,桂花就是他的人了……他吃完了一碗,我要去给他添饭,他说吃饱了,吃不下去了……一个粗粗壮壮的男人,吃不下饭,身体肯定是败掉了……”
许三观的四叔听完以后点起了头,对年长的女人说:
“你这做妈的心细。”
年长的女人说:“做妈的心都细。”
两个女人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许三观,许三观还是嘿嘿笑着看着年轻的那个女人,年长的女人又说了一句:
“和他爹长得一个样子。”
然后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过去,两个女人的屁股都很大,许三观从上面看下去,觉得她们的屁股和大腿区分起来不清楚。她们走过去以后,许三观看着还在瓜田里浇粪的四叔,这时候天色暗下来了,他四叔的身体也在暗下来,他问:
“四叔,你还要干多久?”
四叔说:“快啦。”
许三观说:“四叔,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我想问问你。”
四叔说:“说吧。”
“是不是没有卖过血的人身子骨都不结实?”
“是啊,”四叔说,“你听到刚才桂花她妈说的话了吗?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
“这算是什么规矩?”
“什么规矩我倒是不知道,身子骨结实的人都去卖血,卖一次血能挣三十五块钱呢,在地里干半年的活也就挣那么多。这人身上的血就跟井里的水一样,你不去打水,这井里的水也不会多,你天天去打水,它也还是那么多……”
“四叔,照你这么说来,这身上的血就是一棵摇钱树了?”
“那还得看你身子骨是不是结实,身子骨要是不结实,去卖血会把命卖掉的。你去卖血,医院里还先得给你做检查,先得抽一管血,检查你的身子骨是不是结实,结实了才让你卖……”
“四叔,我这身子骨能卖血吗?”
许三观的四叔抬起头来看了看屋顶上的侄儿,他三哥的儿子光着膀子笑嘻嘻地坐在那里。许三观膀子上的肉看上去还不少,他的四叔就说:
“你这身子骨能卖。”
许三观在屋顶上嘻嘻哈哈笑了一阵,然后想起了什么,就低下头去问他的四叔:
“四叔,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
“问什么?”
“你说医院里做检查时要先抽一管血?”
“是啊。”
“这管血给不给钱?”
“不给,”他四叔说,“这管血是白送给医院的。”
他们走在路上,一行三个人,年纪大的有三十多岁,小的才十九岁,许三观的年纪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走去时也在中间。许三观对左右走着的两个人说:
“你们挑着西瓜,你们的口袋里还放着碗,你们卖完血以后,是不是还要到街上去卖西瓜?一、二、三、四……你们都只挑了六个西瓜,为什么不多挑一二百斤的?你们的碗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让买西瓜的人往里面扔钱?你们为什么不带上粮食,你们中午吃什么……”
“我们卖血从来不带粮食,”十九岁的根龙说,“我们卖完血以后要上馆子去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
三十多岁的那个人叫阿方,阿方说:
“猪肝是补血的,黄酒是活血的……”
许三观问:“你们说一次可以卖四百毫升的血,这四百毫升的血到底有多少?”
阿方从口袋里拿出碗来:“看到这碗了吗?”
“看到了。”
“一次可以卖两碗。”
“两碗?”许三观吸了一口气,“他们说吃进一碗饭,才只能长出几滴血来,这两碗血要吃多少碗饭啊?”
阿方和根龙听后嘿嘿地笑了起来,阿方说:
“光吃饭没有用,要吃炒猪肝,要喝一点黄酒。”
“许三观,”根龙说,“你刚才是不是说我们西瓜少了?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不卖瓜,这瓜是送人的……”
阿方接过去说:“是送给李血头的。”
“谁是李血头?”许三观问。
他们走到了一座木桥前,桥下是一条河流,河流向前延伸时一会宽,一会又变窄了。青草从河水里生长出来,沿着河坡一直爬了上去,爬进了稻田。阿方站住脚,对根龙说:
“根龙,该喝水啦。”
根龙放下西瓜担子,喊了一声:
“喝水啦。”
他们两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了碗,沿着河坡走了下去,许三观走到木桥上,靠着栏杆看他们把碗伸到了水里,在水面上扫来扫去,把漂在水上的一些草什么的东西扫开去,然后两个人咕咚咕咚地喝起了水,两个人都喝了有四五碗,许三观在上面问:
“你们早晨是不是吃了很多咸菜?”
阿方在下面说:“我们早晨什么都没吃,就喝了几碗水,现在又喝了几碗,到了城里还得再喝几碗,一直要喝到肚子又胀又疼,牙根一阵阵发酸……这水喝多了,人身上的血也会跟着多起来,水会浸到血里去的……”
“这水浸到了血里,人身上的血是不是就淡了?”
“淡是淡了,可身上的血就多了。”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都在口袋里放着一只碗了。”许三观说着也走下了河坡。
“你们谁的碗借给我,我也喝几碗水。”
根龙把自己的碗递了过去:“你借我的碗。”
许三观接过根龙的碗,走到河水前弯下身体去,阿方看着他说:
“上面的水脏,底下的水也脏,你要喝中间的水。”
他们喝完河水以后,继续走在了路上,这次阿方和根龙挑着西瓜走在了一起,许三观走在一边,听着他们的担子吱呀吱呀响,许三观边走边说:
“你们挑着西瓜走了一路,我来和你们换一换。”
根龙说:“你去换阿方。”
阿方说:“这几个西瓜挑着不累,我进城卖瓜时,每次都挑二百来斤。”
许三观问他们:“你们刚才说李血头,李血头是谁?”
“李血头,”根龙说,“就是医院里管我们卖血的那个秃头,过会儿你就会见到他的。”
阿方接着说:“这就像是我们村里的村长,村长管我们人,李血头就是管我们身上血的村长,让谁卖血,不让谁卖血,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数。”
许三观听了以后说:“所以你们叫他血头。”
阿方说:“有时候卖血的人一多,医院里要血的病人又少,这时候就看谁平日里与李血头交情深了,谁和他交情深,谁的血就卖得出去……”
阿方解释道:“什么是交情?拿李血头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卖血时才想起我来,平日里也要想着我’。什么叫平日里想着他?”
阿方指指自己挑着的西瓜:“这就是平日里也想着他。”
“还有别的平日里想着他,”根龙说,“那个叫什么英的女人,也是平日里想着他。”
两个人说着嘻嘻笑了起来,阿方对许三观说:
“那女人与李血头的交情,是一个被窝里的交情,她要是去卖血,谁都得站一边先等着,谁要是把她给得罪了,身上的血哪怕是神仙血,李血头也不会要了。”
他们说着来到了城里,进了城,许三观就走到前面去了,他是城里的人,熟悉城里的路,他带着他们往前走。他们说还要找一个地方去喝水,许三观说:
“进了城,就别再喝河水了,这城里的河水脏,我带你们去喝井水。”
他们两个人就跟着许三观走去,许三观带着他们在巷子里拐来拐去的,一边走一边说:
“我快憋不住了,我们先找个地方去撒一泡尿。”
根龙说:“不能撒尿,这尿一撒出去,那几碗水就白喝啦,身上的血也少了。”
阿方对许三观说:“我们比你多喝了好几碗水,我们还能憋住。”
然后他又对根龙说:“他的尿肚子小。”
许三观因为肚子胀疼而皱着眉,越走越慢,他问他们:
“会不会出人命?”
“出什么人命?”
“我呀,”许三观说,“我的肚子会不会胀破?”
“你牙根酸了吗?”阿方问。
“牙根?让我用舌头去舔一舔……牙根倒还没有酸。”
“那就不怕,”阿方说,“只要牙根还没酸,这尿肚子就不会破掉。”
许三观把他们带到医院旁边的一口井前,那是在一棵大树的下面,井的四周长满了青苔,一只木桶就放在井旁,系着木桶的麻绳堆在一边,看上去还很整齐,绳头搁在把手上,又垂进桶里去了。他们把木桶扔进了井里,木桶打在水上“啪”的一声,就像是一巴掌打在人的脸上。他们提上来一桶井水,阿方和根龙都喝了两碗水,他们把碗给许三观,许三观接过来阿方的碗,喝下去一碗,阿方和根龙要他再喝一碗,许三观又舀起一碗水来,喝了两口后把水倒回木桶里,他说:
“我尿肚子小,我不能喝了。”
他们三个人来到了医院的供血室,那时候他们的脸都憋得通红了,像是怀胎十月似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着,阿方和根龙还挑着西瓜,走得就更慢,他们的手伸开着抓住前后两个筐子的绳子,他们的手正在使着劲,不让放着西瓜的筐子摇晃。可是医院的走廊太狭窄,不时有人过来将他们的筐子撞一下,筐子一摇晃,阿方和根龙肚子里胀鼓鼓的水也跟着摇晃起来,让两个人疼得嘴巴一歪一歪的,站在那里不敢动,等担子不再那么摇晃了,才重新慢慢地往前走。
医院的李血头坐在供血室的桌子后面,两只脚架在一只拉出来的抽屉上,裤裆那地方敞开着,上面的纽扣都掉光了,里面的内裤看上去花花绿绿。许三观他们进去时,供血室里只有李血头一个人,许三观一看到李血头,心想这就是李血头?这李血头不就是经常到我们厂里来买蚕蛹吃的李秃头吗?
李血头看到阿方和根龙他们挑着西瓜进来,就把脚放到了地上,笑呵呵地说:
“是你们啊,你们来了。”
然后李血头看到了许三观,就指着许三观对阿方他们说:
“这个人我像是见过。”
阿方说:“他就是这城里的人。”
“所以。”李血头说。
许三观说:“你常到我们厂里来买蚕蛹。”
“你是丝厂的?”李血头问。
“是啊。”
“他妈的,”李血头说,“怪不得我见过你,你也来卖血?”
阿方说:“我们给你带西瓜来了,这瓜是上午才在地里摘的。”
李血头将坐在椅子里的屁股抬起来,看了看西瓜,笑呵呵地说:
“一个个都还很大,就给我放到墙角。”
阿方和根龙往下弯了弯腰,想把西瓜从筐子里拿出来,按李血头的吩咐放到墙角,可他们弯了几下没有把身体弯下去,两个人面红耳赤气喘吁吁了,李血头看着他们不笑了,他问:
“你们喝了有多少水?”
阿方说:“就喝了三碗。”
根龙在一旁补充道:“他喝了三碗,我喝了四碗。”
“放屁,”李血头瞪着眼睛说,“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人的膀胱有多大?他妈的,你们的膀胱撑开来比女人怀孩子的子宫还大,起码喝了十碗水。”
阿方和根龙嘿嘿地笑了,李血头看到他们在笑,就挥了两下手,对他们说:
“算啦,你们两个人还算有良心,平日里常想着我,这次我就让你们卖血,下次再这样可就不行了。”
说着李血头去看许三观,他说:
“你过来。”
许三观走到李血头面前,李血头又说:
“把脑袋放下来一点。”
许三观就低下头去,李血头伸手把他的眼皮撑开: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看看你的眼睛里有没有黄疸肝炎……没有,再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你的肠胃……肠胃也不错,行啦,你可以卖血啦……你听着,按规矩是要抽一管血,先得检验你有没有病,今天我是看在阿方和根龙的面子上,就不抽你这一管血……再说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这就算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
他们三个人卖完血之后,就步履蹒跚地走向了医院的厕所,三个人都歪着嘴巴。许三观跟在他们身后,三个人谁也不敢说话,都低着头看着下面的路,似乎这时候稍一用劲肚子就会胀破了。
三个人在医院厕所的小便池前站成一排,撒尿时他们的牙根一阵阵剧烈地发酸,于是发出了一片牙齿碰撞的响声,和他们的尿冲在墙上时的声音一样响亮。
然后,他们来到了那家名叫胜利的饭店,饭店是在一座石桥的桥堍,它的屋顶还没有桥高,屋顶上长满了杂草,在屋檐前伸出来像是脸上的眉毛。饭店看上去没有门,门和窗连成一片,中间只是隔了两根木条,许三观他们就是从旁边应该是窗户的地方走了进去,他们坐在了靠窗的桌子前,窗外是那条穿过城镇的小河,河面上漂过去了几片青菜叶子。
阿方对着跑堂的喊道:“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给我温一温。”
根龙也喊道:“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我的黄酒也温一温。”
许三观看着他们喊叫,觉得他们喊叫时手拍着桌子很神气,他也学他们的样子,手拍着桌子喊道:
“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温一温。”
没多少工夫,三盘炒猪肝和三盅黄酒端了上来,许三观拿起筷子准备去夹猪肝,他看到阿方和根龙是先拿起酒盅,眯着眼睛抿了一口,然后两个人的嘴里都吐出了咝咝的声音,两张脸上的肌肉像是伸懒腰似的舒展开来。
“这下踏实了。”阿方舒了口气说道。
许三观就放下筷子,也先拿起酒盅抿了一口,黄酒从他嗓子眼里流了进去,暖融融地流了进去,他嘴里不由自主地也吐出了咝咝的声音,他看着阿方和根龙嘿嘿地笑了起来。
阿方问他:“你卖了血,是不是觉得头晕?”
许三观说:“头倒是不晕,就是觉得力气没有了,手脚发软,走路发飘……”
阿方说:“你把力气卖掉了,所以你觉得没有力气了。我们卖掉的是力气,你知道吗?你们城里人叫血,我们乡下人叫力气。力气有两种,一种是从血里使出来的,还有一种是从肉里使出来的,血里的力气比肉里的力气值钱多了。”
许三观问:“什么力气是血里的?什么力气是肉里的?”
阿方说:“你上床睡觉,你端着个碗吃饭,你从我阿方家走到他根龙家,走那么几十步路,用不着使劲,都是花肉里的力气。你要是下地干活,你要是挑着百十来斤的担子进城,这使劲的活,都是花血里的力气。”
许三观点着头说:“我听明白了,这力气就和口袋里的钱一样,先是花出去,再去挣回来。”
阿方点着头对根龙说:“这城里人就是聪明。”
许三观又问:“你们天天下地干重活,还有富余力气卖给医院,你们的力气比我多。”
根龙说:“也不能说力气比你多,我们比你们城里人舍得花力气,我们娶女人、盖屋子都是靠卖血挣的钱,这田地里挣的钱最多也就是不让我们饿死。”
阿方说:“根龙说得对,我现在卖血就是准备盖屋子,再卖两次,盖屋子的钱就够了。根龙卖血是看上了我们村里的桂花,本来桂花已经和别人订婚了,桂花又退了婚,根龙就看上她了。”
许三观说:“我见过那个桂花,她的屁股太大了,根龙你是不是喜欢大屁股?”
根龙嘿嘿地笑,阿方说:“屁股大的女人踏实,躺在床上像一条船似的,稳稳当当的。”
许三观也嘿嘿笑了起来,阿方问他:“许三观,你想好了没有?你卖血挣来的钱怎么花?”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花,”许三观说,“我今天算是知道什么叫血汗钱了,我在工厂里挣的是汗钱,今天挣的是血钱,这血钱我不能随便花掉,我得花在大事情上面。”
这时根龙说:“你们看到李血头裤裆里花花绿绿了吗?”
阿方一听这话嘿嘿笑了,根龙继续说:
“会不会是那个叫什么英的女人的短裤?”
“这还用说,两个人睡完觉以后穿错了。”阿方说。
“真想去看看,”根龙嬉笑着说,“那个女人是不是穿着李血头的短裤。”(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