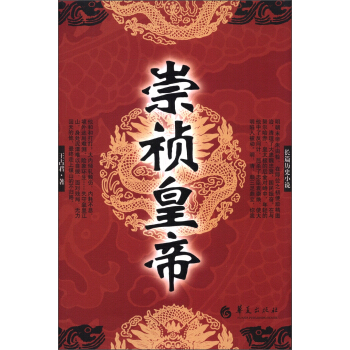许誉卿一听,手中笔都险些掉到桌案上,他心说,后金何等强大,五年岂能平辽,这袁督师既敢放言,定有锦囊妙计。
“好,朕就耐心等你五年。”崇祯却显得兴奋异常,“朕相信袁督师的能力,再有朕的全力相助,五年复辽可期也。大明中兴有望也,朕也必将以英明皇帝的上佳形象载人史册。”
一看崇祯对五年复辽期许如此之高,袁崇焕有几分忐忑,但话已说出,覆水难收,他也只能壮起胆来:“万岁英明睿智,定是中兴之主。”
当晚,在袁崇焕的下榻处,许誉卿特来拜访。来人官职仅是个兵科给事中,袁崇焕便不太看重:“许大人前来,不知有何见教?”
“见教不敢当,下官是前来求教。”
“本督有何德能,许大人却出此言?”
“袁督师日间在平台受万岁召对,看得出皇上对大人的器重,把大人倚为国家栋梁。下官有一事不明,督师言道,五年时间即可复辽,下官总觉得此事难度甚大,不知督师有何妙计?”
“这个,”袁崇焕一时不好回答,“不过是信口而语。”
“袁大人,这样重大的问题,岂可任意而答,这是作为臣子在君前的承诺,说话是要算数的。”
“许大人,难道你没看见皇上对平辽的急切心情,本督只有如此回答,方能聊慰万岁之心。”
“袁大人,”许誉卿提醒,“皇上可不是糊涂人,他的英明超过乃兄乃父多多,圣上对你的要求悉数准奏,等到了五年你不能复辽,只怕你没法交待,皇上也难以放过你。”
袁崇焕被说得后脊梁直冒凉风,有些怅然若失:“事巳至此,如之奈何,且努力去做,尽人事凭天意吧!”
许誉卿也不好再说什么,恰好内阁大学士钱龙锡来访,他正好趁势退走。袁崇焕对钱龙锡的态度与许誉卿相比,就是天壤之别了,他上前一躬:“钱阁老大驾光临,令下官不胜惶恐。”
“袁督师言重了,”钱龙锡也会看门道,“今日平台召对,皇上对袁大人宠信有加,言听计从,实令我等望尘莫及。”
“万岁看重,也是下官的压力,真不知该如何完成皇上五年复辽的宏图大略,还望阁老指点一二。”
“用兵关键是在用人,倘人非己用,指挥不灵,谈何打胜仗。”钱龙锡语重心长,“手下大将,必须是自己人。”
“故而下官在召对时,已提出三个总兵的人选,所幸万岁皆已应允,下官指挥起来便可得心应手。”
“可是袁督师忘了一位极为关键的总兵人选,没有这个人的听调听用,只怕你五年复辽的期望会成为泡影。”
“下官愚钝,但不知还有何处总兵?”袁崇焕深深一揖,“万望阁老大人指点迷津。”
钱龙锡轻轻吐出几个字皮岛总兵毛文龙。”
“他,”袁崇焕知晓这皮岛的毛文龙,应是自己的麾下,可这皮岛远在后金的后方,要到皮岛除海路外,只能通过后金的辖地,故而他没太往心里去,也就没打他这张牌,“钱阁老,皮岛远在海外,有后金阻隔,其实并不重要,复辽大业有他无他料无大碍。”
“袁督师此言差矣。”钱龙锡认真地为袁崇焕摆讲起皮岛和毛文龙的重要性,“你属下三镇总兵的兵力也就四万人,而皮岛一地便有四万五千人,而且毛文龙还经营船运走私生意,所获颇丰,一向是自成独立王国。他从来不服蓟辽督师的调遣,历任长官如孙承宗、杨嗣昌,都对他无可奈何。如今就看袁督师的手段和气魄了,皮岛的四万多大军不能握在手中,复辽之举难上加难,甚至是无望。”
袁崇焕听后也感到这皮岛确实是个关键:“钱阁老,如何对付毛文龙,还请为下官指条明路。”
“可用则用之,如他不为所用,即当除之。”
袁崇焕点头其兵势众,若除当如何除毛。”
“人其军,直取其头。”钱龙锡意在鼓动,“这样方可威慑毛文龙的下属,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领教了。”袁崇焕不再做更明白的表态。
次日,袁崇焕离京返归关外,户部紧急筹措到三十万两白银。他带着皇帝的信任与期待,带着上方宝剑和大笔白银,意气风发地回到了宁远。一路上毛文龙的事在他的心头萦绕,到了督师衙门,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传令所有货船一律不得再停靠皮岛。这一下等于是掐住了毛文龙的命脉,一下子断了皮岛的财路不说,毛文龙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海上大风掀起滔天巨浪,岛上的树木都给连根拔起。总兵府的房瓦也被刮掉了,落在地上噼啪摔得粉碎。毛文龙心情格外烦躁,他对走进厅堂的手下亲信大将,不住地吹胡子瞪眼:“你们都是混蛋,让你们来议事,却为何这许久才到?让你们拖拉,明天你们西北风都喝不上。”
先后走进厅内的副将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和水营都司赵可怀,他们已习惯了毛文龙的训斥,一起躬身施礼,同声认错大帅息怒,我等因故来迟,以后再也不敢。”
“再若这样不遵守军令,我按个打断你们的狗腿。”毛文龙愁锁双眉,“新任督师袁崇焕,断了我们的财路,这皮岛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大伙说说该怎么办?”
尚可喜心中早有算计:“这有何难,数万大军总不能饿死,大帅就向袁督师要军饷。”
“还不能指着他这一棵树吊死。”耿仲明又有主意,“同时给皇帝上本,就说皮岛业已断粮,已是军心不稳,朝廷再不拨发军锏,只怕兵将反叛。”
“我看袁督师意不在此,”赵可怀自有他的见解,“这些年皮岛一直独立于莉辽之外,不要军饷自给自足,也不受督师的调遣,袁督师不怕给军饷,是想要皮岛兵将听他指挥。”
“凭啥!”孔有德很是反感,“我们远在后金的后方,牵制了后金兵力,自己过得好好的,干嘛要头顶找个菩萨贡着?”
耿仲明提出:“给皇上加点压力,就说我皮岛有二十万大军,每年军费至少五十万两白银,让皇上掏不起,也把袁崇焕镇住,他们就不再打我们的主意了。”
“不可,”赵可怀反对,“我们实有兵力四万,虚报二十万,那可就是欺君之罪,真要査实,大帅就是死罪。”
“放屁!”毛文龙开口便骂,“你小子难道要私下里告我欺君?我看你这是活够了。”
“末将不敢,”赵可怀急加解释,“末将是想全岛这四万多人,难保无人不将底细捅出去,末将是为大帅着想,倘为此罹罪就太不值了“本帅是这皮岛的主人,谁敢对本帅背后捅刀子?”毛文龙恶狠狠地,“此事若不漏还则罢了,若走漏消息,就定是你干的。”
“大帅冤枉末将。”赵可怀心中着实懊悔,自己这是何苦。
耿仲明问:“大帅害怕不上本了?”
“怕个球,”毛文龙一意孤行,“给皇上和袁崇焕都报称二十万大军,就要五十万两军饷。”
崇祯接到毛文龙的奏疏,眉头皱起,询问身边的内阁大学士钱龙锡钱大人,毛文龙的皮岛驻军能有二十万吗?朕怎么觉得不靠谱。”
“万岁圣明。”钱龙锡回答,“其实皮岛的军队,满打满算也就四万人。”
“毛文龙他这是要借机想多弄一笔钱花。”崇祯言外之意,并没有对毛文龙过分苟责。
钱龙锡对毛文龙素无好感:“可他也不该狮子大开口,万岁,毛文龙这可是欺君之罪。”
“以往皮岛军饷是如何解决?”
“全系自筹。”
“现在为何忽然想起向朕要饷?”
“那是袁崇焕断了他的财路。”钱龙锡深人下去说,“袁督师禁绝走私无可非议,长此下去,毛文龙还不成了独立于大明之外的皮岛王国。”
崇祯对毛文龙的看法还有独到见解:“皮岛的作用不可低估,他的人马足以同关东铁骑相媲美,他对后金的骚扰,对后金进犯朝鲜的牵制,是旁人难以取代的。因此,对毛文龙还当善加抚慰。”钱龙锡一听立时转换了口气万岁所言极是,毛文龙这种粗鲁的统帅,不要计较其小节,还是要看他的用处。”
崇祯看看身边的秉笔太监王承恩:“拟旨,着袁崇焕从现有军饷中拨付皮岛十万两。”
“奴才遵旨。”
钱龙锡还是不忘对毛文龙的旁敲侧击:“万岁,毛文龙要的是五十万两,十万怕他是不满意呀。”
“他应该知道进退,”崇祯言道,“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
“只是,”钱龙锡犹豫一下还是说,“袁大人那里能否愿意拿出,他毕竟才带走三十万两,而且宁远还有四个月的欠饷。”
“朕想,袁崇焕是不会抗旨的。”
“应该是。”钱龙锡回府后,派得力家人,给袁崇焕送去一封急信,详细通报了事情经过。
袁崇焕接到钱龙锡的密信,心中对毛文龙更加不满。好你个毛文龙,竟然在皇上那里告我的御状。要不是钱阁老报信,自己不按时按数给付皮岛军饷,还不得惹皇上发怒。第二天崇祯的上谕由传旨专差送到。袁崇焕早已打定了主意,派家人袁成,专程去皮岛传令。
毛文龙在总兵衙署大大咧咧地接见了袁成:“上差,一路风波颠簸至我这荒山野岛,不知有何贵干?”
袁成格外谦恭:“总兵毛大人在上,请受我一拜。”
“这如何使得,你是督师的上差。有道是宰相家人七品官,咱没有去码头迎接,不怪我礼数不周便已谢天谢地。”
“我带来袁督师的亲笔书信,请毛大人过目。”袁成呈上信函。毛文龙不经意地接过信,打开便看。他看着看着,不觉脸上笑逐颜开:“上差,这信中所言都是真的?”
“军中大事,岂有戏言。”袁成平静地回答,“况且这是督师亲笔,就更不会有假了。”
“好,请回禀督师大人,七日之后我在皮岛恭迎督师大人前来视察。”毛文龙客气多了,对侍立的赵可怀吩咐,“赵将军,烦你带上差到馆驿休息,准备好晚间的酒宴。”
“这就不劳毛大人费心了。”袁成推辞道,“督师要我即刻返回,小人不敢有误。”
“好,恭敬不如从命。”毛文龙嘱咐,“赵将军,礼送上差登船,再给带上我们皮岛的土特产。”
“末将遵令。”赵可怀与袁成亲亲热热地走出官衙,走向码头。袁成四顾无人,低声对赵可怀道:“赵将军,行前,袁督师要我特别带两句话给你。”
赵可怀一怔请上差示下。”
“袁督师知你为人素怀忠义,要你在关键时刻听从皇上和督师的意见,不可迷失方向。”
“这,”赵可怀还想再掏底,“末将愚钝,督师之言,不甚明了,上差可否再做明示。”
“响鼓何须用重锤。”袁成自然不会多讲,但却叮嘱道,“此番话系只对将军一人所言,万勿外泄。”
“末将记下了。”赵可怀目送袁成的船开走,之后返回总兵官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