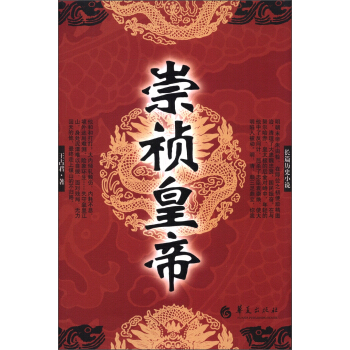刽子手手起刀落,高迎祥的人头落地。此时此刻,崇祯有一种成功的自豪感。多年的剿匪,而今总算取得了进展。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认定自己就是中兴之主,肃清全部匪患已是指日可待。
内阁首辅温体仁见崇祯已是陷人深思,不免提醒道:“万岁,还有三个匪首没有发落呢?”
“还用问,杀!”
温体仁向下传旨圣上有令,把高杰、黄龙、刘哲问斩。”
“万岁,小人冤枉呀!”高杰实在不甘心,他高声疾呼,“小人无罪,还有大功,这子午谷大捷,就是小人的功劳。”
“噢崇祯听到了高杰的喊冤声,一向多疑的皇帝又起了疑心,“莫非这其中还有隐情?”
“不会吧,”温体仁不以为然,“人之将死,大多胡攀乱咬,耸人听闻地胡吹,无非想保全性命而已。”
“且带他上来,朕要问话。”崇祯可是个有主意的人。
高杰被带上午门城楼,未及跪倒见驾,当他与温体仁四目相对,就是一怔,张了张嘴想要说话。温体仁避开高杰的目光喝道:“该死的贼寇,见了皇上还不赶快跪拜。”
“草民高杰叩见万岁爷!”高杰说着,眼睛还瞄向温体仁。
崇祯绝顶聪明,感觉到其中必有缘由,但他隐忍不发,而是盘问高杰:“你说你有冤,冤从何来?”
“万岁,草民本是高迎祥义子,因与李自成不睦逃离,而主动投奔孙传廷大人。并侦察得到民军要走子午谷偷袭西安的军情,孙大人方能在谷口设伏,获得此次大捷,草民不求犒赏,但求免除死罪,自去过农耕的日子,恳请万岁明鉴。”高杰说着不住叩头。
“你无奈之下投靠,并不是主动归顺,做些许小事亦属常理。况且尔等反复成性,惯会降而复叛,留下总是祸害,孙传廷把你列人问斩名单,实为明智之举。”崇祯从来就有独到的见解,“你的死罪难免。”
“万岁饶命啊!”高杰情急,他转向温体仁求救,“温阁老,望您在皇上面前美言,救小人一条狗命。”
“这就怪了,你身为朝廷要犯,死罪当斩,为何向我求情。”温体仁一副无关的样子,“我与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毫不相干,真是咄咄怪事。”
“温阁老,请你看在我舅舅的薄面上,也要说句话救我一命。”高杰已是不住地给温体仁叩头。
“你舅舅,他是哪个,与我什么相干?”
“温阁老贵人多忘事,我舅舅他是钱谦益呀。当初他在朝中为官,温阁老尚未入阁,到他家中拜访,小人曾与您有一面之识。如今我总算为朝廷出了大力,建有大功。温阁老身居要位,说句话举手之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啊!”高杰叩头犹如鸡琢米。
温体仁明白崇祯已生疑心,便冷冷地说我与钱大人只是官场的正常交往,万岁英明睿智,自有处理你的方略。谁说也没有用,你的生死只能由万岁来决定,不要再打我的主意。”
崇祯向来反对臣下窥测他的心思,常常令臣下感到突然:“把高杰权且打人死牢待斩,黄龙、刘哲立即开刀。”
“领旨。”王承恩传旨下去。
黄、刘二人人头落地,高杰被押入了死牢。负责押送战俘进京的副将,又被召上午门城楼,跪拜之后心怀忐忑的等待训话。
崇祯心中髙兴,但他脸上丝毫也不表现出来:“回去把朕的口谕让孙传廷知晓,子午谷大捷朕心甚慰,加孙传廷兵部侍郎衔。还当再接再厉,于年内把张献忠、刘国能、李自成剿平,使朕能过上一个喜庆年。”
“末将领旨。”
“告诉孙传廷,朕还要传旨给洪承畴,他二人要密切合作,在谁的防区出纸漏,肤就追究谁的责任。”崇祯特别加重语气,“如果届时不能平灭贼匪,休要怪朕不讲情面。”
“末将记下了。”副将唯唯而退。
崇祯用异样的目光,扫视温体仁一下,什么也没说,径自下了午门,返回后宫去了。
温体仁回到府中心潮久久难平。真是平地风波起,好好的出来一个高杰,偏偏扯上自己同钱谦益的旧交。皇上原本疑心就重,这下他不杀高杰,又想到崇祯的异样目光,温体仁感到不寒而栗。看起来自己决不能听之任之,为保住相位,还要主动出击。经过一番思索,一条妙计涌上心头。
夜色像一张硕大的黑网,把整个庭院罩住。张汉儒独坐灯下,正在自斟自饮。说起来他也是举人出身,原本想考中进士走上仕途,至少也能当个知县,也好大展宏图。可是时运不济,考来考去,他也只能像范进一样,停留在举人的位子上。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到县衙做了一名师爷。对于这侍候人的差使,他实在是感到羞耻,常有怀才不遇之感,为此他常常以酒浇愁。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月前他特地给内阁首辅温体仁写了一封自荐信,信中他用华丽的语言,展示了他的治国理念,期待得到这位温阁老的赏识。起初,他抱有相当大的希望,认为自己的信动情人理,温首辅看后一定会弓I起重视,说不定就会得个一官半职。
可是整整一个月过去了,京城方面依然是音讯渺然。张汉儒彻底绝望了,夜已二更,还在一个人自己喝闷酒,借以打发无聊的大好时光。酒入愁肠,酸不叽地哼起诗来:
文章盖世孔明才,夜明宝珠沙土埋。
光阴虚度四十载,师爷小位尚徘徊。
自幼渴望乌纱戴,梦里官运盼不来。
他年若得为知县,绿呢官轿八人抬。
忽然他感到身后有人的喘息声,不觉扭过头来吓得他“啊”了一声。面前站着一位黑衣人,头上还罩着黑色头套,只露出两只眼睛,“你,你是什么人,为何一点动静没有便进得房中?”
“老子上天入地还不容易,”黑衣人“嘿嘿”笑了几声,“听你吟的破诗,分明是渴望出人头地,我就是为你送富贵来的。”
“你此话何意?”
“你不是给温阁老写过求助信吗?阁老动了恻隐之心,要给你谋个比较肥的一官半职。”
“此话当真?”张汉儒有些激动,日思夜想得不到的东西,这说来就来了我是否跟你进京?”
“你还要办一件事情,通过了这次考验,才能进京,由温阁老吩咐吏部给你安排相应官职。”
“那你说,要我做什么?”
“写一封御状,状告东林党人钱谦益。”黑衣人叮嘱,“写状子对于你这做师爷的,可说是易如反掌。不过一定要写得严重,要多给他罗织罪名,使皇上看后大为震怒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小人明白。”张汉儒问,“写好后,我又如何把信交与阁老?”
“你连夜动笔,天明前我来取走。”黑衣人语气不无威胁之意,“五更时分,你不能拿出这份御状,那就没有机会了,能写的人还不遍地皆是。”
“写吧,不要看我。”
张汉儒铺展看纸,提起笔,饱蘸墨,便要动笔。回头再看,黑衣人早已没了踪影。心说真是来无影去无踪。一想到就要做官发达,不觉精神倍增,立刻文思泉涌,笔走龙蛇,刷刷点点,一挥而就。而且是工整的蝇头小楷,字迹清楚。从头阅看一遍,数了数一共给钱谦益列出五十八条罪状。自己也较为满意,正得意地放下笔,用嘴哈气让状纸快些干时,身后传来黑衣人的声音:“好一份刁状,此番只恐钱谦益难逃公道。”
张汉儒转过身:“先生,你何时又返回,状子看过了?”
“我这眼睛一扫,即已看过全文。”黑衣人表扬道,“阁老没有看错人,看来你这个知县是到手了。”
“但不知小人何时才能进京?”
“急不得,待钱谦益被皇上定罪之时,就是你的出头之日。”黑衣人安抚,“耐心等待,好饭不怕晚。”
“小人在家恭候。”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说起是奉阁老之命写这御状。若是露底,不只你知县当不成,恐怕连脑袋也保不住。”
“啊,还有这样大的风险!”
黑衣人安慰道:“无需多虑,我只是嘱咐你有所防备,温阁老办的事,谁还敢来找你的麻烦。”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
黑衣人收起状纸,转身就走。张汉儒送到门口,再一看时,人影巳在房顶,倏忽间便不见了。张汉儒简直看得发呆,如此身手要坏人性命,还不就是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宫灯把乾清宫照得雪亮,崇祯面前摆放着那份御状。从头到尾整整五十八条大罪,当年魏忠贤不过也才二十四款罪状。崇祯心潮起伏,钱谦益号称正人君子,文章魁首,曾为朝廷重臣,因科举受贿之罪,是朕法外开恩,被废黜回乡为民。想不到他竟然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如此戴着正人君子帽子的恶徒,才更为可恨可恶。
温体仁一直注意着崇祯的神态表情,他已看透了皇帝的心思,故意在一旁说:“万岁,这写状之人,一定是个包揽词讼的刀笔吏,极尽污蔑之能事,给钱大人罗列这么多罪状,显然是要置他死地而后快。”
“你的意思呢?”崇祯不露声色地问。
“还是不要理踩为上。”
崇祯心说难怪高杰咬你同钱谦益有旧交,果然要为他开脱:“温大人,五十八条不能说条条俱实,可这八条总还有吧?”
“这也难说。”
崇祯把朱笔在状纸上批下四个字:拘京勘问。“温大人,拿去办吧。”
温体仁心中暗喜,这个祸害总算快要除掉了。他表现出不髙兴的样子微臣遵旨。”
圣旨有了,钱谦益被逮进了京城。这一来,堪称是朝野震动。因为钱谦益名气太大了,况且毕竟曾官拜尚书之职,他的亲朋故旧甚多,纷纷上表保奏。几日之内,保他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到皇帝的御案。什么礼部给事中、各部郎中、侍郎、尚书、甚至内阁大学士都参与保钱。温体仁也不忘凑热闹,他也上了一道保释钱谦益的表章。
崇祯对着连篇累牍的表章越看越烦,他没想到钱谦益还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这说明钱谦益他们结党很深。对于这些表章,崇祯一概不予理睬,他要看看还有多少人为钱谦益开脱。
刚开始时,钱谦益对于县衙小吏的告状并不在意。现在他明白了,事情远比他想的严重。究竟谁是幕后黑手,他却无从知晓。他放下清高的架子,亲自给皇帝写了申诉书,托人送达给了崇祯。但是崇祯看也不看,认定钱谦益就是有罪。而且风言风语传出,崇祯是要定他的死罪。这一下钱谦益真的慌了,这天他一夜未睡,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钱谦益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求救信,托人送给了司礼秉笔太监曹化淳。这个曹公公而今是与王承恩同等重要的皇帝亲信,如今只有他出面能和崇祯说上话。曹化淳接到信后反复掂量许久,想起自己曾求过钱谦益,自己的师父王安的墓志铭,就是自己登门拜求的钱谦益,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管管这件闲事。曹化淳开始上下活动,他把王承恩的工作也作通了,崇祯皇帝居然松口了。
温体仁万没想到曹化淳会掺和进来,他明白打蛇不死反被蛇咬的道理,决心置钱谦益于死地。就招了个假证人,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送钱,而曹化淳受贿后给钱谦益活动。原本就多疑多变的崇祯,便又改了主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