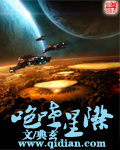“哐——”
苏姨竟直接自石阶上滚落了下来,腿上与右胸处别了两根木箭,白色的箭羽竟也被染的通红,萧弥繁木讷地站在原地,直至石室内阵阵白烟飘进。
萧弥繁蛾眉倒蹙,急忙奔向了洞口,只见白色的浓烟已朝着石室奔腾而来,她眼底划过一抹死寂。
苏姨猛然咳嗽了几声,呻吟声不断。萧弥繁冷眼瞧着她笑着说道:“苏姨,被人瓮中捉鳖的感觉如何?想来当初你便是这样对我时心中一定爽快不已,果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苏姨抬眸瞪着萧弥繁,漠然说道:“今日死在这里的可不止我一人,这陆离住在此处,他定然也是知晓你入了石室的,竟也不再怜香惜玉,连你一并也灭了,我死倒是不打紧,身旁有一大国公主陪葬,倒也值了。”
“那你怎会知晓室外之人乃是陆离,弥繁可记得方才进来时端王是入了书房的。”弥繁眼尾迤逦,缓缓蹲了下来,灼热的目光紧锁趴在地上剧烈咳嗽之人。
“咳——咳——咳——”
烟雾缭绕,且愈加多了,萧弥繁虽说喉间一丝不适,但却不如苏姨那般难受,苏姨整个人离地面又贴近了一些,呛人的气体越发浓郁了。
“王爷不会的!王爷曾说过他此生定不会舍弃于我的!咳……咳咳……”苏姨歇斯底里地喊着,心底早已有了答案,行动之前端王曾兰州说过,无论如何,他都会保全大局,不过也不会让自己受伤的,只是,他到底是他,若他能够有半点私情,也许如今他就不是端王了。
石室中已朦胧到无法看清周围的事物了,墙壁上的火盆熊熊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萧弥繁终于也受不了了,扶着墙壁咳嗽了几声,气喘吁吁地说道:“事到如今,你还是这般自欺欺人!”
意识逐渐朦胧模糊,萧弥繁跪在地上头晕无比,却听到苏姨沧桑模糊的声音,带了几分悲戚,“哈哈哈……我穷尽一生,为了个比我小许多的男子,到头来,却不过是一颗可有可无的棋子……哈哈哈……”
听得刀刃别进胸腔血液四溅的声音,未多时,石室便再无响动。萧弥繁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眸低水波荡漾,说到底苏姨也不过是个可怜的女人而已,但自己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翌日,晨起时景都中已被太阳度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威严大气的景都一片祥和模样。宫中却截然相反,朝堂之中气氛俨然一副凝滞之态。正中跪着的两个人俱是低头不语,龙椅上的建宁帝龙颜颇有些难看,朝中大臣也是一副蔫答答之态。
良久,建宁帝才沉着声说道:“灏儿,你对昨夜之事可有辩解?”
“回父皇,昨夜儿臣只是去五弟府上饮酒,并未有其他意思,五皇弟一事儿臣百口莫辩,甚是冤枉,还希望父皇明查!”
“事到如今,你竟还嘴硬!简直冥顽不灵!”皇弟一巴掌拍在龙头扶手之上,气的险些站了起来,“如今你躺在床上五皇弟生死未卜,朕曾无数次说过无论何时定要将手足之情放在首位,若不是被人瞧见你亲手将你五弟推入那石室,怕是朕今日就要失去一个儿子了是么?”
“父皇!”周景灏急忙大拜了一下,“父皇,儿臣冤枉啊!五弟昨夜说是去书房寻什么物什,儿臣见五弟久久不来,担心之余便进去了,谁知……”
建宁帝闭上眼,稍微压了压怒火,转而说道:“那石室中的两具死尸你又该如何解释?老五的府中密室竟有你的人?”
“父皇,虽说的确是儿臣的人,儿臣也不知晓为何会在石室……”
“闭嘴!”建宁帝怒道,移眼到了身旁颤抖的男子上,问道:“你!将你所见所闻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男子身着陆府家服,始终低着头,脊背微微颤抖,连同这声音竟也有些发颤,“回皇上,小人听见书房有响动,进去时便瞧见……”男子说着朝自己怒目而视的端王瞥了一眼,声音弱了几分,“瞧见王爷正在书架后石室口与五殿下争辩……”
“血口喷人!父皇!简直是血口喷人,平日里本王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诬陷于本王!”端王面色铁青,朝着身旁的很怒道。
“逆子!住口!”皇上满脸黑线,小小家丁,定然不会在朝堂上公然说谎,去指证于端王,若不是事情属实,怕是这家丁也不可能编出这等荒唐之事来,继而问道:“端王与五皇子在争辩何事?后来又如何了?”
“回皇上,小人进去时端王爷与五殿下已争论完,小人只听见五殿下说了一句让端王爷收手之类的话……便瞧见……瞧见……瞧见端王伸手一把将五殿下推入石室,并关上了石室的门……”
“那石室中的烟雾是从何而来?”皇上步步紧逼,诘问道。
“小人不知,小人瞧见这一幕,随后五殿下身边随着的下人便被王爷杀了,小人担心之余,便退了出来,之后,书房便失火了。”男子汗珠已渗满了额头,舌头也逐渐打结,将头埋得很低,他身旁的可是南安朝的端王爷,头顶乃是南安的天子,倘若一个不留意,自己定然是人头不保。
端王跪着的身体已然后倾,他怎地未察觉到那时屋中还有旁人的气息,本来事情天衣无缝,未想到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个这样的下人,今日一早天还未亮,宫中便派人传话来,未想到一上朝竟然就是这副模样。
“皇上!”李博良见朝臣底下议论纷纷,苍老的面容颇有些担忧,便自群臣之中站了出来,拱手说道:“臣以为,此事还有待彻查。端王平日里性子温和,待几位皇子都甚是和蔼,今日怎能听信一人之言,定端王的罪呢?”
端王闻言朝李大人投去感激的目光,未想到这种关键时刻,竟还只有李大人为他说话,想来平日里多多走动,并无坏处。
建宁帝花白的眉头微微舒展开了一些,但仍旧冷着声说道:“如今人证物证皆在,莫非还冤枉了他不成?张爱卿怎么看?”
众人将头埋的更深了一些,目光却朝着张丞相往日的位子上瞥了去,窃窃私语之声一时也停止了。
“张爱卿?”建宁帝不耐地朝丞相的位置瞧去,竟是空空如也,往日无论如何丞相定然是第一个到朝里的,今日却提也未提就未到,果真是胆子大了么?他今日一早便被端王之事气昏了头,也未曾细细查探。
“张爱卿呢?”
众人再次无言,却见李博良再次拱手说道:“回皇上,丞相大人今日一早便未来朝中,众臣俱不知晓是何由。”
似是火上浇油一般,建宁帝“腾”地一下便起了身,怒容朝着众人说道:“宣丞相入宫!即便是病了朕也要瞧见他的人!”
端王垂下了头,眼神迷离,嘴角却一抹邪笑,此事瞧来怎么都不像是意外,若不是睿王陷害,背后便更有厉害之人。他兀地想起那日在茶楼的那一男一女,竟第一次有人趁他毫无防备算计了他。萧弥繁……沉寂了两年,终于是要还击了吗?
殿堂上沉寂良久,终于,御前侍卫匆匆跪地,神色凝重,“末将参见皇上!”
“丞相人呢?”建宁帝板着脸冷声问道。
“皇上,末将方才快马加鞭,赶到丞相府中时发觉府中大门紧闭,好奇之下便强行进入了,岂料府中除了张公子未在,其余人……”侍卫顿了顿,继而说道:“其余人竟全部被杀!”
似是投了一颗火药一般,朝中一时炸开了锅,建宁帝拍手而起,面色甚是寒冷,“什么?”
张丞相与李大人、宁王以及皇上四人的关系亲如兄弟,当初四人曾一同征战天下,只是老年时便宁静了下来,但四人却依旧时而聚首。两年前宁王遭人暗杀,如今已在床上躺了许久,意识也逐渐老去。
今日却听到了张丞相已亡故的消息,皇上怎能不急?端王之事,皇上且先将他软禁在了宫中,那作证的家丁也被送回了府中,丞相一家上下百来十口人,一夕之间,皆化为乌有,景都之中因此事也再次变得草木皆兵。
那作证的下人回了府中时,五皇子院中的几具死尸依旧还在那处,书房所在的那个院子早已成了灰烬,府中的下人一时也散去无数。未过多时,那人便似往常一样提着篮子朝着闹市走去。
转过了几条街,又绕过了几条巷子,男子环顾四周,才入了一家甚是普通的院子,径直朝着破旧的东厢房走去。
敲门声响起,流玉急忙谨慎上前问道:“何人?”
“是我,方买菜回来!”男子语气正常,大大方方地回道。
流玉索性才开了门,见到男子,便急忙将他拉了进来,再朝院外扫视了一遍,轻手关上了门问道:“怎么样?”
男子将篮子扔在一旁,随手便扯下了面上的面具,蹙着眉说道:“事情比你我想的还复杂,萧弥繁昨夜未同我们商量便擅自行动,本以为以此便能让那人失败,谁知今日丞相府被屠,皇上自然是更着急这天大的命案,将此事搁置了。”
“那该如何?”流玉忧心忡忡地问道。
萧肃尧并未言语,瞥了一眼榻上奄奄一息的人,眸底怒火层层,但一张口依旧是愁声,“她,如何了?”
流玉摇了摇头,“靠谷主那丹药勉强还能留住一口气,石室中浓烟有毒,弥繁又待的太久,自然……”
“明日便回药谷!”萧肃尧不耐烦地打断了流玉,不知为何,瞧见萧弥繁那副模样他甚是焦灼,这些天来,他二人相处甚是轻松,他倒真将她当做亲妹妹来对待,如今瞧见她这副模样,又恨又急。
流玉微微一愣,“若是回谷中我们之前的努力便功亏一篑了!”
“那我也不管,我不能眼睁睁瞧着萧弥繁死啊!”萧肃尧激烈地说道。
流玉眸底水雾缭绕,垂下了头,不再言语,这么久萧肃尧还从未凶过自己,果真弥繁在他心中分量重上一些。
萧肃尧见状,愁上眉头,起身拉着她的手,柔声道:“流玉,我们三人这般久了,弥繁是我的妹妹,我不能看着她死啊,你能理解我么?”
流玉眼中噙满了泪水,点了点头,随即才说道:“不过,昨夜之事太过蹊跷,你可曾察觉?”
“嗯?”
“为何会有人替弥繁送信说自己去了五皇子府中,你到时为何又正好瞧见有人鬼鬼祟祟去书房,入门为何又正好瞧见了五皇子与端王言辞激烈?还有……端王匆匆离去,你入了石室救了弥繁与五皇子,为何出来时唯独书房着了火?按理来说,端王的确是离开了,带来的手下也惨死石室,为何最后还是有人纵火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