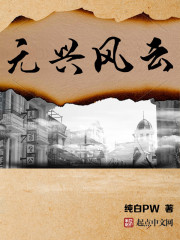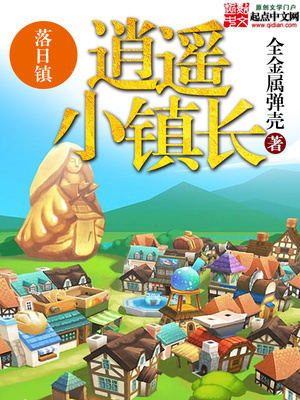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我追着妮可跑了过去。
“那、那个……呃……啊……福——福欧——福欧沃斯乃压!”
我的天!我在说什么!
新年快乐?今天都7号了!还拜个哪门子的年啊!
妮可听见我的声音之后,惊讶的转过头来。她疑惑的歪了歪头,然后转过身来,微笑着对我说:“福欧沃斯乃压。”
对话成立了!
我居然能用遮曼尼语和遮曼尼人对话了!我可真了不起!
我还会什么来着?
啊!对!布吾德俄——哥哥,这个刚听过。范安德——朋友,还有就是,依施立比地施!
这句“依施立比地施”,是毕大小姐在逛街的时候教我的。除此以外,她还教了我两句话,一句是“之日特姆”,一句是“挨拉吾右”。“之日特姆”是佛兰斯语,“挨拉吾右”是因格兰德语,这三句话话毕大小姐教了我好多遍,所以我记得非常牢。
我问毕大小姐这三句话是什么意思,毕大小姐没告诉我,只是微红着脸,用略显倔强的口吻对我说,这三句话我只能对她说,不许对别人说。
呵,你说不让我和别人说,我就不和别人说,你以为你是我娘啊?
你不让我和别人说,就说明你心里有鬼。既然心里有鬼,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搞不好是骗我,让我叫她“主子”之类的,好看我的笑话。
这里现在就有一个遮曼尼人,还是前大小姐。如果我把这句话和她说,她兴许就能把这句话翻译成大先话,这样我不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吗?
“妮可,麻烦你帮忙翻译一下,依施立比地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诶?!”
在听了我的话之后,妮可便像石雕一般定住了。
啊,忘了。妮可的大先话很不好,我把话说的这么复杂,她很可能听不明白。
“呃,我是说,依施立比地施,你,翻译,翻译一下!”
我指了指妮可,又指了指我,将两只手放在胸前,伸出食指和中指,相绕着转了几圈。
“依施立比地施,翻译!”
“啊、啊……依施……依依依依依依施……”
在这之后,妮可便涨红了脸,说话结巴起来。我见到她这个样子,觉得这“依施立比地施”多半不是什么好话。听毕大小姐说,西方人有很多会好几种语言,妮可曾经是大小姐,说不定会说佛兰斯语和因格兰德语。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又对她说了“之日特姆”和“挨拉吾右”。不想在听了我的话之后,妮可的脸变得更红了。她小声嘀咕了几句外国话,也许是遮曼尼语,又也许是其他语言,反正我一句也没听懂。
“我……我,我要……想……想一想……”
在我一头雾水的时候,她用硬邦邦的大先话这样说道。
呃,想一想……
她是想该如何把这三个词翻译成大先话啊,还是想该不该把这三个词翻译过来啊?再者就是,这三个词都不太常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算了,还是别难为人了。
仔细一想,我这先是盯着人家的胸和屁股看,然后就屁颠屁颠的追上来,目的肯定不纯!虽说脑子里没有明确的想法,但骨子里肯定是想做坏事的。
枪理啊枪理,瞅瞅你这出息!
吃不到大姐姐,就来打遮曼尼小妹妹的主意,真不害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先是用刚学的遮曼尼语套近乎,然后帮人家付钱买东西,继续拉近关系,最后趁机去人家家里——你是知道的,约瑟夫不在家,他娘在遮曼尼人的大户人家做佣人,白天多半也不在。家里只剩下孤男寡女,你一个脑子不笨、身强力壮的大男人,还摆平不了一个对你有些好感的小女子吗?
呸!你个臭流氓!死去吧你!
在心里骂了自己一通之后,我总算是冷静下来,将刚刚成形的龌龊念头赶出了脑海。
妈蛋的!我什么时候变成这种人了?
可恶……都是筑瑛的错!!!
如果她不撩我,让我憋了一身的火,我能变成这个样子吗!
不行……一想到她,火就有点压不住了……得找个地方自己解决一下……
“啊……那个……没关系!妮可!没关系!你去买菜吧!买菜!做饭!我回去了!回去!那边!军营!再见!”
我连说带比划,不等妮可做出回应,我就逃一样的离开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军官宿舍,回到自己的房间。在这之后发生的事,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天我没去街里,也没回家。因为心还没有静下来,我不敢再出军营,免得一看见女人就有反应。
相比之下,满是男人的军营就安全了许多。我在军营里呆了一整天,上午的时候是和团里的几个苦力军官一起打牌,下午和士兵们一起踢了一场球,过的非常充实。
晚上五点左右,毕家派人来找我,说水产已经全部送到。也就是说,军火已经全部运到指定地点,明天我就要去各团付款了。
为了保险起见,晚上我又把要付的款子点了一遍。然后我便出了军营,到常胜街的文具店买了些包装纸和礼盒,又买了去商店买了些零碎东西。我将款子用包装纸包好,和零碎东西一起放进礼盒里,在礼盒上做了只有我能看懂的标记,以免给错。
当天晚上,我就去了316团,把他们那份款子付了。第二天,我叫上老农,让他拎着礼盒跟我出去。他不知道礼盒里装着什么,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每次快到一个驻地的时候,我就把礼盒都给他,让他留在外面等着。
进去送款子的时候,我会拎着所有要送的礼盒。如果收款的人问其他礼盒是怎么回事,我就说本来我是想直接带现金来的,后来有人让我帮忙往这边捎东西,我就灵机一动,改用礼盒装钱来了。
我和老农跑了一个上午,把钱都付清了。老农以为又是团长让我跑腿,走路的时候骂了团长不知道多少回。我也不好解释,只能任凭他骂。等完事,请他吃顿好的,酒喝足,让他在回军营的路上再骂一会儿。等他骂够了,就消气了,第二天就不记得这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