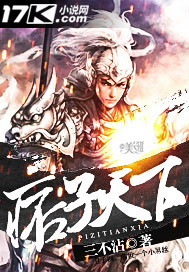从麦琪离开到现在,我见过她三次。
我叫苏紫,在麦琪的故事里,我只是一个旁白,一个忠实的听众,又或者只是一双沉默的耳朵。
她辞职的那一天,我突然觉得很难受。我对她说,真想他朝梦醒,就垂垂暮年,终于不用唱戏给人看。一米阳光,一尺书桌,一床软塌,名正言顺地唱自己心仪的曲名。虞美人也罢,水调歌头也好,千金难买心头好,荒腔走板,总好过鸭子上架。人多奇怪,稍有困倦疲意,心就怯了。一怯到底,把头埋进沙堆,舍不得看外面的刀光剑影,蝼蚁竞血。
她只是淡然地对我笑笑,没有答案。不知道她是因为累了,还是真的盲着眼数春秋。
再后来,我们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我知道她依然是一个人,又或者旁边还有着别人,但都不重要了。她有时候会打来电话,十句有八句里都是那只叫小妖的猫,想来那个男人她真的不想再等了,我宁愿是这样,但又觉得应该不只是那样。
2008年5月12日。滨城沦为一座伤城。
我从灾区采访回来的路上,恰巧路过她的公寓楼下。我给她打电话,原以为在那密密麻麻的帐篷里能搜索到她的身影,可她在电话里说,“你走到小区里来,往上看。”
我从未去过她的公寓,可是一抬头,漆黑的一片里只有一扇窗户里亮着一盏孤灯。这个女人,连死亡都不怕了,还能怕什么呢?
然后我在窗户的投影里看见了另外一个身影,终于我挂掉了电话,折身而去。再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了吧?即使是死亡。
这座城市,似乎在改变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变。生活依旧在继续,而麦琪,我,还有我们中的其他人,就在这座不大的城市里,穿梭着,各自忙碌着各自的忙碌,擦身,然后陌路。
我明白,她依旧独立,自持,冷静。而至于那个人,到底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再后来,便是最近的一次见面了。
她突然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告诉我她正在产房,一边生着孩子,一边拿手机给我发短信,“官方消息,女孩,6斤2两,母女健康。”
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修炼成精,得道升仙,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生孩子,然后再淡淡地告诉你,母女平安。你有再多的疑问都只能生生地逼回去。
去医院看她的时候,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请来的看护刚出去了。孩子躺在旁边的小床上,安静地睡着,新鲜的婴儿,脸上还有些皱纹和蜕皮,可是眉目清晰,跟她的母亲一脉相承。
我没有看见她的父亲,但也没有多问。虽然可以臆想出若干种结局。
“辛苦吗?”
她摇了摇头。
“以后打算做什么?”
“带孩子,当移动奶瓶。”
然后我俩相视而笑。从头到尾,她都没有提过那个男人的名字。
护士走了进来,催促着她跟孩子要量体温了,我告辞,临走的时候我看着她小心翼翼抱着孩子的样子,真好,真的,很好。
女孩,女人,母亲,我们的一生不都是这样的么?
再绚烂的玫瑰,也会成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