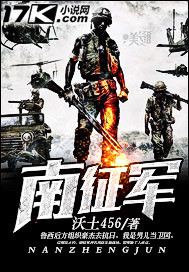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下乡的村里看公社宣传队的演出。那时候,精神生活极度贫乏,逢到演出村里万人空巷,男女老少,携老扶幼,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我特别欣赏兰平的“骑兵舞”,在快乐的音乐中,女“骑兵”纵马扬鞭,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马蹄声声,铃声清脆中,突然一声萧萧的马嘶,烈马受惊。
兰平双手挽缰,右腿高高地挑起,身体后仰,几乎从“马”上跌落。我吓得心里停了一拍,全场紧张得沉默了两秒钟,当兰平重新稳住了身体时,全场忽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和“暴风雪”的搏斗时,兰平常常连续翻几个既轻柔又潇洒的跟头,佩服得我忍不住大声叫好,全场又爆以潮水似的掌声。
在女生独唱中,兰平一曲“北京的金山上”,那甜甜的,圆润的歌喉,就像一股春风,从雪原上轻轻飘过,引得台下欢声雷动,惹得多少个青年爱心萌动。
知青一个个的少了,调走的调走,回家住的回家住。白天干活,能和社员们说话解闷儿,可一到晚上,和我做伴的只有梁上地下乱跑乱蹿咬得木头“咯吱咯吱”乱响的老鼠;土坯墙缝中,艰难地挺起头,窸窸窣窣地抖动着舌信子的长蛇;院子里,懒散地迈动着人手样的爪子,四处寻觅瓜皮的刺猬和院子里拖着美丽的长尾巴,抽答着鼻子,四处嗅寻鸡味的狐狸。
猫叫春时,墙头上来回乱跑,发出婴儿似的啼叫,我常常怀疑,谁的孩子,放到了墙头上。心里感到寂寞、恐惧,常常一到天黑,就莫名其妙地害怕起离村子有一段距离的知青屋。
我也是人,需要和人交谈,需要伙伴,哪怕打架也比寂寞好。
一天晚上,我好不容易又听到宣传队要到小吴庄演出,晚饭也顾不上吃,慌里慌张地赶到了小吴庄,可到那里一看,什么也没有,原来听了谎信,宣传队并没来。肚子饿了,到了村里的小饭店花了三角钱买了一份炖鱼,又要了两碗老烧酒,两个馒头,连吃带喝,一根根鱼刺,片状的鱼头,也被我格嘣格嘣地咀嚼干净,连吃带喝,倒也晕晕乎乎,十分痛快。
回家的路上,一步三摇,专插小路走。青蛙凸着雪白的肚皮,脖子上的气囊一鼓一缩地在“呱――呱――”吊嗓,黄褐色的纺织娘不知疲倦地发出纺棉花似的“嘤――嘤――”低吟,幽暗中的夜莺瞪着圆圆的小眼睛清脆尖声地歌唱,就连无有生命的树叶都“哗啦哗啦”的齐声鸣唱。
耳中听到飞机的轰响,抬头仰望,万颗璀璨的星星组成了一条壮丽、宏伟的银河横贯天际,每一颗星星都是鲜活的生命,忽暗忽亮,忽然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燃烧着最后的光明殒落。哪有什么飞机?
肚中开始隐隐作痛,好像一只蟋蟀蹦进了肚子里,然后迅速繁殖,化做无数的小虫乱蹦乱撞,撞得我想吐,起拉,站立不稳,想摔跟头。坏了,心里还算明白,这不是个好事,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处荒僻,万一趴在地上,死了连个送信的也没有。
心里这么想,自己可就管不住自己了,裤子还没来得及脱,一股污物从下排出,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发觉我已躺在了自己的床上,身上穿着干净的裤褂,盖着又薄又软的花被,花被不是我的。屋外,**点钟炽热的阳光刺透乌云,绚丽的霞光洒满全院,铁丝绳上晾着我的几件干净衣服和拆洗过的被子、褥子。
尖嘴、长尾,穿着白坎肩的黑喜鹊站在房檐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棕褐色、花斑纹背的画眉扬着头和地上觅食的几只黄麻雀婉转地唱和着。阴凉地里,一个衣着俭朴的农村少女正在低着头洗着衣裳,两只手一揉一搓,却也显示出舞蹈演员的优美韵味,面目清丽,虽没有故意表演,却已流露出演员的柔情万分。
这不是兰平吗?我心里突然撞击出蓝色的火花,火花开始燃烧,燃烧使全身发热,我坐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警觉的兰平见我醒了,甩了甩手上的水,进了屋急忙按下我:“别起来。医生来过了,说你这是急性食物中毒,已经打进针,灌过药了。要说昨天也真玄,我和小玲从县里开会回来,看到半路上躺着一个人,浑身臭烘烘的,吓了我俩个半死。我多了个心眼,一看是你,原来是我队的知青啊,就把你背回来,让小玲去喊大夫……”
我慢慢想起昨晚上的事,怪都怪那便宜的鱼,两碗酒,惹了这么大个麻烦的事儿。她说的真轻巧,和做游戏一样。想着想着,就想到了衣服,我顿时感到大事不妙,惶惶地问:“我……这衣服?”
兰平脸红了,扭过脸羞涩地说:“你当时那样子,总不能让你在屎尿中泡着。有人问,就说你自己换的,都说城市人开放,我看挺封建。”
我默默地想,这是在农村,一男一女在一块儿,那都要招来不少闲话,更不用说自己在她面前“暴露”无移了。一个农村姑娘,突破这个禁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她这颗纯洁无瑕的心灵,重重地撞击着我感情的琴弦,使我的心里默默地升起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愫。这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好姑娘。
“要说,你也真有福,怎么这么巧,让我碰上了。大夫说,食物中毒要是治晚了,要死人的。昨晚上,我俩要是真不从那里走,说不定要出大事哩……”
我也略懂医学,有毒的食物和酒一掺,毒药加麻醉,再进入空着的肚子,血里吸收很快,并随着血,向全身扩散,如不及时治疗,很快会使人死亡。是兰平救了我这条不值钱的命啊!
“这会儿你清醒了,鸡汤自己喝吧,我就不灌你了。大夫说,泻得太多了,多喝点汤,免得脱水。”兰平说着,端过来一碗热气腾腾上面漂浮着葱花、姜片,香味一直沁入心脾的鸡汤。我颤颤巍巍地端过了这只碗。
下乡三年了,哪里有鸡汤让我喝?心里寂寞,有谁对我有过心灵的抚慰?救命之恩,涓涓柔情,何以能报?“这只鸡,挺贵的吧?”“什么贵不贵,我的家我当家。”“我以后可是没钱还你啊!”“看你说的傻话,我知道知青都没钱,我又不是图你以后还钱!”
我无话可说了,对于这个农村姑娘,又超脱于一般的农村姑娘,我再也无法表示我的感谢之意,我突然放下碗,两手死死地抓住兰平的手,恍恍惚惚地说:“你……太好了,我……我……我……”
兰平颤动了一下,好久好久,慢慢地推开我的手,佯作镇静地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是个知青,以后有前途,我……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姑娘,还有一个不好的家庭,我和你……”她痛苦地摇了摇头。
从此我觉得,有一根爱情的红线,已经悄悄地把我俩紧紧地拴在一起,再也难以分离。
然而有一天早晨,兰平突然到我们社员中来干活,从此再也不去了宣传队。她的容貌使我大吃一惊,面无血色,满脸憔悴,双目呆滞,布满了泪痕,好象一下子长了二十岁。见了我,她垂下了眼睑,低下了头,身体在微风中瑟瑟发抖,好像稍微大一点儿的风,就能把她吹倒。
我呆住了!
几个娘们在她身后指指划划,嘀嘀咕咕,还不时互相投过一种既神秘又幸灾乐祸的眼神。几天的活都是拉土填沟,平整土地,两个人一辆车,他们就像商量好的一样,一窝蜂似地挤在一起,独把兰平孤零零地抛在了一边。
她就像一棵无依无靠的小树,失去了树林的庇护,随时都可能倒下。兰平还能干活吗?我拉着空车靠近了她。
兰平瞥了我一眼,那眼光不知是凄凉还是感激。我拉着车,绝不让她使一点儿劲,看那样子,她再也经不住一点儿折腾了,脆弱得随时可以折断。可她又偏爱逞能,倔强地摇摇晃晃地豁着命地使劲!她准是疯了。
到了没人的地方,我着急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在宣传队上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到这里来下这个力。病的这么厉害,还来干活?”她仿佛没听见,闭上眼睛,喘气更加粗重,脸色更加可怕。
“你这是怎么了?”我又问。她突然像一头发怒的母豹咆哮起来:“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没敢再问下去,是不是她的哪一根神经出现了问题。
有一会儿,女人们津津乐道的话语随着一阵风刮进了我的耳朵里。“兰平流产了,我一猜就是他。”“那天晚上,你不知道……”“还是他俩近哪。”“还是个知青哪,呸,不要脸!”
偷听着她们的谈话,再看看兰平现在这个样子,越想越害怕,似乎有一根铁棒在我头上重重地猛击一下,“嗡――”地一声,头剧烈地疼痛起来。兰平原来是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光芒四射,现在一阵风刮过,瞬间污秽不堪了。
一股怒火在心里熊熊燃烧,是谁这么丧尽天良,践踏了这么一朵纯洁的、美丽的、盛开的牡丹花,也使我的心里遭受一次难以痊愈的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