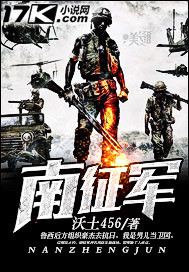一
1973年,我有幸替补别人当了一名疏通漳卫运河的河工,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艰难也是最有收获最有意义的时期。当河工的体验,不仅为我以后的体力与精神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底气,而且亲眼目睹了兰平兰明姐弟俩的厄运,就像刻刀在我的脑海里雕刻了一个清晰的世界,将影响到我一生怎样去认识人,怎样去善待好人!
我刚到漳卫运河的时候,看到干涸的河床上不知什么时候凸起了一个个沙丘,像无数的坟冢,不断地散发着死亡的臭气。两边无坡无壁,模模糊糊的褶皱,像是腐烂的尸骨沤没了轮廓。没有了生命的气息,没有了斑烂的色彩,没有了山水的灵气,只有狂风在这横宽五里,纵长几百里的河谷地带横行恣肆,不断卷起漫天黄沙,纷纷扬扬,混混沌沌,南扫北荡,遮天蔽日。
我手搭凉棚,茫然眺望,风沙遮暗了阳光,遍地黄土,满目苍凉,就连生命力那么旺盛的茅草,也枯黄着身子,有气无力地在寒风中发出梦魇似的*,迟迟不愿意苏醒,耐旱力极强的马齿苋,也死死地赖在土窝里,死活不愿见世面,更不用说别的娇嫩的花草了。没有村庄,没有村民,连耐忍饥寒的野兔也早已逃遁,似乎在这块土地上,只有和沙土粘成一个颜色的河工。
河工住的是阴阳屋,在地下挖一个穴,连土炕和油灯座都挖得规规矩矩,上面搭上一个架子,盖上塑料布,铺上薄土,里面冬暖夏凉,比那村民的大北屋还舒服。逢到大风天,把洞口一封,简直成了世外桃源。
和我同拉一辆地排车的,就是兰明。他也就有一米六五吧,身体瘦得像个小干鸡,小黑脸,尖下巴,又短又黑的眉毛,当中断断续续的,那是为了他的那头宝贝牛,让一头老母牛给踢的。一双大眼睛本来挺有精神,可一见了人总像欠了谁什么东西,乞求别人原谅似的。
他常常默默地呆在一旁愣神儿,不由自主地唉声叹气。他爸爸原是个国民党连长,听说曾抱着一挺机关枪打死过不少日本鬼子,当然也打死过解放军,后来在济南战役中随着吴化文的部队起义。
前几年红卫兵没把他折腾死,倒是他自己气性大,离家远远的,跳河自杀了。等捞上来时,浑身肿得像个大馒头,一块块往下掉肉。兰明他妈从此就疯了,白天黑夜在野地里乱跑,一遍遍地呼唤着丈夫的名字,失魂落魂的姐弟俩一下子没看住,兰明他妈掉到井里淹死了……
兰明挺聪明,学习也不错,可是说什么也不上学了,竟然跑到生产队里去喂牛。兰平去拉他,说:“弟弟呀,你真没出息,好好的书不念,为什么去喂牛?”兰明神态木然,干脆把铺盖也搬到了牛棚里,不回家了。
兰平哭了,一边哭着一边打兰明:“你真没出息,真没出息呀!我可怎么办呀,我可怎么管你呀!”打着打着,抱着弟弟的头失声痛哭,兰明麻木的神经一下子被组组的温情化解了,成串的眼泪往下淌,抽噎着说:“姐呀,我怎么能有……心去念书,这……个书还有什么念头。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
姐姐哭完了又打:“我那傻……弟弟呀,没文化……以后可怎么办哪!我可怎么……管你呀!还指望谁管……你呀!”打完了又哭,哭完了又打,兰明也搂着姐姐哭……
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枯萎了又萌发,叶绿了又遭霜打,瓜依瓜苦苦挣扎。五年了,兰明今年已经18岁了,他伺候牲口也有五年的历史了。他喂的牲口,个个肥肥壮壮,油光水滑,干干净净,社员见了都夸奖。这回上河,他还带来了一头小牛犊,活蹦乱跳的。
一见到牛,兰明的眼睛就亮了,说不完的知心话,有空就伺候它,就像对他的亲兄弟似的。
在兰明面前,我几乎比他高出一头,身子也宽出一大截,本来该我驾辕,可兰明早把辕绳往脖子上一挂,两手抓住两个车把,占住辕位了。他还以一个老河工的口吻对我说:“生哥,你现在恐怕最难熬了。这河上是枣核活,两头松,中间紧,先上来松点,是为了先活动一下筋骨,最后松点,是因为活快干完了好放松一下回家。现在你的腿脚还没有活动开,却要干最累的活儿……这么着吧,你干活悠着点就是,我多使点劲就是了。”
我轻蔑地对他一笑:“你就瞧好吧,我还能不如你!”
驾辕和拉套还是有区别的,拉套只是一种辅助的工作良心买卖,多使点儿劲车就快一点儿,少使点儿劲儿车就慢一点儿,就是一点劲也不使还有驾辕的,驾辕可是一车的主宰,他要是不使劲儿,车是一步也动不了。
到了河底,老茂一个眼色,装车的河工,早已砸开了冰冻层,把河泥切成一块块“豆腐干”,每块七八十斤,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把车装满。我正要拉着架子使劲,兰明对老茂说:“茂哥,再装点,别人装多少,俺装多少。”
我这才注意到,我的车确实比别的车装得少点。我对兰明一瞪眼,是不是他脑子有点儿毛病。老茂也对兰明说:“你不是有点儿病吗!”“行,还行!”兰明又让几个河工给装了几锨土。我看了看兰明,发现他的脸色确实有些灰暗。
我俩咬着牙,瞪着眼,别人帮着,一吆喝,冲上了小河坝。然后,顺着早已碾出的三指多深的车辙,跌跌撞撞地往前拉。一拉上车,汗水就像才从锅炉里加过温似的,翻腾着热气腾腾地涌出体外,和寒冷的空气撞击,冷却、挥发。
汗干涸了,匆匆忙忙的从路旁水桶里,舀出一碗水,撒一半,喝一半地灌进嘴里,咕噜咕噜,扔下碗紧跑几步,又撵上了前面的车队。脸上身上永远是黏黏糊糊,汗粘黄土,黄土吸汗,汗土越粘越厚。
好不容易二里半地,才到大坝。大坝是四十五度的斜坡,约五十米。一辆车是上不去大坝的,我们三辆车组成一组,互相协作。先是运气,六个人先把刚才路上大口大口的粗气喘匀,又深深地吸了两次大气,才互相看一下,点点头,意思是可以上坡了。
有一个人,一声发喊,六个人像疯了一样,豁上命地往前扑。前头拉套的,头几乎拱着地,手脚并用;四个赶车的,腿上青筋暴突,脖子也快从腔子里拔了出来;驾辕的两腿撑开,八字脚,撅腚挺胸下死力驾着车,借着后面的推力往上抬,要是一不小心,被重重的车子压垮,那就麻烦了。
车子是连拉带抬,上来了大坝,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眼睛发黑,腿都找不到了感觉,直想瘫。
卸车倒是省事,车头一转,尾巴朝前,几个人把车冲起速来,朝土堆上猛一撞,黄土利用惯性狂撒出去,犹如“疾风暴雨”,剩下没多少土,驾辕的把车往后一抽,手脖子一抖一拉,只几下,车上的土便被颠得干干净净,真象“天女散花”。
直到这时,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可是来不及在凛冽的寒风中擦一下单褂上热热的汗水,一溜小跑,又是下一个轮回。一趟来回五里地,一天二十多趟。
人,如果一干活就觉得累,那将是越干越累,如果一搭手就觉得撑不了,那将是一场灾难!我自认为在农村磨炼三年,耕锄耙割,样样精通,百般劳累,毫无畏惧,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青年农民了。没想到一上河,就觉得河上的活绝不是一般的累,竟然一天下来,两腿发软,两天下来,脚就像踩了棉花套子,怎么也抬不起来。
以后回想起来,那就是河上的活一会儿也不让你闲着,就拿着河工当一个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使。我也曾怀疑兰明不使劲,也可能是驾辕不累,到了河底装车时,我抢过去驾辕。车子动起来后,觉得自己的腿脚更沉重了,不使上十分的力气,车子是走不快的,离前面的人越拉越远。只要是和车队一拉下,那就意味着被抛弃,这辆车就别想再爬上大坝。再看看兰明呢,上身往前探得大大的,套绳拉得笔直,脸色更加灰暗了。
半路上,一头小公牛见了兰明,“哞——哞——”地叫了起来,它好像也在为身体虚弱的主人感到不安,粗粗的颤音里,饱含着对主人的关注与痛惜,三甩两摇的,挣脱了拴缰绳的石头,一溜碎步跟在了我们车后。
兰明对它挥了挥手,喊着:“回去!没你的事儿。”它却跟得更紧了,并且圆鼓鼓的肚子亲昵地在兰明身上蹭来蹭去,头也晃,尾巴也摇,跳起了快乐的“摇摆舞”。兰明高高地举起手,轻轻地落下,半嗔半怨地嘟哝:“你看你,这么淘气,真拿你没办法!”
要说它也怪可怜的,一生下来,母牛就难产死了。为了能养活它,兰明打听到三里外邻村有一头母牛也生了头小牛,兰明给那个饲养员送了二斤点心,就赶着这头小牛去喂奶。不料,那头母牛又踢又用角抵,把兰明的眉都给踢破了。
兰明就把那头母牛的眼睛蒙上,给那头母牛理顺着毛,这才给小牛喂上了奶。日复一日,一个柔弱的少年含辛茹苦地照料着一个比他更加弱小的小牛。别看这头小牛其貌不扬,毛有些杂,又黑又黄的,长出的一对小角角,也不顺溜,一个直一个弯,但这些丝毫影响不了人与牛之间感情的交流。
牛通人性,人牛同命,天长日久,兰明已把它看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