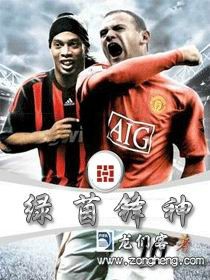() 尽管以“回忆”的方式三篇收笔,而那种乌托邦式的灵感依然循环在血液中,使我迟迟不舍其人、其事、其景,毕竟那是一种感情的全神贯注,又有近似完美的过程,那种快慰是别人无法享受的,终于忍不住,又开了闸,这一回,也许很难随便收笔了,力求以一种现实态度去描摹,但仍不想有矛盾在里面,更不想将周遭的庸俗流进去,相信依旧会很纯净。
北疆的鸿雁传书不断,经不住一再邀请,我终于又踏上了往昔的旅程,夏季里昼长梦短,不几rì,我便来到了那座换了绿装的山脚下,接我的是那个可爱的通讯员,他在付出了极大代价的情况下,转成了志愿兵,在一次训练中,他的左臂严重骨折,部队怜惜这个孤儿,便由营长四处奔波,终于办下了伤残证,并转了志愿兵。他依旧是沉默的,成熟了许多,个子长了些,唇上挂了一层淡淡的黑须,笑起来还是那么憨厚、诚恳。
他是被营长派到镇上特意接我的,顺便给营里采购些东西,一接到电话,当天下午就搭顺车赶过来,和我在旅馆挤了一夜,实际上是谝了一夜,很走运,一辆送机械的军用卡车被他联系上了,二人便提着沉重的行李上了车,他笑着问我:“叔叔,你都带啥好东西了?这么重。”我笑而不答,留一份惊喜调他的胃口。看到他微屈的残臂,我不禁有些心寒,问他:“娃呀,疼不疼?”他憨厚地摇摇头:“早好了,都几年了,只是没劲。”我不再问了,话题转到了他的战友们身上,他告诉我,文书考上了军校,教导员转业了,现在惟有的几个熟人便是新派来的连长,也就是团里的那个干事,再有,就是我的西安老乡已提成排长。我深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能有几个故人相留,已是上苍的无限恩赐了,这几年,事多信少,情况大不相同是情理之中的事,当过兵,就自然很理解了。
车子在高大的白杨夹道的宽阔马路上行驶了约三个时,终于在坎儿井处拐上了土路,一片胡杨林,将坎儿井伪装的荫凉、神秘、原始,偶尔有明渠显露,清澈的渠水反shè出金sè的光芒刺得人眼疼。在一棵巨大的古杏树下,一位维族老汉静坐在阔叶笼罩的树yīn里,他背后是一堆让人望而垂涎的大西瓜,面前的木桌上摆着切开的鲜红的沙瓤黑籽瓜,车到了老人近处开得很慢,怕扬起尘土弄脏了西瓜,我闻到了在关中不可能闻到的浓郁的清香,整个五脏都被香气穿透了。兵向老人打着招呼:“爷爷,您好!生意怎么样?”老汉笑眯眯地摇摇手中的扇子:“借部队的光,生意很好!孩子,下来尝尝爷爷的新瓜?这可是开圆的第一缕香甜啊!”。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来时碰上的维族老汉,会不会是他呢?我问兵,他摇摇头:”那老爹早被儿子接到乌市去享福了!都九十多岁的人了。”他又转向卖瓜的老人:“爷爷,您的瓜闻上一闻就让人心满意足了!”老人连忙抱了个大个的要递上车,我也连忙摆手:“大叔,谢谢您的热情,就让您的瓜在这里多香醉几个人吧!”车缓缓地向营房开去,老人怀抱着西瓜,善意地笑着摇摇头,无奈地又将瓜放回,然后又坐在他碧绿的天棚下悠闲地摇起扇子来。
终于,那两堵是砌成的墙出现在我眼前,我血沸腾了,墙根下,是蓬乱的杂草,其间开着各sè野花,没想到满天星会漫到这里!血红的、紫sè的、粉sè的、白sè的,交织在一起,在阳光下,随着微风轻柔地舞动着纤细的腰枝,有头重脚轻,一一,仿佛在向我鞠躬行礼;门前那两棵高大的松树周围,也长着许多野花,高大的木芙蓉抢了满天星的风头,它们挺拔、玉立,使我猛然间在脑海里迅速闪现出伊犁河畔的木屋来,记忆中的严寒荒漠图一下荡然无存,铁桶哨楼里的士兵走出来,英气勃勃地向军车行军礼,这个正当年华的jīng干士兵,被高原的紫外线涂成了黝黑的面孔,和那两棵巨松十分相称,他向兵打着招呼:“后勤部长,采购齐了?”然后又很有礼貌地对我头,兵顽皮地只对他傻笑,我们犹如闯入了一座野外别墅,车在*场上停下来,司机帮我们将行李卸下来,我们道了谢,车便想库房方向开去。
兵向营长的屋子大喊:“营长,人来了!”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兵应承着,从另一间屋里跑出来,这显然是一个城市兵,眉目间透着几分顽皮,有象我当年刚入伍时的样子,他告诉我们:“营长到后山去了,他们不好好训练,在那里胡闹,排长没办法,下来搬救兵。”他很殷勤地帮我提行李,似乎早就认识我:“盛老师,我们营长常提起您,没想到您长得这么年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嘴上抹了蜜的兵,同时也想通了一件事:当初新兵连连长为什么那么喜欢我。我问他:“你是通讯员吧?怎么这么就当兵?”他挠挠头笑着答到:“我是后门兵,和您当时一样大。”。
我感到奇怪:“怎么,你们营长总揭我的老底?”他诡秘地笑了,到了营长屋前,他顽皮地伸手弯腰:“大人请!”我便推门而入,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就见一只巨大的花环仿佛从天而降地套在了我的脖子上,我假装生气:“是谁恶作剧?敢拿你们营长开玩笑?”两个家伙只笑不答,兵帮我放好行李,提着水壶对我:“叔叔,你先坐,我去打水。”通讯员连忙抢过壶:“算了吧,谁敢劳你后勤部长的大驾?营长知道了,我就死定了!”他又一脸赖象地问我:“您呢,叔叔?”一张甜嘴足以麻倒一大片,我便分配起来:“你们一个去打水,一个去叫营长,公平合理!”。
通讯员提着壶顽皮地立正行了个军礼:“是!叔叔大人!”然后破门飞了出去,而憨厚的兵却慢慢推开了房门,准备去叫营长,刚出门,我听到洪钟般厚重响亮的关中口音:“人来了没有?”兵答着:“早来了,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我戴着花环,不忍摘去,意yù冲出屋去,去被他高大的身影门板似地堵住:“哈,老哥,你真的来啦?!”他兴奋地和我拥抱了,爽朗地发问:“怎么样,见面礼合适吗?”我立刻明白了花环是他导演的,我:“我还以为是娃娃们遭怪呢!原来是老伙子的出手!”兵给他解释着:“准得很,正好套在叔叔的脖子上!”营长爱抚地拍拍他的肩膀:“去,通知灶房,加几个菜,给你叔叔弄瓶伊犁特来!”兵有不太愿意:“酒就免了吧?”他有生气了:“这娃娃,管我也不分时候,快去!”兵仍不挪步:“好营长叔叔哩,我求你别惹事?!”。
我问原因,兵告诉我:“他的肝才做过手术,不能喝酒。”我明白了:“老弟,这可是你的不对了,喝的时候多着呢!”他无奈地头,仍做着努力:“都半年了,早好了,要不你喝着我看着?”我看到他失望的样子,从包里拿出两瓶路上解渴的啤酒:“实在忍不住,咱们喝这个。”兵高兴地望着我:“行行!灶房还有一捆呢,叔叔,你尝尝这儿的啤酒。”他兴奋地跑出去了。
营长和我坐下来,他仔细地端详我:“老兄,你一都没变,还是那么年轻,你要再不来,我都忘了你什么样了。”语气有几分哀伤,我重重地否定他:“哪能那么随便就忘了呢?有的人,天天见,就是记不住;有的人,见一次,就终生不忘,这是缘分啊!”他又兴奋起来:“我真没白教你这位大哥呀!又爽快,又解人心,实在!”二人的旧话,一句不断地续了起来。午饭是在那间食堂里用的,这里被翻新了,地面处理的十分光滑,墙壁上也贴了洁白的瓷片,水磨石的地面上没有油污,十几排整齐的长桌和长椅被固定在上面,战士们不用蹲在地上吃饭了,另外,灶房边上有新盖了一间招待厅,桌椅较为讲究,那是招待上边下来的领导或探亲家属的,我以亲属的身份被让进了招待室。
兵现在管后勤,特意准备了几个下酒菜,一捆啤酒放在墙拐角,营长特意喊来了几个排长做陪,最兴奋的是西安的老乡,他比过去成熟多了,脸上的稚气已全无,他主动承担起跑堂和看酒的工作,七八个人,一捆“天啤”,没有醉人的可能,况且到货都以营长的肝病为由,免提白酒,有一道菜是他们最满意的,那便是我带来的家乡的宴友思系列,熏鸡、熏猪蹄等,一抢而空,不久便是一桌骨头。
午饭后,暑热中烧,在品尝了维族老汉的大西瓜后,我请营长陪我去拍照,他显然已不胜酒力,眯着眼抱歉地:“对不起,老哥,我实在乏得撑不住了,让二连长和一排长陪你,你们文化人在一起,共同语言多一些。”我不便勉强,二连长就是团里下来的那个曾为我录过像的干事,一排长,是我的西安老乡。我深知营房是不能随便拍照的,便提出到后山上走,二人都很赞同我的意见,连长告诉我:“后山可真值得一去,保准你的胶卷不够用!”三人绕过活动楼,战士们都午休了,四周静得出奇,有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在高大的雪松上窜跃鸣叫着,使得山脚下的营区更显出一排安祥,有如世外桃园,又象是香格里拉,又好似二者的有机结合。一迈上后山,迎面一阵凉风拂来,使人本来就没有多少的醉意猛醒,兴奋也突升,我们步履蹒跚地沿着一条绿草掩住的道登上了山。
极目远眺,我被北面远处的峰峦那连绵的雄姿惊呆了,一层比一层绿的伟岸山峰,被镶嵌在白云蓝天下,偶有青山露出身姿,仍被千姿百态的松树盘住,那一层层翠绿,是由近及远的庞大的红松林染就的,眼前山坡上的万紫千红的野花,是这幅巨画的前景,我的广角镜有些不够用,我一退再推,一张接一张地贪娈的拍着,又换上了长交,试图把远处的一切都拍到,连长告诉我:“从那边看这边也是一样的。”这话不无道理,当人进入一种环境,便身在此山不知深了,总以为远处的更好,其实往往最好的就在我们面前,只是意识不到罢了,正如人的贪yù,总觉得别人拥有的比自己多,那种近距离的窥探,使得有的人们迷失了本xìng,忘了自己应该持有的真实态度,对生活,有时应是远距离看,近距离想,走好脚下的路才是最重要的。
我请连长和排长做模特,他们已脱去了上衣,将军装搭在胳膊上,军帽拿在手里,我仰拍了几张,他们在镜头里,俨然两棵最健壮的红松,巍然挺立在山上,和这群山中的林海融为一体,在炽烈的阳光下,脚下是满目的花草,背后是天然的绿sè布景,衬得他们更加高大、威武、英俊、挺拔,高原又将他们造就成憨厚的西北汉子,在他们的目光中,有的只是如山泉般清澈、如苍山般宽阔的屹然神态,少了jiān诈和庸俗,多了忠厚和坚实,他们又仿佛是山石中的一部分,粗壮黝黑的臂膀恰似稳健的山岩中伸展出的巨松,他们和博大的自然早已浑然一体,成为它们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时,连长冲着我背后高声道:“哪儿都少不了你们俩鬼!”我回过头,只见兵和通讯员笑眯眯地站在我身后,我有歉意:“噢,对不起,咋把你们俩给忘了,来来,叔叔给你们拍照赔罪!”两人互相推拖着,连长爱怜地训斥到:“军人嘛,怎么象个大姑娘?不照我们可走了?!”二人立刻蹦到我的镜头前,顽皮、活泼、可爱的形象占满了我的镜头,排长挖苦他们:“真臭美!这么热的天,还捂得这么严实,也不怕发芽!”。
我替二人辩解着:“你们俩壮得象头牛,他们怕腿比不过你们的胳膊!”几个人都笑了,笑声传到了脚下的送林里,兵已站好,并摆好姿势,端端正正地站直了,通讯员摆着手:“不行不行,太死板了!这儿的木头够多了,不少你一棵。”兵有生气了:“那你让我咋弄?”还是当过宣传干事的连长有经验:“你左手插腰,右手扶住军帽,腿做弓箭步,好象刚从山底下上来,这样比较自然。”兵照办了,的确不错,我腹拍了一张,连长为我也拍了几张,然后他介绍到:“咱们下去吧,底下有水,漂亮极了!”
我们随着连长,心谨慎地在山林间穿梭着往山谷里走,一迈进林中,一阵清凉袭来,身上的汗水立刻被封住,好象在巨大的空调前走,只是空气间充满了松油的清香和花草的淡香,顺手摸一把身边的巨石,凉凉的,我嘱咐着前边引路的连长和排长,他们一红一白的背心在林间闪烁着,仿佛流动的目标,我:“你们俩穿上衣服,心着凉!”他们相继答应着,但并未执行,想必他们习惯了。
渐渐的,我和两个家伙被两个连长和排长拉得较远,只能偶尔看见他们鲜艳的背心在闪动,不久,便听见谷底连长在喊:“老大哥!快下来吧!”排长也跟着喊:“大哥!加油啊!”我答应着,身边的两个鬼也答应着:“噢,来了!”终于,我们到了,连长和排长在一条清澈见底的溪间,各占一石,坐下来,脱了鞋和袜子,双脚伸进水里,二人悠闲地抽着烟等我们,我连忙抢拍了几张,溪水从他们脚下分开,又合流,然后欢快地拍击着参差的山石向东流去,我在水里摆着毛巾,对他俩抱怨着:“你们俩子,腿上充了电了?想把老哥哥累死呀?!”他们相视而笑了,连长摆出一付不可侵犯的官架子冲着两个鬼:“刚才你俩是谁占我们便宜了?”通讯员指着兵:“是他!他一听那么喊老哥,就憋足了劲答应。”。
排长显然很了解兵,对着通讯员:“你子最坏,人家比你大,你还老欺负人家,只有你!”我在一旁观虎斗,在我眼里,他们是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我把镜头一次次伸向他们,不久,便换了个新胶卷。连长告诉我:“这水是从天山上流过来的,一部分在坎儿井,一部分从这儿穿过去,一污染都没有。”我捧起一掬渗凉的泉水喝了一口:“有一股雪莲的清香,还有不上的水果味儿!”连长笑了:“老大哥,你的联想力也太丰富了,不愧为作家!”我脸上有发烧:“什么作家!只是忍不住被陶醉了。”排长每次都要把你的信在喇叭里念几段给大家听,他很崇拜你的诗人气质,经常配上音乐在晚会上朗诵,我们都很爱听!”他的话,使我想起了那次令人终生难忘的晚会……
连长借机试探我:“怎么样老大哥,再给我们办一次晚会?”我摇摇头:“不行,我老了,怕激情不足了!”排长把脚从水里抽出来:“会有的!只要你一登场,掌声一响起来,你就会兴奋的!现在这拨新兵更会玩,好大哥,求求你,再展示一次您的风采吧?”通讯员跳了起来:“叔叔,我早就听您的才华了,办一次吧,让我也开开眼!”我:“你们营长会同意吗?”连长抽出脚,边擦边:“他要不同意,就没人同意了,他最想的就是你的那场晚会了,走,回去找他!”几个人被另一内容所左右,急匆匆地往山上走为的是早下到营里找营长商量此事,当重新迈上山时,我无限回恋地望了一眼青山秀水的谷底,一层层绿树挡住了我的视野,兵和通讯员拽住停在那儿的我:“叔叔,快回去吧!我们都等不及了!”我们一路跑着冲下山去。
等回到营房,已是下午近三钟了,营长略带埋怨地对我:“刚来,不好好休息一下。”我抱歉地:“我太兴奋了,控制不住自己!”他从屋里拿出把折叠躺椅撑开:“我的好大哥,快歇歇吧!娃们正当年,劲有的是,累坏你老人家我可担当不起!”。
他拿了把扇子,端了凳子坐在我旁边替我煽着,象侍侯皇上,他问:“咋样,这后山可值得你一看?”我没有躺下,坐在躺椅上仍兴奋不已:“没想到,这里的夏天美到无可奈何的地步!”他有听不懂,连长在一旁解释着:“我们照了足足有两个胶卷,老大哥可真会选景!”我有不好意思:“有你做高参,还能差?!”营长笑了:“你们一大一,两个疯子凑到一起,我可要倒霉了!”他发出爽朗的笑声,排长洗完脸也走过来:“怎么,营长同意了?”营长莫名其妙:“同意什么?”排长认真地:“搞晚会呀!”营长:“亏你想得到,也不让老哥歇歇,想把人累死不成?!”排长强辩着:“你就不怕把我累死?!”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我被这种特殊的气氛挑起了兴趣:“为了弟兄们的盛情,我累死也值得!”。
营长作出了最后决定:“好!后天是星期天,明天准备节目!”连长激动极了:“好!干就干,我派人去采购吃喝,咱们办隆重些!”他高兴地不知该怎么表达,满脸的孩子相,莫名其妙地:“我去洗脚!”我们几个都笑了,营长告诉我:“这子最怕洗脚,只要他一洗脚,那帮猴jīng就能猜出有好事。”我不信,营长:“咱们等会到营房去,看看我哄你没有。”。
这简直有离奇,新鲜的让人难以置信,我喝了杯水,便和营长绕到营房后,在一所营房的窗根儿底下悄悄地停住,他示意我靠近听,就听有人问:“排长,到底有啥好事,求你快嘛!”只听哗哗的洗脚声,又有人:“快别摆谱了,我们都快急爆炸了!”排长答到:“那你们以后还在背地里叫我臭脚大王不了?”几个年轻的声音一同答到:“没人叫你臭脚大王!”排长拿架子到:“那叫什么?”众人齐声道:“叫大哥!”排长满意了:“哎!这还差不多!”。
他故做神秘地压低声音:“我告诉你们吧…”众人都不做声,只听他:“饭后宣布!”众人失望地齐声:“臭脚大王!”然后都跑开了,我和营长都被这特殊的欢乐氛围吸引住了,二人在窗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有人发现了,连忙打开后窗:“后边有人偷听!”营长突然伸直了腰准备逃跑,头嘭的一声撞了一下,他揉着头:“死子,有撞死我呀?!”众人笑着齐声到:“营长!”然后又接着大笑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铺牌了,对于那场晚会的怀念,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是我记忆中一个永不磨灭的光结,正是那次晚会,才使我牵挂至深、至久,来之前,我是做了jīng心准备的,但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我是不便主动提出的,部队毕竟是不同于地方。现在,一切都如愿有了开头,那么,积极准备是我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我是个不愿做重复的人,任何一件相类似的事,都要有两种不同的效果,至少,过程应一次比一次更圆熟。
晚饭后,我将十几张故事片VD光碟交给了兵,他兴高采烈地去四处通知今晚有新片看;营长则一再稳住我,让我休息好,仿佛明天要上阵指挥一场大战似的。饭,要专人送来;洗脸水,要人打来;连我的袜子也被兵抢去洗了,他拎着我的袜子:“又一个臭脚大王!”我顺从地享受着军营里给我安排的一切,因为,我绝不能有负于他们,我被安排到兵的后勤室休息,他早已为我铺好了崭新的被褥,口外的夜,是很凉的,温差很大。
兵将教导员的台灯拿来放在桌上,而刚从镇上回来的教导员,更是一个大活宝,他对我的见面熟是毫不奇怪的,营长不知给他了我多少事,他简直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自己,这是一位心直口快的山东汉子,口音里夹杂着百分之八十的山东味儿,当他听到我也用山东话跟他交谈时,他那两道浓浓的剑眉扬出了极其兴奋的神情:“老弟,你可真中!不愧是搞文艺的!什么话都能象。”我告诉他,妻子的祖籍也是山东,他乐透了:“真是天大的缘分!那你就是俺山东的女婿!”。
这是一位和我同属相的龙人,比我大两个月,但话语间却给人一种他长我十多岁的感觉,他没有架子,话直得能捅人骨头,你不必有任何避讳,一切的俗世间的防备和戒心,都会在他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和令人感到羞耻。通过饭间的交谈,我发觉彼此的投缘已超过了营长和我的缘分,难怪营长对他:“你们俩好象早就认识一样,我倒显得多余了!”教导员的笑声比营长的更爽朗:“这你没办法,什么叫缘分?子你该明白了吧?!”。
在他的周密安排下,除了兵为我服务外,晚上没有任何人打搅我,我感到有些不安,我做了些什么事,这么值得战士们如此款待?良心上有些过不去,我问兵;“你们怎么对我这么好?”兵:“我们一直拿你当自己的战友看!”这句话透了一切难言之情,我扶案挑灯,一直写到深夜十二,直到兵再一次催我:“叔叔,快睡吧,营长和教导员知道了要骂我的。”作完最后一段串白,我较为满意地放心睡下了。
(盛顺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