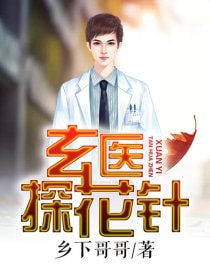祝允同又笑了,笑得憨厚万分,就像是农家汉子吃饱了饭走到田间,看见农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都垂到土壤中时露出的那种笑容,也像是谁家的一个懒女人,睡饱了觉,睁开眼便看到眼前是一桌丰盛的饭菜时所露出的笑容。
那笑容很满足,满足到极点。
祝允同少年的时候用剑,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也觉得剑中直,端正,很适合自己。
但是现在祝允同不用剑了,因为剑终究是身外物。
祝允同现在喜欢用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手。手是身体中最灵活的部位,也是最锋利的剑。
无论是怎样繁杂的指诀,手都能比划出来,所以无论怎样强大的剑意,都能通过手释放出来。
祝允同出剑了,也就是出手了。
祝允同一抬手,手势笔直,从指尖到肩膀,一条无可挑剔的直线。他比的是剑指,食指与中指并拢打直,直指迎面扑来的恒星。
前一刻依然光华夺目,令人无法直视的恒星发出“嗤”的一声,就像是烧红的铁浸入了冰水之中,那光芒瞬间爆发出千百倍的光芒.
但是只是这一瞬,这一瞬过后,再耀眼的光芒,再炽热的火焰,都彻底黯淡冷却。
恒星崩溃了,坍塌了,消散了。
一击破一击。
看上去谁都没有吃亏,但是陆茹满是褶皱的脸上却露出一分凝重的神色。
她是前辈,她本该是一击得手,至少要占到一点优势,但是她没有占到任何的优势。
这就意味着,对手至少在实力上与她极其接近——八阶巅峰,百余年就达到了八阶巅峰,他还有很大的希望冲入九阶。
这让陆茹有些嫉妒,随之而来的是恼恨,她要今日在这里边将这个希望彻底摧毁。
祝允同笑容依旧,眼中反而有了光芒,道:“有意思。”
欧凯咳出了一大口血,挡住了追击自己的洛星——他只要拖住洛星就好了,易苏苏会和祖恭联手,迅速解决掉已经负伤的吕牧之。
一声凤凰清啼,凤栖梧长剑破空,凤凰燃烧起的烈焰将一片星辉引燃,燎天火舌,疯狂翻卷。
“有意思吗你们,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这么多人打我们这几个人,你们好意思吗你们!”凤栖梧愤怒地咆哮着,手里的剑却没有停下。
他的一身红袍已经满是裂纹与鲜血,狼狈万分。
“话太多了。”路驽笑骂道,也一般地狼狈不堪。
虽然两个人都是五阶巅峰,但是迎战这么多人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在一层接着一层连绵不断的攻势之下,他们只有防守之力,而随着防守的进行,他们也变得越来越被动,防御之中的漏洞也越来越多,被突破防御只是迟早的事情。
穆少恩没有说话,只是用尽全力将两仪轮展开,将自己、凤栖梧和路驽纳入防护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将来自敌人的攻击卸去。
云埔本来以为应该会很快战胜眼前这个美丽的女人,因为他自信自己六阶中段的修为,更相信自己的能力。
但是云埔非但没有能够取得胜利,甚至没有一丁点的优势——他始终处身于劣势之中。
刘鱼悍然的贴身肉搏让云埔招架得很困难,尤其是那一道道冷冽到极致的剑意,不断地在他的身上划开一条条口子,哪怕他能够堪堪躲过,但是那森冷的剑划过皮肤的感觉——一点也不好受,让云埔有种忍不住要战栗的错觉。
看着那一道道以凤鸣山庄的功法运转起来的剑,云埔却总会想起关于剑宗的一些故事。
傲剑洞天很简单,专注于修剑,不然也不会自名为傲剑洞天。
但是在这条路上,傲剑洞天也产生了分歧——很多年前诞生了一个一心一意修剑的男人,他专注于把一柄剑发挥到淋漓尽致,不需要任何的法术,一剑破万法,这就是剑宗。
剑宗已经毁灭了,但并不代表获胜的气宗真的就把剑宗的一切都弃如敝履。
实际上,雄才大略的前代洞主春山君便将剑宗的很多理念引入了气宗。
云埔作为一个很有天赋的年轻人,他难免有些傲气,所以他虽然接触到了剑宗的理念,但是认为,这既然是失败者的理念,那么应当被摒弃。
所以云埔从来不把剑宗理念放在眼中。所以云埔也认为,自己那个沉迷于剑宗理念的大师兄,只不过是比自己早入门十年,再给自己十年,自己就能超过他。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云埔看到刘鱼的战斗方式,他总会不由自主地将它和剑宗的理念联系起来。
刘鱼的剑来得很凌厉,很干脆,很果断,没有任何拖泥带水,没有任何犹豫不前。
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剑,只要她一递出这一剑,这一剑的剑势便已经形成,那么这一剑便无可阻挡。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剑法,在他们印象中,不管是修的气,还是修的身,任何招式,任何法术,都需要经过真气从体内释放,然后通过真气与天地间灵气形成联系,从而驾驭天地间灵气呈现出相应的具象。
这需要时间。
从你动这个念头,到操纵真气,到灵气具象,这都需要时间,哪怕再快,都需要时间。尤其越是消耗真气,越是强大的法术,那么需要的时间越是长久,因为他们需要调集更多的灵气。
所以实际的战斗中,每个人清楚自己做出每一个对策需要多少时间,对方的反应需要多少时间,从而使自己的应对尽可能合理,更能做出预先的判断,逼得对方无路可走。
但是刘鱼的剑,真的不讲道理。
因为她不需要时间,她说这一剑是怎么样,这一剑就是怎么样。
尽管每一剑都披着凤鸣山庄的九歌剑的外皮,但是,却令人难以相信明明潇洒飘逸的九歌剑会来得这么猛烈,简直就是狂风暴雨打在了在荒原中行走的路人脸上,而这些路人还没有伞与躲雨的地方。
云埔费尽心思想要预算处刘鱼的下一个动作,提前封死刘鱼的退路。
他根据刘鱼剑意耗散速度推算,刘鱼向前十七步,剑意刚好耗尽,所以到刘鱼踏出十六步半的时候,云埔的剑迎了上去。
但是刘鱼第十七步落定,剑意再起,云埔反应快,飞速闪避,但是两个追随而来的师弟师妹却慢了半拍,顿时被凌冽的剑意所斩,鲜血四溅,好不容易才堪堪从这一道剑意中脱身而出,但是刘鱼却穷追不舍,剑意不减,掩杀而至。
云埔心里有些发苦。
对面那个清丽的女子,现在和她手里的剑很猛烈,他有点不愿意去和这个女子对战了,但是那股凌冽的杀意紧紧锁定在他的身上,无论他如何退避,如何躲闪,下一刻,她一定会持剑杀到跟前。
一个六阶中段,被另一个六阶中段追杀得像条狗,这实在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至少对于被追的那个人来说,是这样。
不过至少值得庆幸的是,有师弟师妹从一旁进行协助,分担走了他不少的压力,使得刘鱼的攻势虽然能够伤到他,但是至少却还不至于动摇到他的根基。
这在云埔想来真不是个滋味,被追得像条狗也就罢了,居然还要联合师弟师妹才觉得能够战胜对手,这对于云埔的骄傲来说,实在有些难以忍受。
不过云埔再骄傲,也知道不能因为自己的骄傲坏了大事。
师傅说了,要不择手段,那就只能不择手段。
剑名无闻的目光不再落在黄海与黑舟的对抗上,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个他并不熟悉的女子身上。
剑名无闻觉得那个女人穿红袍一点也不漂亮,虽然她长得很很美,她的面庞被那红袍映衬出了几分血色,就像是一抹娇羞的红晕。
但是那却与那女子的气质格格不入——甚至是相去甚远。
剑名无闻觉得那个女人应该穿上一袭一尘不染的白色衣裙,然后配上手里那口如流动的溪水一般的长剑,才能与她那强大的剑意相配。
这样的话,那女子便会变得更美。
尤其是一剑划过咽喉,血染白衣会有一种别样的美感。
剑名无闻觉得自己的心有些躁动难安,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
他想和那个女人战一场,但是他一时之间不能走开,所以便只能有些焦躁地看着那个女子。
不过让他庆幸也让他兴奋的是,那个女子在围攻之下没有任何要落败的迹象,依然占据着主动,依然主导着战局的走向。
他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他越来越难以压抑心中的那股冲动。
要与那个女子好好地战上一场,尽情地体会剑与剑的交织,剑意与剑意的交锋,看一看,到底是谁的剑更强,谁的剑更快!
但是他依然没有动,因为他万分地好奇,好奇那个女子能够将那剑发挥到什么样的地步。
剑道之上,剑名无闻已经孤单了太久了。
这个女人会带给他更多的惊喜,会让他知道,剑道之上永无止境。
他如此期待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