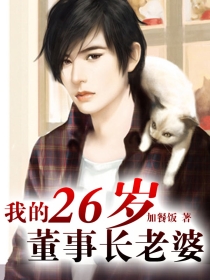与望京相比,东陵城里的大通钱庄生意好了许多,几乎每个镇上都有大通的分号,来福客栈斜对面就有一家。
长歌抱着侥幸心理找来钱庄掌柜,亮出金印,问道:“京城可有信传来?”
掌柜倒也谨慎,不卑不亢的说道:“京城分号太多,不知公子问的是哪一家?”
“第五分号。”
掌柜作揖行礼:“不知是小姐光临,多有怠慢,赎罪!”
长歌摆摆手:“掌柜的客气了!我三哥怎样?毒解了吗?伤好了吗?”
掌柜的神色凄惶:“避毒珠被劫,三公子性命危在旦夕,全凭二公子以内力和药石护住心脉,勉强吊着一口气。”
“什么!”长歌大惊:“怎么会被劫呢!”
“似是那下毒之人,算准了我们要用这避毒珠,早早设下埋伏。我们接应不及,被对方得了手。”
顾羽珏听到赵振来报,说葛小姐一大早就去了大通钱庄,等了一刻钟正要前去找人,人却自己回来了。
看她神色有异,顾羽珏上前询问。长歌神情恹恹:“我有件事想单独和你说。”
赵振找了个“准备早餐”的理由退出去,不忘掩好房门。
顾羽珏拉住她的手坐在圆凳上:“小姐尽管吩咐,在下洗耳恭听。”
长歌咬咬牙:“上次你给我解毒的冰蟾,能否借我一用?我保证,用完立刻归还,绝不会有半分推迟。这里有大通钱庄的三十万两银票,就当做订金,用完之后我会再补上七十万两,你看如何?”
顾羽珏皱眉:“你要冰蟾何用?”
“对不起,我不能说。”
顾羽珏心中起疑,一大早突生变故,莫非她收到了什么消息?可是有赵振把手,别说是生人,连只生鸽子都没见过。对了!大通钱庄!
“你去大通钱庄所为何事?”
长歌抽出一沓银票,倔强的迎上他的目光:“借与不借就一句话,一刻钟后我便出发。”起身走到门边:“还有,此事不要告与第三人。我二哥叫我不能相信别人,可我相信你,请不要让我失望。”
长歌回房收拾行装,令小二准备了两天的干粮和水。一刻钟已过,小枣吃饱喝足,长歌拍拍它的马头:“咱们回家了,你去看看你娘,我去看看三哥。”说罢再不回头留恋。
长歌日夜赶路,人马俱疲。见小枣实在累坏了,她便停下来让它吃草喝水稍作休息。她拿起一块烧饼,咬一口味同嚼蜡难以下咽。闭上眼睛就是三哥的脸,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想着想着泪水便流下来。
小枣本来伏在地上小憩,听到长歌的抽泣声,伸长脖子舔舔她脸上的泪花,重新站起来甩甩头,又是精神抖擞。
长歌捋捋它的鬃毛:“小枣真乖,咱们回家。”
“咱们回家”是这几天唯一支撑着长歌不倒的原因。五天的路程只用三天就赶到。长歌由东门入城,穿过京城大道从西门出城,再到西山梅园。
今日城门设了关卡,官兵对进出城的百姓挨个盘查。长歌等了两刻钟,前方队伍不见缩短,后方队伍逐渐延长。与其在此排队浪费时间,不如从城外绕行。长歌调转马头,不料与后方一马相撞,那马长嘶一声引得众人侧目。
守城的官兵闻声看来,立即高声喝止。长歌也没多想,继续往前走。
一小队官兵赶来将她团团围住,头目喝道:“说你呢!跑什么跑!一看就是做贼心虚,给我拿下!”
长歌不明所以,眼看刀枪无眼一齐向自己招来,挥起马鞭乱舞。
那官兵见长歌反抗,更是来劲:“果然是通缉要犯,兄弟们,都小心点儿!这贼子甚是邪门儿,当心着了他的道!”
又来一队铁衣重甲的士兵前来助阵,这下场面更混乱了。
长歌明知自己不敌,索性不再反抗。眼看包围圈越缩越小,绝望之际脑海中灵光一闪,强自镇定的说道:“敢问各位将士归属哪位将军帐下?”看众人一愣,抽出刘北送的令牌:“不知各位可识得此令?”
将士们定睛一看,这个“刘”字谁人不识?立刻收兵赔礼:“不知是刘将军的人,误会误会,多有得罪!”
长歌撇撇嘴,“刘将军的人”听起来真是别扭。于是纠正道:“我乃刘将军的故交,今日有些急事,望各位行个方便。”
“那是那是,您请!”
长歌点头,正要御马前行,忽听得背后一声“且慢”。众人循声望去,一骑红尘直奔长歌而来。
长歌看清来人,皱着眉头语带怨念:“你来做什么!”
顾羽珏眉目含笑却难掩脸上风霜:“来给你送东西呀!”从鞍上的褡裢里掏出一个锦盒:“这东西原本在望京家里,我派人回去取了来,连日赶路终于追上了!”
长歌看着锦盒,又是激动又是感动,喉间哽咽的说不出话来。顾羽珏将锦盒塞到她手中:“不是赶时间么!还磨蹭什么!”
长歌把锦盒抱在怀中,转问守城官兵:“他也是刘将军的故交,能否同我一起进城?”
“这……”士兵为难的看着他俩:“这位公子可有令牌?”
“不必了。”顾羽珏拍拍长歌的肩膀:“你先走,我晚一些进城。”
也只能如此了。长歌看着顾羽珏:“等我办完事就去找你,城北有家聚福楼,我和四哥从前常去,你便住在那里吧。”
顾羽珏点点头:“我记下了。你路上小心,速去速回。”
有了令牌,长歌自西门出城也方便很多。出城之后直奔西山,眼看道路两旁绿树成荫,与三月前离家时全然不同,心中忽生悲戚,果然近乡情更怯。
来到梅园,小厮早就在门口等候,替长歌牵马,告诉她二公子在书房等她。
长歌施展轻功起落间来到书房,尚未开口,屋里便传来韩修远的声音:“长歌,进来吧。”
长歌潸然泪下:“二哥!我回来了……”
韩修远起身把她揽入怀里,轻拍她脊背:“二哥知道,你在外面受苦了!”
长歌摇摇头:“我没事,我很好。三哥呢?他好不好?”
韩修远叹口气,神情之中尽显疲惫:“二哥无能,平日里只研究些草木之毒,对这蛇虫之毒却是束手无策。”
“二哥,你带我去见三哥,我有办法,或许能试一试。”
韩修远没有多问,携了长歌来到周念的卧房。一个灰袍大和尚正在替周念运功疗伤。长歌见周念印堂发黑,唇角不时有黑血溢出,大和尚不住的流汗,两个人看起来都很辛苦。
待大和尚收掌调息,韩修远上前将周念放平,抱拳道:“有老智全大师!”
那和尚睁开眼睛,竟是一双白目。长歌惊的倒退一步,韩修远皱眉:“小妹无礼,大师莫要见怪!”
智全呵呵笑着:“只怪老衲生的吓人,怎么能怪小姐无礼呢!”
长歌低头抿嘴,上前一步跪下:“大师见谅,请恕小女子少见多怪。大师为我三哥治病疗伤,小女子感激不尽,不敢有丝毫不敬。”
智全轻挥袍袖,一股柔和的力量将长歌托起:“小姐不必行此大礼,老衲受之有愧。治病救人乃是份内之事,济仁堂造福万民,老衲能够尽一份绵薄之力,自是义不容辞。”
长歌抬头看看韩修远,心里明白了七八分。感情他是打着济仁堂的名义就冥远楼的楼主!
韩修远说:“大师辛苦了,请到厢房稍作休息,在下准备了一些素斋请大师品鉴。”
智全颔首,抓起床边的禅杖,由小厮带路离开。
长歌趴在床前,看着周念凹陷的双颊心疼不已。“二哥,让我跟三哥单独待会儿行吗?”
韩修远摸摸她的头发,转身出门。
长歌从袖袋里小心拿出锦盒,打开一看,盒分两格,一边是晶莹剔透的冰蟾,一边是红红绿绿的三十万两银票。长歌微微一笑,轻轻取出冰蟾放在周念嘴边,小声念叨着:“冰蟾啊冰蟾,救救我三哥吧。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毒全都吸出来,让他快快醒来。”
冰蟾肚子一鼓一鼓的吸起来,不时发出“咕咕”声。不消一刻钟,原本雪白的冰蟾全身浸润了黑色,往后一跳,恹恹的趴着不动。
长歌有些惊慌,难道三哥的毒性太厉害,连冰蟾都毒死了?
却不知这冰蟾乃毒中之王,专以毒为食,此刻不动全因吃饱了所致,就像人一样,每每饭后便发懒犯困,冰蟾吸毒吸饱了也要打盹。
这一人一蟾就这么趴在周念身边两三个时辰。长歌连日赶路疲累至极,不小心睡去了。醒来后发现冰蟾又是通体雪白,静静的坐在锦盒之中。再看周念,面色已不似刚才那般青黑,苍白中隐隐透着血色。
长歌高兴坏了,又不敢声张,生怕二哥问起。连忙把锦盒装入袖袋中,趁着没人发现,偷偷的骑马下山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