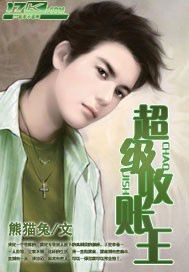这样的过程一直重复到了中午十一点多,算一算出来已经四个多小时了,赵爷喊停。看得出来,他对今天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一直端着茶在下面看,不住地点头。
来到食堂的时候,我仍旧是打两份饭,我一份,傻宝一份。等着傻宝来到食堂,两个人一起吃完了饭,我没有拖延时间,立刻带着傻宝回了宿舍。今天的手指操还没有练习,不能荒废了。上午的训练让我觉得做手指操的难度降低了很多,而且手指交换的速度比以前快了一个档次。
跟着傻宝做了四五遍之后,这小子已经歪着头,嘴角流着一抹口水,呼呼大睡了,我只能自己练习。现在的时间,对我来说分外珍贵,任何一种能够保命的方法,我都没理由放过,现在的忙碌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不敢停下来,只要一停下来,就会想起三周以后的擂台赛,感觉到恐慌和压力。做着做着,胳膊渐渐抬不起来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头一歪,也睡着了……
下午的时候,是赵爷摇醒我的,起床一看,边上的犯人已经全走了,整个房子里就剩下我和赵爷两个人,再瞅瞅墙上的钟——四点一刻……
赵爷笑着拍了拍的肩膀:“上午高强度的训练不轻松吧!看你都累得起不来了!”
我挣扎着从床上翻起来,真的,从上肢到下肢,从胳膊到腿,没有一处不疼的,就是那种仿佛折断了一样的疼痛。
我两把穿上衣服,跟着赵爷走了出去,在各条路上七拐八拐。看样子,不是去上思想教育课了,也不是去铁丝网的方向。估计下午,赵爷也有安排吧,我没吱声。
半个小时后,赵爷带着我来到了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很靠北,从场子里望出去,已经可以看到四岛后面的高山了,边上竖着高高的哨塔,能看见里面有扛着抢的兵,走来走去。边上的围墙足足有六七米高,墙垛上拉着电线,没有外包皮,裸露着里面红红的铜丝。戒备森严的四岛,在我眼前慢慢呈现。
这间屋子就像是卖毒品的那个据点一样,周围全是一模一样的屋子,看得人眼睛都有点发晕。要是不知道的人到这儿,在这样的一堆屋子中间绕来绕去,迷路是肯定的,就像是迷宫一样。
屋子里开着灯,拉着窗帘,所以光线还可以,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台电视机,底下有个录像机放在右侧。屋子的另一边是纸质的大箱子,总共有四个,靠着墙根,摆放地很整齐。赵爷在一个箱子里找了半天,拿出来一盘录像带,弹了弹上面的灰尘。我顿时有些无语——叫我来看录像?
这东西好像已经快要灭绝了吧!还记得那是上初中的时候,在唐阳,录像厅是很风靡的,大街小巷里都有营业的,有的甚至是昼夜营业,生意很红火。那时候电影院是远远比不上录像厅的。
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下午,这段时间是放枪战片和动作片的时间段,成龙和李连杰等功夫巨星的片子被放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一些翻刻的外国片子,质量参差不齐,既有好莱坞的大片,也有不知名的小电影场拍出来的剧情很烂的片子。
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播放一些比较有内涵的片子了,除了一些恐怖片,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僵尸系列,僵尸爷爷、僵尸叔叔、僵尸妈妈什么的,反就是把僵尸家,按照族谱拍了一遍,看的人很多。还有外国早期的恐怖电影,以日本的为主流,也常常能在录像屏幕上看到。
还有一些录像厅是只有男人、没有女人的,反正我很少见女人去那儿。从晚上八点多开始,就放一些男人感兴趣的片子,俗称的毛片。按照情节来分,有有剧情的和没剧情的,按照人物来分,既有非洲大陆的同胞,又有来自欧美的白人,还可以见到亚洲的黄种人……
总之,世界五大洲的人基本上全齐了。从当时最多的,还是日本的吧,除了日本的就是香港的,基本上呈垄断态势。看来岛国从那时候就有独霸全球
黄片的雄心壮志,政府大力支持A片的拍摄。时至今日,这个民族也向我们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和忍耐力——言必行,行必果。
今天,谁还敢说欧美的色情产业链能和日本的相提并论?至少在中国,日本一家是独领风骚——清晰程度有有码的*的,人物数量从一到多,还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情节更是层出不群,新意翻番(为防河蟹,这儿留给大家足够的想象空间)……
初中的时候,我就经常逃课,基本上唐阳所有的录像厅,都去过了,可以一口气报出来哪个录像厅比较实惠,哪个场子里经常进新片,哪个场子是专门的午夜场,哪个场子里可以包夜看,哪个场子提供不限量的、有些发霉的瓜子……
我这方面的启蒙,也要多亏这些数不清、看不完的激情好片子,还记得,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录像厅老板蘸着唾沫数一毛钱时神情的专注和贪婪;中间散场后,中场休息时候,厕所爆满;看录像的人,从小学的小孩到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们,全都是充满血丝的双眼,不知道是看屏幕吃力的,还是激情燃烧的……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现在这种录像厅,在网络和电影院、家庭影院的三重打击下,已经很难抬头了,曾经的繁荣已经成为了历史,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几家,稀稀落落,门可罗雀……
一个属于录像厅的、一代人的记忆已经远去,再也找不回了,从小到大,我们有多少这样的记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了历史,或者化作了了云烟?
今天带我来到这儿,一看到熟悉的录像机,我就有种想哭的冲动,再看着赵爷手里拿着的、熟悉的带子,我内牛满面:“赵爷,看片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