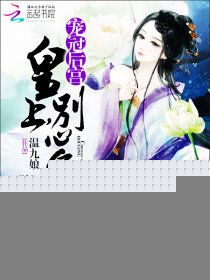教室里,乔蝶雨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亦如往常一般静静地看着窗外发呆,而丁兰和李好两人,一个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坐在他对面,满眼惊奇地看着他。
现在整个初中一年级六个班都在议论他,对于他九门试卷都是不到一个小时就提前交卷猜测不已,有说他弃考的,有说他作弊的,甚至高年级的学生都有不少人在议论这个开创壮举的学弟。
但不过不管他们议论地有多夸张有多离谱,丁兰心里明白,乔蝶雨既没有弃考也没有作弊,至于他是如何做到的丁兰已经询问过多次,可乔蝶雨都以沉默作答。
这让她的好奇心愈发地强烈,因为他们两人除了睡觉的时间是分开的,其他的时间都是形影不离,对于乔蝶雨有没有好好学习,下狠劲,丁兰是一清二楚,可他的表现却是恰恰相反。
乔蝶雨不仅不是努力刻苦,甚至可以说是极度地散漫,因为他一天的时间不是在教室里看着窗外发呆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窗外发呆,要么就是在他父母的房间里摩挲着他们的遗物发呆,上课既不认真听讲,下课也不温习功课,要不是以她对乔蝶雨的信任,丁兰都要以为乔蝶雨依旧在那悲伤的世界里自暴自弃了。
“小雨,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没有告诉姐姐,快说,要不然,哼哼!你是知道我的手段的!”沉默良久,丁兰还是压不住心中的惊奇之意,拿出了杀手锏。
只见她噌的一声就将自己的椅子挪动了乔蝶雨的身侧,手臂一扬便搭在了他的肩上,随即头一伸搁在了另一边的肩头上,和他一起看向那窗外满眼可见的柳树林,一半撒娇一半威逼,软硬兼施了起来。
“没!”对于丁兰的动作,乔蝶雨没有半点反应,只是淡淡的一个字。
“没有吗?可我的感觉却是你藏有一堆的秘密。小雨,还是老实招了吧,要不然姐姐今天晚上就去你房间找你彻夜长谈,呵呵!”丁兰的这句话或许李好听不懂,但她相信乔蝶雨绝对听得出来此中是要与他共处一室,大被同眠的意思。
然而对于丁兰更加严厉的威胁,乔蝶雨依旧只是简简单单一个字的回应。
“没!”
“你!”乔蝶雨平淡的回应让丁兰不禁紧紧地握住了拳头,脸上浮现出佯怒的神情。
但在此刻,丁兰却是满心不可言喻的悲痛,脑海里浮现以往甜蜜美好的种种过往。
“哎呀!你,你快放开我,好多同学都看着了,被你这样搂着羞死人了,你不怕羞,我还怕了!”
“哈哈哈!怕啥!学校里谁不知道你是我的人,有什么好害羞的!放心!兰姐会对你负责的!哈哈哈!……”
……
“你快放手!我爸妈还在这了!快放手!”
“呃!那个叔叔阿姨!你们交代的事我会放在心上的,保证不会让他出任何一点意外!”
……
“以前我这样搂着他,他绝对会羞红了整个脸庞,明知力量不足却每每都是拼了命地要挣脱我的怀抱。可现在,可现在他既不躲闪我的强搂,也不羞愤难当,更没有半点的挣扎,这还是我心目中的那个羞涩地可爱的大男孩吗?现在的你除了平静无波的脸庞,寂静若死水的眼神,就只剩下那永远也发不完的呆,回不来的神。小雨,小雨啊!你告诉姐姐,告诉姐姐该如何才能让你回到之前那个羞涩朝气的书生模样,怎样才能唤醒你那颗冰冷而悲伤的心呢?!”
回忆的模样与现实慢慢重叠,却发现眼前的人仿佛只是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要让他回到记忆中的模样只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罢了,也许这只是一种奢望到绝望的奢望而已。
随着心中的万千思绪,丁兰佯怒的神情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满脸想得出神的悲伤。
在丁兰心中,其实她并不是要在乔蝶雨这里挖到些什么惊人的秘密,她想的只是要乔蝶雨更多地回归一些正常人的生活,有着喜怒哀乐,哪怕是稍稍给点其他的表情也好,不要再是那一成不变的平静与漠然,平静的让人窒息,漠然的让人绝望!
“也许是我太着急了,慢慢来,慢慢来!”丁兰心中自语着安抚着自己急躁的心情、紊乱的心绪,不觉兰息轻吐,吹起了几缕乔蝶雨耳边的鬓发,也扰动了他平静外表下渴望的心弦!
“兰姐,对不起了!我知道你的用心,可现在的我却是越陷越深了……”
无语之间,只有心与心的跳动,欲近却离……
“唉!大消息呀!大消息!”就在丁兰和乔蝶雨彼此沉默,相对无言的时候,一道尖利的声音吸引了教室里所有人的目光,此刻,只见教室的门口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身影,在午时烈日的强光照耀下,却是一时看不清容貌。
“包苟同,把你那个破镜子拿开,晃得我们眼睛的真不开了!”
“苟仔!你在搞什么呀,你以为这样的出场方式很拉风吗?”
“包打听,你要找揍吗?别到时候又要你老爸帮你出头呀!”
“呵呵!我看是要和以前一样,不是我们出手,而是被他老爸给修理了!”
……
在一片嬉笑揶揄声中,这个叫包苟同的学生已经走了进来。光华散尽,此时再看,已是可以清楚的看清他的模样了,却是一副颇为滑稽的模样——眼小如豆,尖嘴猴腮,像老鼠般小小的鼻子上却挂着一副厚重的眼镜,头上是一头稀疏的黄发,而此时他却还在对镜而梳,用手摸得根根整齐。
这,这个长相滑稽,甚至可以说有那么一丝猥琐的男孩子就是包苟同,人送外号包打听,也称他作苟仔。
说起他,那就有一篓子的话要说了。他的老爸包大同是他们这个班的数学老师,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包老师不仅为人和善,而且还是个美男子,虽已至中年却依旧玉树临风,潇洒儒雅。
相对于包大同的帅气来说,包苟同就长得磕碜了些,在很多时候同学们都会纳闷的问他为什么他们父子会长相差距与此之大,甚至可以说是绝然相对的两种模样,是不是包苟同有可能不是包老师亲生的。
对此,包苟同也是大感纳闷,多有猜疑,最后他还亲自跑去问过包老师这个问题,而包老师却回答他这样一句话:“你要不是我亲生的,我早就捶死你了!”
此话一出,吓得包苟同赶紧逃跑,自那之后,只要有人问起他这个问题,他都会如此回答:“我绝对是我老爸亲生的,我虽没有遗传到他的帅气,但却遗传到了他的智慧,至于我的容貌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是老天对我的一种妒忌,若非如此,岂不是让我包某人才貌双全!要是如此,你们岂不是无地自容地见了包某人就要退避三舍了?!像包某人这般和善的性格,无法与人相亲相近,简直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对于容貌的问题也许我们还能接受,可对于他的性格而言就更是奇葩的让人无语。听刚才同学们叫他的外号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二了,没错,他就是学校里消息最灵通的人,而这也是他的爱好,喜欢四处打听消息。
就他常挂在嘴边的话语来说就是他长大了做一个世界上最厉害最出名的记者,因此仗着他三尺厚的脸皮和不怕打击超级自恋的个性,他也的确每次都能得到学校里最新最快最准的消息。
而这样的奇葩儿子,包大同每次见到他都是无语到暴走的边缘,即使以包大同绝佳的气质和修养都压抑不住这股莫名火气,但包苟同却好似没有发现这点一样,经常作死的跑到包大同那里打听学校里最新的消息。
说来也奇怪,虽然包苟同每天都把业余的时间用在了打听消息之上,可他的成绩却老是处于年级的上游,好像真如他说得那般自己是遗传到了包大同的聪明才智一样,当然,要不是他的成绩还说得上去,想来包大同也不会对他这个不务正业的儿子这般容忍了。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他的名字也是一件趣事。包大同当初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本意是要他做一个有主见的人,希望他在以后的人生中能保持自我,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而包苟同也却是做到了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是做超了,因此他也有了句口头禅——包某人不敢苟同也!
“嗯!那个!包苟同,你能不能把你那破镜子收起呀?你看哪个男生像你一样这样的臭美,整天都拿个镜子来照啊照的,还不断地捋那几个稀毛,你就不怕到最后把自己摸成了个秃子?”
就在包苟同依旧在那对镜梳妆,自我欣赏的时候,一个国字脸皮肤稍黑,却五官端正的女生忍不住笑闹了起来。
闻此言,听此声,包苟同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谁,可他还是颇为依恋地收起了他的随身宝贝——一个折叠的小圆镜,这才抬头看向刚才出声的那个女生,咧嘴一笑,却是给人一种忍俊不禁的喜庆感。
“我说,陈珍珍同学,你能不能别每次都拆我的台好不?好歹我们也是同桌,说起来也是同一个战壕的同志,自相残杀可不好吧!?”
“慢!我们虽是同桌,但我却以此为耻,都是你这个奇葩,搞得每次我都被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他们议论的话题无不和你有关,却让我莫名中刀。再者,我不是和你一个战壕的同志,别拉我下水,对于那些八卦新闻我没有半点兴趣!”
听到包苟同厚颜无耻的拉关系,陈珍珍面色一黑,满脸幽怨地抗拒到。
“哎!好歹我们也作了两三年的同桌,你无情我却不能无意,我们之间的缘份不是你三言两语就能抹杀得掉的!”
对于陈珍珍的幽怨情绪,包苟同视而不见,只是一个劲地嬉皮笑脸。
“啊!还说了,哪次排位不都是你涎皮赖脸地硬凑过来的,撵都撵不走,而且还躲都躲不掉,别以为我不知道,明明我们都不同班的,可你却赖着脸到你老爸那去苦求,让他调动关系为你调班,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和他说的,他也能容忍你这样的要求!”
说到同桌之事,陈珍珍像是被踩了尾巴一般,恼怒不已,真不知道自己上辈子和包苟同是怎样一段冤孽之缘,今生要对她如此纠缠不放。
见同桌缘分之事被道穿,包苟同不禁嘿嘿一笑,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心虚。
陈珍珍说得没错,他们只间的缘份的确是包苟同可以营造出来的,至于为什么一定要缠着她不放,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是不该存在也不会存在的情感方面的缘由,包苟同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和她在一起特别地有趣味。
自从他们认识到现在,从第一次见面到以后每次的在一起都会吵闹不休,拌嘴互掐,这让包苟同感觉他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生机盎然,这种感觉让他感到舒心与自在。
也许,在他心中,这就是他一直纠缠陈珍珍的原因,他不知道这种感觉的背后代表着什么意义,但他知道,他喜欢这种感觉,而他也确信,陈珍珍也是同样很享受这种莫名言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