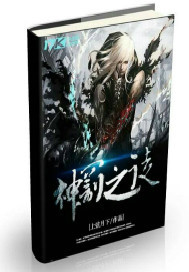8、第 8 章
暮色正浓,白日里暖阳的温度尚未散去,半夜竟下起雪来,细细密密的雪花从天而降漂浮洒落,不断发出“簌簌”的声响,倒也为这寂静寒夜平添几抹生机。
御书房内灯火通明,倚在坐榻上小憩的帝王忽然睫羽微闪,随即缓缓睁开双眸。
当看到面前堆满案几的奏折文书时,他目光有那么一刻迷茫,却很快恢复以往的清明,抬手揉了揉鼻根,长吸一口冷气。
近几年他一直多梦浅眠,零零碎碎梦到些少年的时光,都是久远得几近模糊的画面,可无论是怎样的梦境,总少不了那一抹熟悉的身影,如同鬼魅般,跗骨难逃。
也正是这时他才惊觉,从初时的艰难困苦,到如今的无上尊荣,原来她真的贯穿了他目前为止生命中所有的跌宕起伏,喜怒兴悲。
或许是年岁渐长的缘故,那些极为暴戾厌恶的情绪竟慢慢淡去,反而显露出一些本来的画面。
年少时的上官梨,时常背着个包裹,飞一般跑进他破旧的偏殿,一双黑眸亮晶晶地望着他,献宝似的将东西呈到他面前。
有书籍文墨,干粮糕点,银钱衣物,冬日里甚至会弄来几盆炭火,然后自个儿笑意盈盈坐在他案旁,或是痴痴看着他,或是替他磨墨,时不时发出崇拜的惊叹,总有着数不完的赞溢之词,虽夸张了些,却并非那种令人讨厌的敷衍,就像一团烈火,熊熊燃烧,炽烈且挚诚。
而他呢?那时的他因不得父皇喜爱,又遭皇后迁恨,日子很不好过,一度沦落到被奴才欺压,宫人轻践的地步,即便他当年厌极了她,也不得不承认,是她的爱慕与维护,帮他在皇宫中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护住了他作为一个皇子应有的尊严。
可是少年的爱意与恨意总是那样分明,分明到容不得一丝质疑与犹豫,上官晚棠原也说得不错,他自私,敏感,孤傲,偏执,他认定的人和事又怎会轻易改变?所以她才会一次次头破血流。
他至今都记得她那日被骂之后崩溃大哭的模样,那是苏颖遭人陷害的次日,密报所示正是上官氏所为,不知为何,原本还算冷静理智的他看到这个消息,几乎暴怒得不能自持,所以她平日的纠缠讨好皆为表象,背地里竟然是这样一个阴险卑鄙不择手段的女人?
说来可笑,分明他自己也是如此,可当这些言词落到她身上,便焚烧成了滔天怒火,直直要将人吞噬殆尽。
他毫不留情地讽刺,用上此生最恶毒的言语,冰冷中夹杂着不加掩饰的厌恶,终于,她最后大哭着跑了出去,自此,竟再未踏足偏殿半步,也再未见过他一面,直至父皇驾崩,朝堂动乱,他们绕了一圈,终究还是成了夫妻。
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也能清楚地描述出当日的情形:
她边喊“季桓”边笑着跑进,双手捧着一小盅热乎乎的燕窝递过来,期待地看着他,他却毫不犹豫地将燕窝拂开,瞬时瓷盅破碎,洒落一地,她似乎不明所以,有些慌乱地看向他,只听得他冷道:
“郡主好歹也是千金之躯,怎的这般自轻自贱。”
“季桓,你怎么了……”
“身为一名女子,竟如此纠缠不休,你就这么缺男人么。”
“季桓……”
“简直不知廉耻。”
“……”
她脸色一寸寸惨白下去,大概金枝玉叶的郡主是从未受过此等侮辱的,眼眶周围越来越红,滚烫的泪水如断珠般滴落,终是双手捂脸,跌跌撞撞跑出门,直至行远,依旧能听见那孩子般的嘶声哭鸣。
她原本出身世族,又早早被封为郡主,有着执掌凤印的姑母和权倾朝野的父亲,如此尊贵的身份,她自然是有资格追逐自身所爱的。
她并非特立独行的女子,也不如苏颖那般娇艳柔弱心窍众多,或许是因为父辈过多的疼爱,反倒将她养得愚蠢而天真,喜欢与讨厌皆表现得格外鲜明,小性子不断,傲气还不小,否则便不会从那以后,竟当真狠下心再没入他院门一步,若非后来联姻,他们……只怕此生再无任何交集。
娶她做皇后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可心底里又似乎没那么难以接受,新婚那夜,她显然是高兴的,她说先前之事一概不论,从此以后他们就是夫妻了,夫妻之间只有琴瑟和鸣,无需多礼。
他只是冷笑,这个女人该不会觉得成了婚便是一生一世?
然而他渐渐发现,她兴许当真是那样以为的,她的父亲上官裕是个痴情之人,一生挚爱发妻,无庶无妾,在如此的潜移默化下,才让她生出一种夫妻必定情深的错觉。
婚后的头一年,她愈发喜欢缠着他,时不时找借口上门,只不过因为身份的转变,时常被他拒之门外,久而久之,竟也渐渐消沉下来,常年深居简出,再没闹出过什么动静。
后来朝野巨变,上官一族尽数入狱,废后那日,天空一片灰蒙沉暗,和着微微细雨,淋湿了她原本素净的眉眼。
对于上官氏,他的确是想斩草除根的,却在同她目光纠缠的须臾间,突然就改变了主意,他从不知上官梨也会拥有这样的眼神,坚决,果毅,视死如归。
死亡于他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可放在她身上,却显得如此地遥远而不真实,他恍然想起她为他挡剑身中剧毒的当日,也是这般义无反顾,然后魂魄游离于地狱与人间,几近远走,几近身亡。
正是那一刹那的退却,几乎令他下意识地作出让步,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他是多么坚定地下旨处死上官全府,数十年的仇敌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然这戏剧般的转变,仿佛印证了上官晚棠临去前的咒言--
“你不会那么做的。”
“有她在,你……永远,不会,灭上官一族!”
抚着扶椅的指骨一点点收紧,隐隐可见其上青白。
良久,他松开五指,豁然起身,披上灰黑大氅,长腿一迈,大步朝寝殿走去。
秦霄殿安静极了,只剩青栀守在门口,有一阵没一阵地打着盹,忽觉一片阴影落下,猛然惊醒,见着来人后,连忙弯膝行礼:“陛下。”
季桓身姿颀长,靴底陷于浅浅的雪地中,零星白粒飘落在他发梢额角,愈发衬得他俊美挺拔。
“她如何了。”
青栀不太敢直视眼前这位帝王,只躬身低道:“回陛下,姑娘已经好多了,只是……只是不知为何,迟迟未能苏醒。”
虽然她不知陛下为何唤来太医后又遣回,但多年的直觉告诉她,若里头那位当真出事,谁都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她一整天都悉心照料,特地着人煎了祛风寒的药,丝毫不敢马虎。
季桓不再多问,转身跨入殿内,衣摆掠过一抹清冷的寒意。青栀打了个哆嗦,回过神来紧紧跟上。
掀开厚厚的布帘,一股暖意迎面而来,青栀替季桓解下大氅,自觉退居一旁。
床上的人脸色极差,一张侧颜如同白纸一般,脆弱纤薄,似乎只需轻轻一戳,便能捅出窟窿来。
季桓眸色愈渐深沉,目光缓缓下移,忽而停顿在她右手掌心缠裹着的白布上,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蹙。
青栀敏觉地捕捉到这一细微的变化,轻步上前解释:“陛下,姑娘的伤口在水里浸得有些久,复又裂开一道口子,故而奴婢重新包扎了一次。”
季桓撩起袍裾,就着床沿坐下,握住她枯瘦的手细看了片刻,唇齿间溢出低沉的声响:“这伤口为何还没好。”
说完不待她回答,又接着道:“可有上药。”
青栀腰身躬得更低了:“回陛下,上了些金疮药。”
凭她的身份,只能拿到此类普通的药物,但她想了想,仍是补充道:“姑娘之前涂抹的应当也是这种药粉。”
季桓敛眼,黑眸如夜色一般深寂幽冷,半晌后才淡淡出声:“取白玉膏来。”
“是。”
青栀福身退下,不消多时,便拿了个玉色的盒子进来,打开盒盖,跪举过头顶。
季桓拆开她右手上的白布,挖了一坨细细抹匀,清凉的药膏散发出阵阵幽香,丝丝缕缕萦绕鼻尖。
青栀又将准备好的丝绢递上,可那骨节分明的手触到白帛的瞬间又忽然停顿住,灯影交错下,他黑眸沉远,恍若无边暗夜。
青栀心中疑窦丛生,还未来得及细想,却见那人已然收手,起身往外,空中只余下深冷的回响:
“给她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