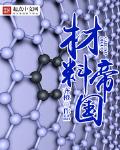台湾
戴着深灰色墨镜的黑也焰站在一问豪宅的大门外。
他的唇畔淡淡地勾勒出嘲谑的笑。
那老家伙肯定已经等待许久了。
“少爷?!”走出那扇古董级的铜门,佣人乍然见到伟岸的身影,不禁大叫一声。
“去禀告太上皇吧。”
“是,老爷一定很高兴。”佣人马上回身往大屋走。
藏在墨镜底下的瞳眸熠熠生光,仿佛森林之王。
他进了铜门,冷冷一望,仍是两排的警卫。
黑也焰觉得十分可笑…
宽敞的前院仿佛是一座艺术公园,足以容纳几百个人举行宴会。这般大的空间在寸土寸金的台北来说着实夸张了些。
青绿的草坪依然是一年重新栽种一次,由国外空运而来。
可以想见的,后花园的郁金香和牡丹花仍是迎风摇曳。
越过两座价值几千万的古董狮子,他跨进玄关,扫视金碧辉煌的大客厅。
老家伙不觉得刺眼吗?一屋子金光闪闪,瑞气千条。黄金已经不算什么了,水晶和彩色钻石竟然被当成摆饰般的随意放置,还有数不完的古董皆以鱼线固定住,这间大屋根本不是人类的居所,应该当成博物馆收取门票。
他决定直捣黄龙,大步往父亲的书房走去。
“我等你很久了。”八十八岁的黑太将眯起眼坚笑。
是的,好笑
他喜欢和晚年才得到的传家香火斗智,只要见到儿子狂飙狠扫,他就心情大悦,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儿臣叩见太上皇。”黑也焰嘲讽的一笑。
“你是牛津有名的太子,身为你的父亲的我,应该不是太上皇吧?”皇上才是。
“那么是孤单老人一个。”
“不肖子!老父亲八十八岁了,所剩不多的人生你一点孝心也不尽!”他已经开始选购上好的棺木和绝佳风水。
又是这一招!“放心,祸害通常是百岁以上的人瑞。”
“你是祸害所生的小祸害。”黑太将呵呵笑出声。
“无聊。”黑也焰十分怀疑这老家伙的企业财团是如何创造的。
“见到优柔了吧,她可是我津挑细选的智慧型美女。”
“那又如何?”
“如何?”跟他装蒜,欺负老人家!“也焰,你也二十八岁了,需要个老婆温床叠被。”
“温床的女人到处都是,至于叠被,佣人即可。”
“京极呢?他需要个妈。”
“你认为哪个女人可以使京极开口叫声妈?”他这个做爸爸的和老家伙这个爷爷至今尚无荣幸听见京极开金口。
“这…”黑太将站起身,龙头拐杖往地上敲了几响,“总得试试!”黑家子孙怎么可以自我禁闭。
“这和你大肆宣告我的婚讯有何关系?”卑鄙老人。
“怎么样,各界名流的大礼全放到仓库去‘安息’了。”这叫先下手为强。
“黑太将,你真是老人痴呆!”黑也焰冷笑一声。
“死儿子!”存心气死他这处心积虑的慈爱老父。
“我在台湾没有任何事业,”两家上市公司是段夜涯所有,他只是人头总裁。“你的先斩后奏丝毫影响不到我。”
“所以我才要优柔主动一点,叫她到你的地盘与你日久生情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如果我对她视而不见,她撑得了多久?”女人的薄脸皮禁不起他的无心对待。
“但是你已经来了,不是吗?”真可怜,因为想念儿子,希望见儿子一面,他必须无所不用其极的使计。
其实他是相中左优柔做儿媳妇没错,不过他真正的心意是要激怒宝贝儿子。否则他飞来飞去的就是懒得飞到台湾和他联络联络父子亲情。
人老了,什么都是虚幻的,只有亲情才是唯一的依靠。
“难道闲舞也是你这老狐狸所安排的?”天底下最会算计儿子的当数他黑太将了。
闲舞?谁呀?忖思老半天,黑太将才恍然大悟的拍拍额头。
“是那个和我无缘的儿媳妇啊!”
“不必装成毫不知情的模样!”一肚子谋略的老人绝不可相信。
黑太将扁扁嘴,“我真的不知道嘛!”冤枉老人是很残忍的。
“心肝儿子你想想,十年前为了让你看清楚那女人的真面目,我不惜和你恩断义绝,还把遗嘱给改了,我这么讨厌那个放荡的女人,怎么还可能安排她到你的地盘去?”他几乎要老泪纵横。
“与你无关?”黑也焰仍是三分存疑,毕竟老家伙心思不走,和三岁小孩没啥两样。
重重的点头,黑太将一副士可杀不可辱的严肃表情。
他好歹是黑氏企业的掌舵者,是政商名流口中的将老
蓦地,他眼神一亮,眸中泪雾全失。
“是不是优柔和汪闲舞杠起来了?”哈哈哈,一个是前妻,另一个是现在众所皆知的未婚妻,这等阵仗的确有够瞧。
眄着老父亲的兴奋样,黑也焰不知该气或是微笑。“她们快把我的家掀了。”
他唇边骤然浮起几不可见的轻笑…
他的小绯儿好像被惹恼了,她现在大概想要千里追杀他这罪魁祸首。
“无情的宝贝儿子啊,你是由于两个女人的对抗,专程来找我算帐吗?”绝对事有蹊跷!也焰是那种情爱兜不上心头,也从不为女人烦恼忧愁的男子汉。
“我是到皇家解决股东之间的纷争,顺道过来探望你…”死了没有。
黑太将好感动,儿子的心中总算把他这老子搁进去了。
果然血浓于水,虽然他不太喜欢他搞那些军火和赌场的邪门生意。
黑也焰不想再待下去,更受不了老家伙几乎泪涕齐下的温情样。
他挥挥手,“等你的心脏快要罢工的时候,我会带京极回来见你最后一面。”顺便上香。
“段夜涯,外找。”
“一辆凯迪拉克耶。”工头吹了一声口哨。
身为小工人的段夜涯只是耸耸肩。凯迪拉克?嗯哼,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即已拥有七辆百万名车。
但是现下他的代步工具是一辆拼装的破摩托车。
洗去手上黑污的他走出工地,看见来人之后,他不禁好笑的拨拨乌亮的齐肩发丝。
“黑老太爷。”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啊
黑太将瞪着他许久,然后笑叹道:“你哦,好好的继承者不当,跑来当个建筑小工,难怪段老弟四处嚷嚷他生了一个不肖子。”
“您和我家的老头子不是同病相怜?”
“也焰迟早有一天遭天谴,但是他至少成为大亨,虽然经营的是不入流的大行业。”足堪安慰,毕竟宝贝儿子的帐户里有数也数不清的零。
段夜涯展开一记比阳光还要灿烂的笑,“晚辈不才嘛。”
“二十二岁就拿下博士学位的你称得上不才?”那么其他的年轻人不就是白痴?谦虚是种美德,但是用在段夜涯身上可就是个讽刺了。
是不是举凡优秀过度的小伙子全是怪胎
唉!他的宝贝儿子和段小子旗鼓相当,一样的不屑老父打下的金银江山。
“黑老太爷驾临这脏乱吵闹的土地应该是有事相询吧?”总不是来找他谈天、喝汽水。
黑太将于是开门见山地问:“也焰是不是有专宠的女人了?”
他不知道多嘴是福还是祸,只好道:“他的女人多如过江之鲫,谈不上专宠吧?”
龙头拐杖重击石子地,眼看就要敲上段夜涯非比寻常的俊俏美颜,他只得慌张求饶,“让我想想…”
“意思就是有了?”黑太将眸中津光一闪。
果真是老坚巨猾!“是有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啦!不过不知是rou体上的欢愉伙伴或是掺了些许的爱怜。男人嘛,总是缺不了女人这一味…”
“那女孩德行如何?”
德行?这还真难形容。“活泼叛逆的天真少女,外形是属于氧气美人那一款,清纯时像是小天使般可人,邪魅时又似津灵般诱人。”
黑太将瞠凸了老眼,“你在写散文啊!”
段夜涯双手一摊,状似无奈,“老爷子,我只见过她一次,哪里知道她的德行如何?”况且她的德行好与坏干他何事?那是黑也焰的女人耶
“他们是如何结下孽缘的?”一定又是一只贪爱财富的金丝雀。
“好像是她在s里诈赌,差一点就要被剁掉手掌,黑太子和她条件交换,把她带去澳洲。”
“诈赌?是个年纪轻轻不念书的落翅仔?哼!拼了我的老命也一定要把他们的孽缘斩断不可!”
哇!老人家似乎激起万丈雄心,决定来个棒打鸳鸯喽。
段夜涯幸灾乐祸的暗笑于心。
不是他不够义气,爱情这玩意儿得受点苦才能刻骨铭心,才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美感,他是在“成全”黑太子和司徒女娃伟大的爱情。
“咳咳…”他肚子里笑到大小肠扭搅在一块。
“小子,做工太劳累,需要铁牛运功散补补气。”
“感谢黑老太爷的关心,小辈无以回报,愿献一计,解您烦忧。”
“铲除那只金丝雀?”太好了,他迫不及待要大显威风。
铲除?!太恐怖了吧,又不是两军对峙。“左小姐和汪小姐全跑到澳洲去抢夫是吧,老太爷以为两女之中谁有胜算?”
“当然是优柔,她相貌端庄,聪明有才能,又是出身良好家庭。那个汪闲舞?不过是交际花一朵。”还是即将凋零的烂花。
“据我的观察,也焰不太可能对一个太过能干的女人动情。”连想要**都不会有。
“难道就任由那只诈赌的金丝雀成为我黑家的媳妇?!”他绝不允许!黑家少奶奶的名号高贵尊荣,哪能落到不三不四的女孩头上。
“对了,画衣嫂子近来可好?”段夜涯不慌不忙的问,心中暗想,坚计就要得逞了。
“哎,还不是老样子。”那得人疼爱的小妮子只做了他两个多月的儿媳妇,呕啊。
“她还爱着黑太子吗?”
“可不是!”否则哪会依赖抗忧药度日。“小子,你突然问这问题,打的是啥鬼主意?”
“如果把画衣嫂子直接‘打包’送到澳洲,三女,哦,是四女抢一夫,老太爷觉得这算盘拨得津不津?”
“但是也焰又不爱画衣。”当初他们俩结婚之前,也焰就把话给撂下了。
段夜涯眯起丹凤眼,微笑着,“此一时彼一时嘛!人的口味可能改变。”
黑太将拄着笼头拐杖,一边大力敲地,一边笑得前俯后仰,“对对对!红辣椒吃太多总是会上火,偶尔吃些百合莲子羹才是养生之道。”
正摆着漂亮Pose的段夜涯差点摔跤。
倪画衣是百合莲子羹,汪闲舞是红辣椒,那么司徒弱绯是什么?最狂猛的炸药
男欢女爱和养生之道牵扯不上关系吧。
只听得威严的老人缓缓说着,“我立刻把画衣送到澳洲去,最后不管是优柔或是画衣做我的儿媳妇都成!”
“伯父。”怯怯的声音充满敬畏和感念。
“什么伯父,叫爸爸。”他可是她的公公
倪画衣的眼睛湿了,“我已经不是也焰的妻子,没资格喊您一声爸爸。”充其量是下堂妻。
“一日为父,终生为父!连你也违背我的心意?”
老人家的怒火使得倪画衣手足无措,惶惶不知如何足好。
“我…我不敢…”
“是不敢违背我,或是不敢称呼我爸爸?”
“爸爸。”她慌张的轻喊。
“很好!既然你叫我一声爸爸,无论是以女儿或是儿媳妇的身份,我都高兴。”
“爸爸请喝茶。”赶忙端上奋起湖的冬茶,倪画衣恭恭敬敬的连坐都不敢。
黑太将点头微笑。这才是他要的儿媳妇嘛,也焰的眼光着实有问题,竟然不知怜爱,白白糟蹋她的纯情。
瞧瞧,服帖的长直发,只上些唇彩的小嘴,白色端庄的洋装,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粉红色指甲,瓜子脸儿,细嫩的白皮肤,青山黛眉,活脱脱是从古画里走出来的大家闺秀。
加上柔婉的温良性情,洁净无瑕的过往,怎么都极合他的心意。
她怎么看都此汪闲舞那交际花强
至于年纪轻轻就跑到拉斯维加斯诈赌的那个小女孩更甭提了,恐怕连画衣的一根脚指头也比不上。
他一定要阻止轻佻的野女人成为也焰的第三任老婆
“身体好些了吧?可吃可睡吗?”
眼中刚刚打住的水雾控制不了的即将泪如泉涌,倪画衣强忍着,“好多了,谢谢您的关怀。”
其实她是幸运的,哪一个下堂妻能够如她一般的蒙受公公的关怀?像她一样衣食无虞
两亿美金,折合台币六十几亿的赡养费啊
黑也焰是个慷慨的男人,仅仅维持六十九天即夭折的婚姻,“代价”竟是令人咋舌的天大数目。
外人误以为黑也焰错待了她,以至于她在离婚之后数度进出津神疗养院。
但事实往往与流言相惇,也由于黑也焰的行事主风难以捉摸,加上他对流言一笑置之,所以愈传愈盛,版本也多得撩乱人心。
“画衣,你立刻整装到澳洲去,也焰的那间花冈岩平房你去过一次,知道怎么去吧。”他的口吻是命令式的,不带三分商量。
她大骇,“爸爸!我不能…”
“好哇!叫我爸爸原来是叫假的!”
“不!画衣绝对不敢,只是…”
“哼,明知道我的血压高,你这样扭扭捏捏的,不怕我一个脑中风就去天堂喝茶了?”
“爸爸,您别这么说!”他是她唯一的亲人了。幼年丧父,二十岁亡母,她已是孑然一身,无所凭依。只有用之不竭的赡养费…
“我去澳洲能尽些什么力吗?也焰可能不喜欢我的打扰。”
“胡说,也焰一向疼你。”
是呵,当她如亲妹妹一般的疼。这是她的幸运,亦是她的悲伤。
她爱他已经爱了好些年,心里再也容不下第二个男人,即使追求者甚多,她也无法强迫自己移情别恋。
人的不幸通常是自我造就的…
“你不知道,汪闲舞那忝不知耻的女人又黏上也焰了!”
“她和也焰曾有夫妻名实…”虽然只有三十天的短寿婚姻。
“什么夫妻名实,我不承认!”那朵烂花贪求的是什么,他这个老人可是心知肚明,否则十年前他便不会使出杀手锏来斩断他们不该有的姻缘。
“您是不愿意她和也焰旧情复燃?”她很清楚,其实汪闲舞和她一样,攫获不了黑也焰的心。
汪闲舞用孩子得到一个月的婚姻,而她呢,因为老人家的另眼相待,因为京极需要一份母爱,因为黑也焰视婚姻契约加敝屣,所以荣登第二任的黑少奶奶。
倪画衣、深深的叹息。
黑太将气呼呼的大吼,“除了那不知羞耻的汪闲舞以外,还有一个落翅仔!”
“落翅仔?”
“诈赌的小女娃!”八成又是倾心于也焰的酷俊风采和他的赌城王阂。
倪画衣笑了,“也焰的条件一等一,女人对他动情是轻而易举的。”一抹苦涩悄悄地爬上心底。
“你不爱他了?放弃了?”虽然当初会离婚是画衣主动提出的,但他相信她对儿子仍有情。
“我能不放弃吗?”作茧自缚的女人伤了自己,也伤了他人,太不应该。
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剂,孤独的八年岁月使她不得不看透。
她依然爱他,一分不减的深爱着,然而她已经拨云见日,不再困住自己。
“总之,你必须飞一趟澳洲,设法离间也焰和那小女娃初发芽的情苗!我可不允许京极有这样的太妹后母。”
“爸爸,我没这个能耐…”一旦面对黑也焰,她害怕自己的心又控制不住的为他鼓动。
“画衣,好歹你也当了京极两个多月的后母,你狠得下心冷眼旁观京极被虐待?”他抓准了她柔软的善良心肠,心想,呵呵,姜是老的辣。
倪画衣踌躇了。即使京极从未开口叫她一声,也几乎不曾正眼瞧过她,但是她不能任由另一个女人伤害自闭于世界之外的京极。
“我可以吗?毕竟我已不是黑家的媳妇了。”而且她要用什么法子保护京极
将她的犹豫难决看在眼底的黑太将哈哈大笑,好一会他才道:“你当然可以!别忘了你是也焰的前妻之一呵!”最要紧的是他清楚儿子一直对她心怀愧疚,她是钳制住他的绝妙好棋。
扭着双手好半晌,她嗫嚅着说:“我去一趟,但是能不能达成您的交代,我没有把握。”
“只要你去一趟即可。画衣,如果你和也焰能再绩前缘是最好的了,若不,请你协助优柔吧,她一定可以胜任黑少奶奶这个身份。”
“好的。”她敛眉苦笑。老人家真是津力旺盛啊。
黑太将缓缓的咧开嘴角。面色红润的他完全不显龙钟老态,甚至带着些许顽童气息。
他自顾自的得意着,“老谋深算的我怎么可能输这一盘棋?”
澳洲
司徒弱绯打开门,笑着说:“想不想我呀?黑京极。”
想当然耳,小帅哥的金口依然未开。
“可怜的孩子,你一定被那两个唇枪舌剑的女人给吓惨了。”所以不再拿扫帚扫阶梯,也不再到餐厅吃白粥。
黑京极眨着眼,他的嘴唇蠕动了下,欲言又止。
“你是不是想说话?来,试试。”她知道这十年来他除了哭泣和“碰”、“自摸”等等字眼以外,没发过其他声音,她好期待。
“哦…”他发了声,却仍是徒劳无功。
他伤的不是声道,而是一出生即关闭的心门。
“这样好不好,我问话,你点个头或摇头?好歹我们曾经昏天暗地、没日没夜的打了几千圈的麻将。”牌友情谊非比寻常。
怔忡半晌,黑京极点了下头。
司徒弱绯开心的将他抱满怀。
久久,她放开他,喜见他漂亮的脸蛋抹上层微红光泽。
“小帅哥,你是不是和我一样讨厌她们?”
他点了下头。
“你喜欢我吗?还是讨厌我?”
他重重的点点头,又快速的摇摇头。
“是喜欢我喽?”她咯咯的笑,像只小母鸡似的不太有气质。
“嗯。”黑京极低哑着声音,害羞的笑了。
她正想摸摸他的小脸,不速之客却擅自闯入。
汪闲舞带着笑容进房,“嗨!儿子。”
黑京极瑟缩了下,不习惯有人接近,而且她身上浓重的香水味十分刺鼻。
丝毫没察觉他抗拒的汪闲舞仍是笑意满脸,“你一定不认识我对吧?我自我介绍,我就是生你的妈咪,你是我的儿子,这份血缘永远不变。”
黑京极一骨禄的躲到司徒弱绯的怀里,他怕眼前这个脸上抹紫抹红的女人。
笑意倏地不见,汪闲舞提高分贝开骂道:“还是这副德行!难怪我几乎以为自己不曾生过孩子。”
“喂!你别吓他。”有人这样伤害自己的孩子吗?她简直怀疑黑京极不是从汪闲舞的肚皮生出来的。
“干你何…”汪闲舞连忙止住火气,她是特意来笼络这小女孩,可不能搞砸。
多一个朋友总是比多一个敌人来得济事。
她勉强扯出一抹笑,“哎!瞧我这忘性。司徒小姐,我有事和你商量。”
“哦。”安抚好深受惊骇的黑京极,司徒弱绯才走出敞开的房门。
停步于廊道的最底端,司徒弱绯轻吁一口气,“什么事?”快快说完,她好快快闪人。
“我是黑也焰的初恋情人。”她面不改色的说出谎言。这可是她汪闲舞最为拿手的好戏。
“哦。”她很懒得回应,连假笑都免了。
司徒弱绯的淡然,汪闲舞毫不在意,反正她的敌手是另一个该受诅咒的女人。
“你应该明白,男人和女人一样,对生命中的最初总是铭记于心。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不仅仅是前妻,更是他儿子的妈,以及他的最初。”
“你要告诉我的就是你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哈,原来黑也焰第一次的性经验发生在十八岁,未免晚了点。
她粲然一笑,可是却感到椎心刺骨,极想将那个男人拆吃入腹。
她好恨,可是又不能怨他,毕竟他的过去里本就该没有她的参与。
臭火焰。
“汪小姐,请问你对我说这件八百年前的陈旧往事干么?”司徒弱绯并不知道自己这句问话酸味十足。
正沉浸在算计当中的汪闲舞也未察觉她的异样。“要你去对左优柔透露啊!”不必本尊出手。
“说这个?有啥用处?”传声筒这角色太不济了。
“我要叫她知难而退!哼,仗着有黑老头的口头允婚,她还真当自己是未来的黑少奶奶啊!”
“你可以自己去对她说呀。”拉她蹚这浑水?她才不要。
讨好的一笑,汪闲舞爇情的拉起她的右手轻轻拍着。“你是局外人嘛,由你传话,姓左的才会有自知之明。”事实则是当年的黑也焰是个采心大盗,驭女之数足以荣登榜首,她汪闲舞只是他床伴的万中之一。
但是人总要懂得自抬身价。
“麻烦你喽,可爱的小保母,我会牢牢记得你的大功劳,绝对少不了你的好处。”说完便翘着娇婰一扭一扭的走了。
司徒弱绯几乎要尖叫出声,如果她不是用力的咬紧下唇的话。
汪闲舞都这么说了,那她到底算什么嘛
这笔帐,她已经记到黑也焰的头上了,非找他清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