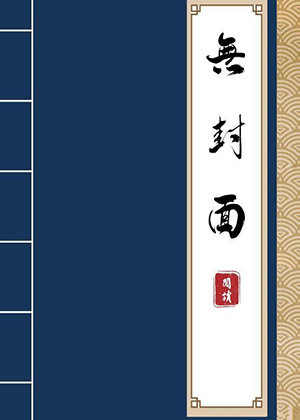俞香兰心悸惊魂未定时,听余姐说弥勒岩寺来了一位云游高僧。高僧之所以高,就在于他可为凡夫俗子们指点迷津。
俞香兰急奔了去,高僧身旁信众不少,容不得她喋叙不休,俞香兰神情恍惚中亦难全盘领会高僧的点拔,但还是记住了他的一句话:“世人若明了断舍离,怎生诸多的贪噌痴?!”
回到家中,她看看何仙公的牌位,又看看手中的念珠,心里不停地琢磨:搞了半天才明白道和佛原来真不是一家。我迷迷糊糊地求了大半辈子,求子求财又求寿,不过是应了一个贪字,有时明知一切皆有定数,却又心有不甘。这儿拜拜,那里求求,均不过无知妄想执念而已。我已活到了黄土埋脖子的份上了,万不能东扯葫芦西扯瓢得个原则。这念珠随时串在手上,遇了事捻一捻珠子,稍能平些气儿,不如就归了一途,从此弃道敬佛,每天诵诵《心经》和《金刚经》,只求平安和顺,其他的都归于歪门邪道,永不再理会。
深夜中的俞香兰依然睡意全无,身边的俞大明呼噜声此起彼伏,而她枕边的那台小播放器里众人齐唱“南无阿弥陀佛”,轻悠绵长,声声不绝。她突然间心绪宁静了下来,此夜安然入睡。
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俞香兰先将俞大明的被褥衣物等收拾一番,拿到了另一个房间,嘴里喃喃地直说:“太累了,该放下了,不贪也不欠了!”
收拾完俞大明的一切东西后,俞香兰请人将何仙公的神位从家里挪了去,毁了所有的香炉和问神掷杯的工具。又在靠西的方位挂上了一张南海观音的神像。在一张八仙桌上不仅摆了崭新的香台,还摆放了几盆塑料花束,看上去格外的令人赏心悦目。花束中间有一青花瓷瓶,瓶里装满了清水。俞香兰每感神情浑沌时,稍稍地拍一些清水在额头,心头立马舒畅开来,比那南洋的万金油还有效,不免心中无比感慨,观音净瓶里的净水确是神水。
俞大明看她好一番折腾,不明事由,但又想她最近的心情必是好不得,就由着她去,不说也不问。
可他自己为基金会的事不免烦恼,忍不住在她身旁叹道:“那个沈书记本已安全上岸,偏偏心大,如今晚节不保,落了个声名狼藉而又无家可归。我一想只觉头疼,为他,也为俪俪!”
俞香兰:“你来试一试观音瓶里的圣水吧!”边从青花瓷瓶里为他倒了一杯水出来,边又说:“喝完了管保马上就轻松神爽。”
俞大明既困惑又不满地说:“老太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服从党的领导,我有权利抗议,跟你的观音菩萨不扯关系!”
俞香兰原还想坚持她的关怀,但转念一想万事皆讲缘份因果,不得囿于勉强,也就不再多话。
俞大明内心里时刻焦虑着基金会的官司,本想跟她多说道说道,可见她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心想她这样也好,人老了就该图个清净心。
他如此这般地调剂着自己的心情,俩人的日子也就相安无事!
过几天就是冬至日,老俩口简单地过节,简单地度日。
这一季的冬天天气奇好,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阳光灿烂。有阳光的冬天本应令人心情爽畅,俞大明却感身处暴冰之天,全身凉透又心急如焚,提着菜篮子往家疾走。
他一进家门见俞香兰正坐读《心经》,几步就冲到她跟前,拔拉掉她手上的《心经》,急急地说:“你快问问建华,他关了养鳖场,在家歇上了,可他什么都不跟咱们交待!”
俞香兰不相信地瞪大眼,:“关了养鳖场?你听谁说的?”,却又本能地已提起了电话筒。
俞大明坐了下来,使劲地喘着粗气,:“刚刚在菜市场遇见了老家的阿木,闲聊中无意间知道了,阿木说建华倒大霉了,鳖死了一大半,剩下的也没人收购,现在天天在家吃鳖,说不知道建华过的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
俞大明说话间,俞香兰已拔通了电话,俞建华正好在那头。
她直接了当就问上了,:“你的鳖场到底怎么呢?才多久前我还问过你,你不都说正常经营么?怎么外头传闻说场子关了呢?”
俞建华的声音宏亮,:“我的亲姑姑,合该我这人没好运气,别人嘬了螺肉头,而我吸了螺尾,却也是臭烂的货,真倒霉!最近我愁得直上火,浑身难受,心想等身子好一点,亲自去您家给您二老说清楚情况。”
俞香兰忽见眼前金星直冒,只得努力撑住不让自己倒下,颤着声说:“我每次问你,你偏都不讲实话,这下可好,只一回就能把我往死里逼。”
俞建秋急促着回应:“姑,您别急呀,您要是有事了,我爸我叔他们不得把我活埋了?!不怨我不勤快,是这老天真不长眼!鳖仔和大鳖都卖不上价,该死的防疫站卫生局,不知关了他们什么事,三天两头地来捣蛋,农业局工商局更来踹一脚,将那场子说封就封了。我一连着求爷爷告奶奶找关系,可那鳖等不及,不给药下就死了一大半。”
俞香兰:“早就想不对劲,可就没想过会闹这一出,封场子的事为什么不跟我们说?”
“我哪敢多说话?只怕您担忧!您老投资的钱,我做牛做马都得还您!”
俞香兰听见俞建华的妻子在一旁骂说:“你就剩下了一条裤叉,做牛做马也是还不起了。”
俞建华发狠说:“这辈子还不了,下辈子还做牛做马还债!我姑的钱我是赖不掉的。”
俞香兰想哭却无泪,开骂说:“你爸和你叔常说你老大不小却还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我本不信,这回信了,你真是不争气!”
俞建华竟突然间哭出了声来,却又压抑着只哽咽着,好不容易又说了句:“我知道自己没本事,愧当俞家的长子长孙!”
俞建华的妻子又在发怒说:“好命的在你这个岁数都快要当上阿公了,可你将儿子娶亲的钱全给败光了!……”
俞香兰被一阵压抑的男人哭声和女人的气话搅得眼前发黑,只好撂下电话。
俞大明气呼呼地说:“我一开始就打心底里觉得不踏实,他说借款却又写了是投资款,说投资吧,又从来不让你说事,分不清是我们是债主还是老板!”
俞香兰心头又泛悲苦,却不甘愿地反驳说:“他原是好心好意的!”
俞大明更生气了:“只有你还觉得他是替你好心着想,我却认为他是窝着祸心。这下子连提起诉讼都无门。”
俞香兰一听,又是伤心又是愤怒,:“你还想着去告他?他就剩了祖屋里现住的一间房,那还是我阿爹南洋回来时建的!难道要让他带着老婆孩子露宿街头?再不济他也是我侄儿,我大哥他还在世呢。”
俞大明:“上回是你亲弟弟,这回是你亲侄儿,不说钱亲不亲,就说到底是孩子亲,还是他们亲?你这是一个肘子往外拐,不怕疼了自己?”
俩人你一言,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俞香兰原本无泪,一吵反而有了泪水。
俞大明吵了几句,觉得心累,:“怪只怪自己太贪,一连几年尽瞎折腾,苦了自己不说,还连累了儿女。”说完后,转身就出了家门。
俞香兰哭了一阵,浑身无力,挪着身去观音像前静坐。
家里寂静得令人窒息。
她打开《心经》,想大声诵读,却无法集中精力,更觉双眼干涩不堪,索性独坐想心事:鳖鱼也是生灵,养大了却要给吃掉,这本身就是在造业障。鳖鱼吃了药,又祸害了更多人,冤冤相报何时了?难怪不得收益。我这几年里确是没遇上几件舒心的事。受亲弟弟的鼓动去投了基砖厂,亏了钱不说,弟弟也再也亲不起来了。原以为海海会是个做事的人,自雅安去了日本后,他回来过几次,看他毫不正经,又成了那个浪荡的二流子,破败之相已现了。俪俪的积蓄无缘无故在我手上了许多,而她也去了远方,其他的人也是如此。若有牵挂,也是徒劳。连大明近来性情也变了,挑剔多了,恩爱少了……俗事种种,让我家财尽散,亲情耗尽,是要让我去得无牵无挂吗?
俞香兰想了想,又痛哭了一场,哭后却觉得轻松了许多,可不舍之情又丝丝泛起,只好竭力让心情平静下来,捧起《心经》大声念诵:……菩提萨陀,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
俞大明走在冬天的太阳下,并不觉得温暖,反而口干舌燥得难受,在街上走了又走,逛了又逛,百无聊赖,却不想找人诉苦,看日早已偏西,只好回转家中。
听见俞香兰在楼上大声诵经,锅灶却冷清,只好上楼去问她。
俞香兰面无表情,语气冷静,:“我想开了,留在这世上的时候不多了,如果再不苦修,真来不及了!从今天起,一心皈依,过午不食了,你以后自己照顾好自己吧!”
俞大明想她还在气恼,自己的一口气也堵了上来,就不吭声,逐走下楼,在厨房里转溜了一圈,又上街去了。
连着几日,俞香兰不停拾掇着她的衣物,俞大明虽有疑问,却又懒得开口,心里记挂起小儿子俞敏海,不知他的养殖场又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