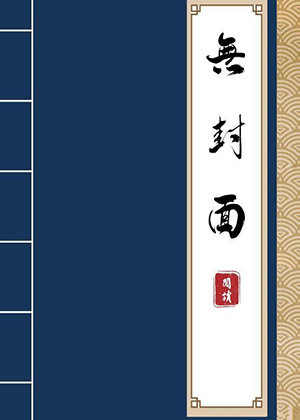俞香兰看了看黄历,发现近几日里竟没有宜嫁娶的吉日,又想俞敏海与许雅安不过是先见过父母,并非正式嫁娶,心中略安。
她放下黄历,见俞敏海拉着许雅安的手又匆匆地出了家门,俞敏俪正抱着一本画满石头的书读得津津有味,而俞大明还在一份报纸接一份报纸地审翻得认真。她只好独自一人到院子里慢慢步,心里却又莫名地隐隐作痛,思想着莫非自己真是老了,不再如往日那般有火火的自信,无法轻易地就可拿捏拍板主意,忍不住抬头看天,日正当午,不禁嗟叹起日出日落只在转眼之间,曾可似勇士般握住似箭光阴,而如今只能保持勇士的姿态目送飞箭逝去。俞香兰忧愁平添,无声无息地呆立原地,忽又转头一想凡人自有烦心事,已恭请了何仙公护宅,不如一心虔诚地听从仙意,省得心头杂乱如麻。如此一念,竟然舒坦了许多。
她有意忌荤,吃了几天斋,买了五样新鲜的果品,在何仙台牌位前焚香祷告。
俞大明见她几天里言语显少,怕她心中又有郁结而平生事端,主动帮她提了果品上楼,在她身后定定地看。
见俞香兰掷了几次杯后,眉头紧锁,俞大明忍不住问:“出什么问题了吗?”
俞香兰:“真奇怪!不知什么意思。我为海海的姻缘掷了三次杯,第一次一正一反阴阳调和,大顺的圣杯。第二次,两正面,普通杯。第三次,却是两反面,笑杯,难道说此事不可为,最好放弃?怎么会这样呢?到底什么意思?”
俞大明心里一惊,忙说:“不明摆着仙公只想回答你一次,见你一问再问,烦你了,给你个笑杯,分明嘲笑你,哪是说要放弃的意思。”
俞香兰神情迷惘,俞大明心中又生不忍,:“你敢再问问?”
俞香兰:“一般问神只一次就好。”
俞大明:“孩子要是不识趣,在爹娘正忙时,问了问题太多太无知,亲爹娘也会烦的。求仙公的人太多,哪能一一给予耐心。”
俞香兰原想反驳他,却也觉无言以对,只好说:“在仙公面前我就是个招烦的无知小孩,我得诚恳认个错。”先正了正身,再屈身跪下喃喃告罪。
俞大明忍住笑下楼。
俞敏俪盘坐在厅里沙发上,抱着一本关于寿山石印章雕刻的书藉,正神游天际地想入非非,想书轩的字体别有一番意象,倒不必强求立宗成派,若能看他以书入画,寓雕成趣,自是此生难遇的幸事。
俞大明走过去坐在俞敏俪的身边,感慨说:“你妈妈也只有在仙公面前才会认错。”随即将刚才的事又述了一遍,俞敏俪笑得直想打滚。
她好不容易止住笑,一看手表,忙说:“爸我得该上课去了!我们总算又有事情干了,海海与雅安的婚礼差不多要筹备了。”
俞香兰又为了俞敏海的婚期选日子尽费心思,可俞敏海自己预先定了“五一”这个大日子,他预计那时第一批鳗苗已成功下池,逢公众假日,恰又是诸事大吉之开端。俞香兰无法异议,看他处置得头头是道,也只好配合就是了。
俞敏海三哥要结婚了!新娘子是学生又是闺蜜,还是自个儿力促而成,俞敏俪投入了十二万分的热情张罗起新房的装饰。
婚房里张灯结彩,彩带串着一张张小小的大红字,绕过墙壁四周,再从边缘结网般地穿梭向中间的白色水晶宫灯。俞敏俪自做主张地选用了玫瑰紫闪亮彩带,宫灯一亮,整个房间紫色光芒闪耀,炫目而又魅惑,这才是世间最浪漫的世界。婚纱照正对着婚床高高悬挂,几帧布质的婚纱画轴挂在了过道的墙上,依偎着的一对新人在画中甜蜜微笑。照片中的许雅安更是精致美丽,在紫色之光照衬下,一袭白色长婚纱裙飘逸着一股迷蒙的仙气。俞敏俪真心羡慕着,心想自己在幸福的日子里也该如此地美丽动人一把,当然,最好那时就直接选一袭紫色婚纱穿上。
俞敏俪陪伴许雅安预约了化妆师,就拉她过来参观已经布置好的新房,以为她会欣喜于小姑子别具新意的选色。谁知许雅安进了新房,定定地盯着婚纱照一言不发,见俞敏俪犹自兴致勃勃,只幽幽地叹了声:“这婚真得要结么?”
“什么话?雅安!我的三嫂!不会得了那什么婚前恐惧症吧?说呀,紫色是不是比红色更浪漫高贵呢?爸爸妈妈嫌说不够喜庆,可我喜欢!”
“我感觉不到浪漫,死了!这几天我只希望自己突然被宣布得了绝症,或是走在街上突然被车一撞就没了。”
“别吓人!原谅你的这份损幽默。”
俞敏俪自顾自地满怀得意,再次浏览一番自己的杰作。
许雅安像是鼓足所有的劲,却又似即将虚脱般地低语:“海海还是那样,身边不缺女人围绕!”
“海海的女人当且仅当就你许雅安一个,丫头!”俞敏俪丝毫没听出许雅安的悲愤。
“不是,在我们回来的前一晚,他喝多了,我发现他的白衬衫领口有口红印!”
俞敏俪回头无声怔怔地望着她。良久,弱弱地问:“不会吧,你问他了吗?他怎么说?”
许雅安摇摇头:“我没问,但它却是真的!”
俞敏俪心里打了个冷颤,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那你嫁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好想有人告诉我怎么办?你说我该怎么办?会是误会吗?”许雅安原先软弱的语气突变得尖锐,:“你说他怎么能这样?”
俞敏俪越发没有底气,:“我以为有了你,一切都好了。”
“他知道我看到了那个口红印,可他若无其事,我希望他跟我解释一下,哪怕他撒谎说是有人捉弄他,可他根本就是不当回事。”两行泪从许雅安的脸庞滑落。
俞敏俪上前用劲地搂住许雅安,有着和许雅安同样的心力憔悴,但又脱口而出说:“心似七巧塔,总会有人被藏在那心尖上而备受呵护,因为那里是最柔软的地方!”
虽然这么说着,俞敏俪却感无限害怕,害怕许雅安将喜庆变成沮丧和笑话,大哥他们都在飞机上了,全家人似乎都希望通过这场欢庆,消弥掉之前所发生的种种不快。记得妈妈也曾言之凿凿说过俞家的男人都是纯情的种,海海哥应不是狂蜂浪蝶,他正用一场盛大的婚礼向世人广而告之他已名草有主,也是他与过去彻底了结的界线。
俞敏俪闭上眼,在心中默默地祈祷。
许雅安哭了一会儿,又感觉难为情,担心俞敏俪跟着难过,于是抽了抽鼻子,拍了拍她的后背,:“我现在好了许多,你不用想太多。我先回家去,还有好多事情,我妈老唠叨说我是家里的长女,她没什么经验,怕一些礼数处理不好,你跟爸爸妈妈解释一声!”
俞敏俪睁大眼,用力点头,心想这会儿该轮到自己感动哭泣。
俞敏海和朋友一起,驾了几部车,从机场接了众人回来,仅除了俞婉娉。
家里的人多了起来,拖行李的拖行李,忙着拥抱的忙着拥抱,俞大明和俞香兰激动万分,不知该跟哪一个先聊上。
俞敏俪不管不顾,只扯着俞敏海上到三楼自己的房间,关紧房门,神情严肃地问:“俞敏海同志,我必须问清楚一件事情,结婚是你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吗?”
俞敏海不解地看着她,伸出手去摸了摸她的额头,又探了探自己的额头,:“还好,没发烧!我以为你生病了,连哥哥都不叫,居然直呼同志,还问了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别打岔,再问你一遍,俞敏海同志,你是不是真心决定要娶许雅安?”俞敏俪不耐烦地甩掉他的手。
俞敏海见俞敏俪目光凛厉,不禁也发了怒:“谁说我不想娶许雅安就是胡说!我要让她成为骄傲的新娘,让所有的人都明白她是我俞敏海的妻子。”
俞敏俪:“俞敏海同志,要知道,人这一辈子的生命很短暂,短得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短得一生做不了几件事。当你做了决定,就不要留给自己和她人反悔的机会。从朝霞到夕阳,绚烂的不过旦夕,学会珍惜!”
俞敏海怒骂:“有点文化就装神弄鬼!”
俞敏俪:“大人的世界里更讲究自律和规矩。比如,不许酒后失态,更不许酒后胡闹!”
俞敏海恍然大悟,:“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这般诈尸了?雅安说了什么?”
俞敏俪:“我记得你说过,如果许雅安愿意嫁给你,你会让她成为百万新娘。”
“我一定做到!”俞敏海一说完就直奔向楼下。
俞敏俪在他身后喊道:“许雅安是金贵的许雅安,你要永远记得,百万才不是什么具体的金额。”
三天后,许雅安的婚礼摆场盛大,热闹隆重又讲究奢华。
宝马车和奔驰车列成一队长长的迎亲车队,红艳的玫瑰花缀满了每辆车的车身,车队沿路撒了许多包装精巧的巧克力糖。两工具车上满载着礼担,那么些贴着大红双喜的大礼盒,被挨个依序地扛进了新娘的家中。
当大礼盒的盒盖被掀开时,一封特制的大红礼帖醒人耳目,内装一张定期一百万元人民币的存款单,许雅安三字名又是如此的惊人夺目,而礼盒里那些被捆扎得结实的活红鲟、活螃蟹,还在喘息跳跃的大活虾,以及生生蠕动的八爪鱼……足够开张几十桌酒席的海鲜生猛,已入不了众人已然被震惊发晕的眼里。
摄影师扛着长长的摄影机,捕摄了太多太多的羡慕妒忌的目光,也摄留了太多太多的惊叹和称赞。
许雅安像盛装的瓷娃娃一般,在众多亲人的簇拥下走下楼梯,俞敏海抿嘴微笑着将手伸向她。
许雅安稍稍犹豫了一下,抬眼看俞敏海,他的眼里满是宠溺之情,一霎那间,许雅安心中突觉安然,缓缓地将自己的手伸了出去。
迎亲车队在乡村的土路上扬起了滚滚尘烟。整个乡村为许雅安的百万存款单和盛大的迎亲仪仗而陷入了沸腾。许雅安的父母在方圆若干公里内的范围内名噪一时,多少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嫁给像俞敏海这样的日本客,多少个少女梦想着有这样的迎亲车队来迎接自己。
俞香兰忙碌不停地周旋在来宾之中。宾客里不乏权贵中的权贵,除了俞敏佳和俞敏洪携回来的外籍爱人,还因了俞敏涛的缘故,市府市委和侨办来了几位领导,而也因为主角俞敏海,来了不少老板模样的人物。领导和老板们腆着的大肚子,无形中壮实了婚宴的气势。
俞大明的老朋友们,那一群已经退休的老革命同志,他们并不关注俞敏海和许雅安在婚宴中究竟换了几套衣裳,新人又是西式又是中式的礼服,惹得许雅安的同学朋友啧啧声起,而老同志们更在意的是俞大明这么个闷疙瘩的人,今朝的祖坟似乎狂冒起了紫烟,熏得让人晕头转向,也熏得令人对他刮目相看。
老同志们争相端起酒杯,哄哄闹闹地誓要将俞大明灌出醉态来,必得让他醉后吐出真言,交待他到底暗中使了什么绝招,才让他的孩子们如此争气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