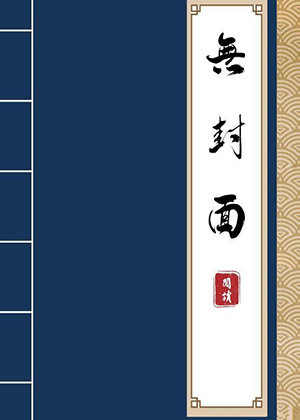俞婉娉不仅不是简单的不快乐,而是到了度日如年的挣扎和痛苦的地步。
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俞敏洪像许多普通的中年人一样认真地拼命工作,他开了家日式料理店,自己担任主厨。观月姿子跟普通的日本女人一样,俨然是一位精致的家庭主妇。
他们搬了住处,不再租房子,而是买了一处房子。
学校、父亲的餐馆和家,三点构置成一个大三角形,将东京都大部分区域纳入其中,可它令俞婉娉心生畏惧,她在三点的移动时间挤掉了每天本该需要的许多睡眠。
她必须每天很早起来为自己准备午餐便当,还得替全家人做好早点。下学后又得马不停蹄地赶往父亲的料理店帮忙。
本来可以转学至离家较近的中学,可俞婉娉的成绩羞于见人,继母姿子就让她留在原校,说是不要轻易放弃难得的同学情谊。
可俞婉娉并不觉得同学之间的情义有多深厚,她们偶尔表现出大惊小怪来,俞婉娉看见了那眼里的刻薄和鄙夷藏都藏不住。
俞婉娉有时想极了母亲刘娜,很想告诉她说,自己早已不在意她身边的佐藤,可每次极度思念时,又忍不住恨恨地想她已不辞而别。恨意生起时,她又开始痛责自己。
在没有泪水的矛盾旋涡中,一根缝纫针成了她的舒缓剂,将它狠狠地扎进肌肤,再缓缓地拔出,自虐的痛楚覆盖了所有的恨与悔。
唯一可牵挂的人是小姑姑俞敏俪,可她却去了赤道的另一边。俞婉娉喜爱她的来信,通篇都是励志鼓舞的话语,虽然空洞无趣,却又亲切眷恋,但很多时候她又无比纠结烦闷,自己并不完全读懂小姑姑的来信。那一句:“我志未酬人犹苦,东南到处有啼痕”,说得真够无聊,要是能有泪水挥洒,何需针刺自愈?!
小姑姑寄来的一枚玉鱼钩一直挂在脖子上,它已是俞婉娉的一道救命符。
每当站在站台上,她瞪着无神的双眼,聆听动车呼啸而来的声响,死命地捏住胸前的玉鱼钩,她克制住自己必须站在黄线的后边再后边。只想她的小姑姑曾说,毛利玉石雕琢的鱼钩代表着力量和果断,意味着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就如同中国的平安扣或日本的勾玉那般有寓意。
俞婉娉边捏住玉鱼钩,边害怕自己会有一份莫名的冲动去奋力一跃,就像只断翅的小鸟,小小的身子瞬间就会飘坠进深陷的轨道。
好不容易熬到了又一个暑期的来临,俞婉娉略松了一口气。她宁愿二十四小时呆在父亲的餐馆里,也不想看见观月姿子那张擦满白粉的脸。
蒋芷萱刚从上海回来,带着俞浅墨姐弟俩,特地来料理店。
俞敏洪忙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蒋芷萱开门见山就说:“墨墨是中学生了,小姑娘已长大了,平时做事挺让我放心的。我和敏涛想让她去上海学习两年。大哥,您看娉儿可以吗?姐妹俩凑个伴挺好,并且娉儿比墨墨懂事多了,有她当姐姐的带着,我更放心。”
俞敏涛低下头,嗫嚅说:“去上海?你真放心?费用不低吧?”
蒋芷萱说得极其认真:“学校规模虽说不大,但是全封闭式管理,我特地去看过了,也问了好些学生和家长,评价不错的。”
俞敏洪双手在身上的围兜擦了又擦,又低声说:“娉儿不如墨墨聪明,成绩也不如墨墨好,她现在上的是公立免费学校,日本学校的教育质量都不错。”
蒋芷萱知道他在意的是费用,:“我们只是希望孩子可以多学习中文,上海学校有更多更好的社团活动。我跟敏涛商量过了,要是娉儿愿意,我们一并付了她的费用。”
俞婉娉为她们端着一壶水过来。
蒋芷萱眼尖地瞥见她半袖遮掩的手臂上布满伤痕,密密麻麻,红红紫紫一片,分明是被针扎过的印迹,看得触目惊心,不禁一愣。
俞浅墨却惊呼了起来,:“姐姐,你的手臂怎么啦?你这是想要刺青吗?可又不像哦。”
俞婉娉掩饰地拉扯住袖子,神色紧张。
蒋芷萱一把将她的手抓了过来,认真端详片刻,目光清凛地瞪向俞敏洪。
俞敏洪一开始不明所以,细看后脸色煞白,无法言语。
几个人一并站着,呆立了良久。
俞敏洪像是刚想起来,急促地说:“我给你们做些sashimi(刺身)。”仓皇地奔回厨房。
俞婉娉忙转身去招呼另一桌的客人。
俞浅墨好奇心陡生,目光跟着俞婉娉转动,俞婉娉紧张憋屈的神情显然。
俞浅墨转向蒋芷萱,娇声说:“妈妈,我也要刺青,刺几片樱花瓣,卡娃依嘤!”
蒋芷萱轻声喝止女儿,:“别不懂事!不许再在娉儿姐姐面前提这些!”
可她又自言自语地说:“该不该管?可我都得管!这真不是闲事!大嫂,你到底在哪里?”
俞浅墨听得莫名其妙,见妈妈脸色肃然,只好另挑话题说:“奶奶要是知道我们吃sashimi,又得念好多佛经!上次我跟她说大姑妈不敢吃生鱼片,她说大姑妈有善根,还说小姑妈有慧根,大伯、我爸和小叔这些人都是劣根。我说他们都是爷爷和奶奶种的根。”
俞浅墨边说边嘻嘻地自乐。
过了一会儿,她又意犹未尽地说:“奶奶很奇怪!最近她不让我叫奶奶,说要叫她做‘居士’,是不是很奇怪?妈!”
蒋芷萱敷衍地应:“不奇怪啦,奶奶已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有她的标准,你尽你的孝敬,小孩子家别多评论!”
俞香兰成了‘居士’,却不是个安静的居士。
俞大明看她整天精神饱满的样子,心情却复杂难表。
他忍不住唠叨几句:“你整天念阿弥陀佛,整天忙着放生,家里一有荤食,你就一堆轮回说,闹得海海三天两头往外躲。不知道雅安到底什么时候毕业,她一找到工作,必须得打得他去日本。这家要是只剩我们俩,你爱怎么吃,我都跟你。”
俞香兰不满地反驳说:“你就一顽固分子!动物本来就有灵性,你们怎么忍心吃它们的肉?人的贪就是一大罪根,你的糖尿病就是贪出来的。吃得太多,胃囊太重,老压着胰腺,胰腺闹了意见,就让你得了病。”
俞大明:“我是说不过你,但年纪大了,饮食清淡为好,一天两餐也不算少了,蔬菜水果多吃更健康!但你不能老爱用你那一套干预孩子。俪俪偷偷跟我说了,她那儿从早到晚不仅一日三餐,还得有上午茶和下午茶,要照你的一天两餐,午后不食,她得每天叫救护车。”
俞香兰急了:“别拿俪俪说事,这孩子从小能听懂花语,她必有慧根,自有她的果报,我不愁她!愁的是海海,明明已经是穷途末路,却一直坚持说他不会再去日本,也不去庆祥仔厂里。如今庆祥仔的设备厂看上去发展得有规有模了,就海海还在嫌七弃八地不找正经事。”
俞敏海回来了,嘴里吹着口哨,看上去心情愉悦。
俞大明忙迎上前说:“今天怎么会这么早回家?”
俞敏海一屁股坐下,晃荡着双脚说:“跟雅安约好了要等她的电话,她去参加了三松公司的实习面试,不知道运气怎样?”
俞香兰突然生气说:“我就恼那个涛涛,一个会挣钱的大男人,放着家里的财政大权不管,由着芷萱任性,又是上海买房,又是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偏就不舍得帮兄弟的忙。”
俞敏海贼贼地说:“二嫂她顾着孩子顾着我二哥的那个家就好,干嘛要让她顾着小叔子?”
俞香兰瞪了瞪眼:“你倒想得开,可我一个半出家的人却替你郁闷得慌。”
俞香兰在恼蒋芷萱时分,蒋芷萱却在忧虑着俞婉娉。
自打从俞敏洪的料理店回来后,俞浅墨觉得妈妈整个人显得神经兮兮,动不动就来一番感慨万千,全是教化她姐弟俩,尽说“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诸如此类的话,令她听着心烦,真宁愿带着弟弟上补习班。
俞敏涛已去了泰国出差好几日。
蒋芷萱一个人在家备感孤独,想跟观月姿子好好谈谈,又觉那不过是井中求火,整个人一筹莫展。
心绪波澜中,她照常为自己沏了一壶茶,茶色虽淡浅清冽,香气却馥郁纯浓。细嗅片刻后,她一口饮完了一小杯,兰花香韵溢满心田,顿觉心舒气爽,心想铁观音不虚声名,独拥了“观音韵”。
曾有记载说福建名茶“铁观音”出自清皇帝乾隆赐名,只因茶叶形似观音之脸重如铁。
蒋芷萱一时间兴致突来,拈出几片茶叶来细细观赏,却并无“观音脸重如铁”的感觉,但观音送子之说却浮上了心头。
她不自觉地攥紧了手中的茶叶,心想俪俪无儿无女,不如将娉儿送到她的身边。只要俪俪愿意,相信遂了多人的愿。
蒋芷萱将茶叶放进嘴里细嚼,一股涩味停留在唇齿之间,等她慢慢地吞下了茶叶碎沫,忽觉口中兰香萦绕,回甘生津。
她打开电脑,心想刚注册了qq号,这回算第一次正式使用,可一看俞敏俪头像黑屏,只好又缓缓地提起了电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