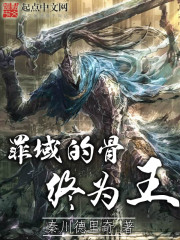"是吗?"阮文邕嘴角扬起一个窃喜的笑意,问道,"那么絮儿倒是说说,这个比絮儿大三岁的男人,是谁呢?"
"大三岁?"阮朱琪摇摇头,道,"我曾以为那个人是三叔。"阮文邕听着阮朱琪的回忆,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可是后来三叔取了晋安公主,四叔又跟我说那个'三';是比絮儿大三岁的意思。"
阮文邕的眼里又升起了一丝希望,但时间不长,阮朱琪很快便扑灭了这一丝希望:"我在战场遇见千傲,他比我大三岁,我也曾一直以为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可是知道一个月前,我才知道,我竟是不喜欢他的。"
阮朱琪说着说着,想到了自己如今的境遇不就是和尚所说的"情路坎坷"吗?不由得鼻子一酸,眼角掉落几滴泪水:"我不喜欢的男人,怎么可能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呢?我到现在才明白,'三';不是三叔,不是比絮儿大三岁的千傲,是絮儿第三个动心的男人,也是絮儿真正喜欢的人。"
阮朱琪看向阮文邕,眼角的泪水越来越多,渐渐汇成一股缓缓流淌。阮文邕心疼了一下,抱住了阮朱琪,轻声道:"不哭,找到了就好!四叔一直都在呢!"阮文邕此刻正盼望着,阮朱琪嘴里说出的那个人会是自己。
然而希望总是用来破灭的,阮朱琪擦了擦眼泪,哽咽道:"可是四叔,等絮儿明白这一切时,宣十度已经不记得我了!他不记得我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阮文邕身上的肌肉瞬间紧绷了起来,她说,那个人是宣十度!阮文邕不知道该怎么掩饰自己的震惊,只能抱住阮朱琪不让她看到自己的脸,生硬地说道:"忘了就说明你还是找错了,再说了和尚们胡言乱语的话,岂能当真!"
无论何时,阮文邕的胸膛都能给阮朱琪温暖的支持。泪水肆意地流在脸上,阮朱琪觉得自己好累好累,就像儿时被徐氏毒打之后一样,慢慢地在阮文邕的怀抱里闭上了眼睛。
"睡吧,四叔在这儿呢!"这句话是多少年来,阮朱琪的摇篮曲。阮文邕轻轻抱起阮朱琪,小心翼翼的放在床上,掖好了被子。正准备脱去外衣,躺在阮朱琪身边陪她一会儿时,何泉忽地跑了进来。
阮文邕冷冷扫了何泉一眼,目光最后落在何泉的脚上。何泉脸色微变,知道阮文邕这意思是说他进来的脚步声太吵了,便小声道:"奴才知错了!"
阮文邕收回目光,轻轻拍了两下手脚乱动了一会儿的阮朱琪,声音温和地说道:"好好睡吧,睡一觉什么都好了。"阮朱琪最终安静下来,再无动作了。
阮文邕走出寝殿,背对着何泉,冷冷问道:"什么事?"
"回陛下,白塔寺有一个高僧求见陛下。"何泉暗暗擦了擦冷汗。
"哦?可是一个叫慧觉的和尚?"阮文邕语气里的冰冷,让原已紧张不已的何泉不禁打了个寒战。再偷偷瞄看阮文邕的脸色时,何泉更是惊骇,此时阮文邕的眼里已露出的杀意。
"把齐东叫过来!"何泉心里发怵,要知道,现如今僧人无论是在民间还是高官贵族之间,都如同神祗一般,可阮文邕召齐东前来的意思,莫不是...何泉虽是觉得心里不安,但也不敢违逆阮文邕。
慧觉在偏殿东看西看,惊叹于皇宫里的宝贝的数量和质量,都远不是外面能随意看见的。慧觉暗喜:"想不到当年收了点小银子,替人家扯了个慌,如今还能再来抱大腿!"
慧觉的目光流转于五光十色的瓷器和玉器之间,时不时伸手摸一摸,敲两下,暗想着等会儿见到了阮文邕,说不定能将这里的某一样带回去。寺里的青灯苦佛岂有这些珠光宝气的东西吸引人呢!慧觉想了想,若是阮文邕赏的东西多,他倒是可以考虑还俗了。
阮文邕进殿有一段时间了,可慧觉的注意力完全被宝贝们吸引,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屋里来了人。"咳咳..."何泉见状,连忙假意咳了两声。
"皇上驾到..."何泉尖着嗓子喊了一声。
慧觉转过身来,眼睛放亮地盯着阮文邕,一时间竟连礼都忘了行。
"大胆!见到陛下还不跪下行礼!"何泉见慧觉呆滞的模样,生怕阮文邕大怒。
"贫僧慧觉见过皇帝陛下!"慧觉立刻双手合十,行了一个僧人的礼。礼毕之后,慧觉依旧是眼角带笑地盯着阮文邕,好似盯着一个大元宝似的。
阮文邕似是和睦地回了慧觉一个笑,慧觉大喜,却将何泉惊得不行。何泉跟随阮文邕这么些年,阮文邕从来都不对外人露出笑脸,除了阮朱琪。何泉又惊又疑,再细看阮文邕的表情时算是恍然大悟,这笑意里的杀意全隐匿在了眼神里。
然而慧觉却没有这等觉悟。
"一别十数载,想不到阮文四公子如今已是人上之人,真是可喜可贺啊!"慧觉笑眯眯地说着奉承话,算是在跟阮文邕套近乎。
阮文邕淡淡地回道:"朕也没想到,大师还能在白塔寺混下去。"
慧觉脸上的笑容尴尬了一下,干干地回答道:"一切都是托陛下的洪福。"
慧觉见阮文邕一时间没有再说话,生怕自己失去了这个大好机会,连忙说道:"当年陛下托贫僧向絮小姐,也就是如今的长公主殿下旁敲侧击的一句话,也不知帮到陛下了没有?"
何泉在阮文邕身后明显听见了一阵关节的响动声。阮文邕说道:"朕让你告诉她,有缘人就在身边。你是怎么告诉絮小姐的呢?"
慧觉闻言一惊,心道阮文邕这话难道是责怪自己说的还不够明显?便急忙解释道:"佛家有云:天机不可泄露。是以既是要贫僧告诉絮小姐命中的有缘人,自然不能说的太多。况且当时是独孤夫人带着絮小姐一起去的,独孤夫人是多年虔诚的信女,贫僧若是直说,定然会被独孤夫人所怀疑。"
"所以你就只给她说了个'三';?"阮文邕上前伸手掐住了慧觉的脖子,脸上表情有些狰狞,眼里的怒火让人不敢直视。
慧觉立刻腿软,整个身体几乎是被阮文邕提着,紧张地吞吞吐吐地说道:"陛下比絮小姐...比长公主...大三岁,所以...贫僧给独孤夫人做了这个手势..."
慧觉颤抖着手,手指的肌肉抽搐着慢慢摆出一个"三"的手势。姿势还没有摆完,只听得"咔擦"一声细响,何泉瞪大了眼睛看着慧觉倒在地上,没了呼吸。
"陛下..."何泉顿时觉得一阵腿软,这是第二次他亲眼看见阮文邕杀人。第一次杀的是易萨保,可这一次杀的是个和尚!在何泉以及普通老百姓的眼里,和尚就等同于他们所信奉的佛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但阮文邕竟然杀了他!
"承明殿所有的和尚,都格杀勿论!从今天起,但凡我北周的领土上,不许出现和尚的身影!。"阮文邕慢慢从慧觉的尸体上收回目光,看了看自己的手,嘴角微微瘪了瘪。这双手,似乎已经杀了很多人了,可这些人算得了什么?
"陛下..."何泉一听这与佛为敌的旨意,平时的轻言细语的态度都抛之脑后了,急忙向阮文邕劝说道:"陛下,此举不妥啊!单单只是长安城中,佛寺就有数十所,僧众之多,占了全长安城人口的五分之一。陛下难道要将这些人全杀了吗?"
阮文邕将手背在身后,道:"给他们三天的时间,要么还俗,要么滚出北周。三天之后,但凡有穿僧衣的人,统统杀掉!"
阮文邕回到寝殿,床上的女子已经熟睡了,睫毛上挂着的泪水随着呼吸一一上一下地在空中扑动。阮文邕心中一滞,这场景见过很多次,只是之前都在儿时。她受了委屈便哭着来找自己,然后在自己怀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委屈?阮文邕心里的苦涩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刻意安排她出去走了一圈,以为可以让她尝尝苦头便回来,然后便能将她永远拴在自己身边了。阮文邕自信,这世上,没有人能比自己对阮朱琪更好。
她走的时间比自己预想的要久得多,久到阮文邕悔恨了千百万次,不该让她出去。尤其是在看见她回来之后,这个悔恨像是断肠的毒药一般,疼得阮文邕没法呼吸。
因为她回来了,不是因为尝到了苦头,而是为了另一个男人...高纬。
"宣十度...宣十度..."阮朱琪的梦话给了阮文邕更重的一击。
入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昨个儿北风一阵肆掠,雪花总算是姗姗来迟地飘落下来了。宣十度坐在庭院中煮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桌上刚剪下来的梅花沾上了一层雪。烟雾朦胧中,开水沸腾,宣十度引水泡了一壶茶,瞬间茶香四溢。
簌簌的落雪声中似乎还夹杂着别的什么声音。宣十度捧起梅花的花枝,轻轻抖落上面的积雪,说道:"茶都泡好了,邕皇既然来了,就过来喝一杯吧!"
踏雪声渐渐靠近,白茫茫的一片雪中,走出来一身镶金黑衣、披着黑色披风的阮文邕。不太远的距离,阮文邕却走了格外久,久到宣十度已经是第二次将花枝上的雪花抖落了。
"请邕皇喝杯茶真不容易,喏,茶都快凉了!"宣十度放下花枝,指了指阮文邕面前的一盏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