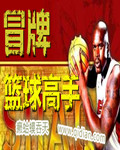这么想着,再往邢德全身后看了一眼,邢芸笑盈盈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去,邢德全竟是一个人来的。
邢德全见邢芸脸色不太好,倒也极乖觉,上前向邢芸请了安,便垂手立在一旁不说话,瞧那模样,竟是连头也不敢抬。
邢芸见着邢德全这样,心里略舒服了几分,看这样子,邢德全如今还不是原著里那个只知吃酒赌钱,丑态百出的傻大舅,因而说道:“你怎么也不带个小厮长仆出来?大冷天的,外头人又多,万一叫什么人碰着撞着了,可如何是好?”
邢德全规规矩矩地抬起头,看了邢芸一眼,才闷声道:“原有一个小厮跟着,因来府里,就命他回去报信了。”
邢芸柳眉一拧,才一个小厮跟着邢德全?她知道送回去的银子不可能完完全全用在邢德全身上,但是这漂没也太过了,差一点就赶上大国印度了。
邢芸压着气,又笑问道:“前儿你二姐托人来说,你已入学读书了,在学里可还习惯?”
邢德全犹豫道:“学里……”
邢芸冷了脸,问道:“学里怎么了?”
邢德全这才说出来,原来邢德全入学得晚,又不曾怎么启蒙,进了学里,未免跟不上进度,先生虽然有教无类,但学里那些同窗多是些小孩子,懂得什么,见得邢德全年长许多,却因自幼养在家里,不大与人接触,显得呆笨,便发着性儿捉弄邢德全。
邢德全起先还谨记着家里的教训,不和那起淘气孩子计较,谁知他越是退让,越是被人欺负……邢德全也不是没告过先生,只是不告还好,一告先生,越发被人孤立欺负,先生管束也无多大用处,而且邢德全入学晚,学业也不见上进,先生也不愿多理会这些。
所以,邢德全心里一鼓气,索性就跑来找邢芸了。
只听得邢德全一边哭一边哽咽道:“我不是不想读书,可每天不是书被人撕了,就是笔不见了,我也告诉过二姐,二姐只骂我废物,连个书本也看不住……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我不想再去那念书了……”
“不去那,又去哪儿?京里的学房虽多,也不是能由着人尽着挑选的。”邢芸在前世好歹念了十几年书,也知道学校里那些事,像这种校园欺负事件,老师管得严呢,动辄请家长退学呢,倒能压服住那些淘气学生,若是老师手软呢,那些熊孩子结了伙,什么奇葩事情都做得出。
撕书打架偷东西什么的,还算是普通的,邢芸前世才念初中时,刚巧学校里出了一件人命案,死的是个初三女生,死因是自杀,不过不是因为什么学业压力,而是因为得罪了当时同年级几个混混女生,那些女生看她不顺眼,就找了几个初二和社会上的无业青年,把她□了……当时媒体不发达,受害人家长也觉得出了这样的事儿脸上没光彩,所以轻而易举便被压下去了。
但学校还是狠狠整治了一下校园秩序,那些不爱学习爱惹事的所谓坏学生,基本上都被学校劝退学了,校园风气算是有了极大的改观。
所以,邢芸的初中生活,还算平静,况且邢芸的性格也不绵软,谁要是敢欺负她,她绝对会报复回去,就算人多了打不赢,也会揪着其中一个下死手打,于是,在隔壁就是监狱和技校的普通初中,邢芸顺顺利利考上了重点高中,从而告别了以盛产不良青年和从军预备队而出名的初中校园。
因此,邢芸看在在眼前哭的邢德全,既理解又生气,理解的是邢德全的情绪,生气的是,邢德全居然这点耐压力都没有,撕书丢笔,算个屁大的事儿,打听清楚是谁撕的,谁偷的,再依样还施回去不就成了。哭有个屁用,能把书和笔哭回来不成?
至于同窗不理他,邢芸更是无语,这世上男女一见钟情的还少之又少呢,何况是别的关系,不想被孤立,自个找突破口啊,要不下死力气学习,学业上进了,自然先生喜欢,同窗想欺负孤立,都没那个胆量。
要不弄点吃的喝的,努力打入同窗中的小圈子,又不是万人迷,要人人都喜欢,有那么几个能说得上的朋友,不就成了。
情商不行,智商不行,一遇事就知道回家在家人面前哭,这样的人有什么能耐?
日后就是侥幸得了功名,做了官,衙门里的小吏不好相处,也回家哭不成?
又不是没断奶的小屁孩!难怪邢夫人在原著里心理变︶态,夫家娘家没一个能扶起的,邢夫人作为一个深宅夫人,除了两眼朝钱看,为自己做点老了以后靠钱度日防身的打算,还能怎么着?
脑子飞速闪过这些念头,邢芸看着邢德全掉着两泡鼻涕的模样,又说道:“本来呢,给你在家单请个先生,也不费多少银子,只是咱们家里又无管事的男子,便有那渊博雅正的先生,也未必肯上门来做西席。就是有那肯上门来的,咱们家里那些人都是些粗识文字的,先生教的好与不好,也看不出来,万一遇上个闷头讲课不管不问的,耽搁了你的前程不说,将你教成了个木胎泥雕,不通人□故才是悔之晚矣。到底要立些根基,学个榜样才好,为这个,我和你二姐才送了你去学里读书,你如今既说学里的风气不好?想必心里已有看法,要选个什么样的书塾,若说得有理,我这做姐姐大不了费些心,替你再寻个书塾,也省的日日牵心挂肠,唯恐你被人引诱坏了。”
邢芸这一番话说出,邢德全心里倒自在了几分,用袖子抹了抹脸,抽着气嘟嚷道:“我也不知道要什么样的,只要不被欺负……府上不是也有念书的地方,我去那读也一样……”
去贾府家学念书?邢德全不亏是原著里的傻大舅,提的主意也是傻到家了。
贾府家学是个什么地方?就是给贾府子弟免费吃喝,顺道着结交契弟,行那龙阳之事的场所,至于读书,用宝玉的话说,还是不提为罢,省得脏了这两个字。
当然,邢芸穿越以来,为着种种目的,也用各种方式推动着整治了几次家学。但是,就如贾府的烂,是从上到下烂透了根的,专供贾家族里子弟读书的家学,其糟糕程度也是难以想象的,要把这些从根子已经长弯了的学生,重新扳正过来,所需要付出的金钱和重视,是贾府管事的老爷们给不起也不愿意给的。
邢芸推动的几次整治,充其量,是让那些族里子弟知道,家学还是有人管着的,不敢在学里闹腾太过分而已。
正是因为清楚这些,邢芸才不让贾琮去家学念书,而是特特挪出屋子,请了先生来府里教贾琮。
贾琮这个庶子,邢芸尚如此慎重,邢德全这个和邢夫人有血缘关系的弟弟,邢芸更不可能轻忽处置。
须知邢芸一入修途,冥冥之中,便有所感,自从她得了邢夫人的肉身那一刻,便染上尘世因果,如非了结这些因缘牵扯,否则即便她心无二用,一念不生,功行之时,依旧有魔头杂念,纷至袭来,伺隙相侵,略一疏忽,轻则功亏一篑,严重时,走火入魔,元神受创,就是转世重修,亦难成就道果。
因此,邢芸才会漫使银钱,由着邢家人予取予求,在她看来,金银这等俗物,不过泥土石头一般的东西,能用金银这种人间物事,了结一部分与邢家的因果,对她而言,已是再便宜不过了……
所以邢芸是绝不肯让邢德全到贾府家学念书的,这倒无关教学的好坏,实在是家学中贾家族人太多,邢德全一去,难免生出枝节,长此以往,因果纠缠,越难了结。
“家学?”邢芸嗤笑一声,骂道:“你当那家学是什么好地方?我提起来就恶心!”
看着邢芸变了颜色,邢德全一脸委屈,拿袖子抹着眼,一副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
桂叶木香原都是邢夫人从邢家带来了,知道邢家就邢德全这么一条根,又因邢芸与贾母已是水火不容,膝下只一个女儿,若是与邢德全再一生分,真个是婆家娘家无一能靠了。
因此,桂叶忙走上前,拿出帕子替邢德全擦了擦泪,笑劝道:“全哥儿有心向学原是好事?只是府里的家学,确实不是个好去处。全哥儿你想想,太太和你是嫡亲的姐弟,万不会存心害你。”
听着桂叶说了这话,木香也哼了一声,不满道:“可不是,那学房里本就是贾家族人和亲戚附学的地方,太太原先也想着,这府里的学房到底是姓贾,倘或全哥儿在家学里念书,便是学里有什么事,太太不问也能知道些,倒比外头的书塾妥当。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家学早和个戏园子差不多了,那些儿族里的远亲子弟,若长得略好些儿,到了学里,竟成了那些粉头一般——”
“木香!”桂叶忍不住喝了一声,淡淡的责备道:“这也是你能说的。”
木香被桂叶这一打断,也醒过来自己失言了,只是她性子倔强,仍旧放低了声音,嘟囔道:“本来就是,我又没说错。先前秦家哥儿来咱们学里读书,为这些事,不是很闹了一回,听说连宝玉也打了呢?府里那些小人本就瞧咱们太太不顺眼,全哥儿若进了府里学房,不是由着人打骂吗?”
桂叶看着木香瞧着这不服输的劲儿,深觉头痛,又看着邢德全听了木香的话,很有些有些抬不起头来的模样,只得叹了口气,向着木香说道:“你没说错,可就是没半点忌讳。”
木香越发不服气,嘟着嘴就欲反驳两句,却不意邢芸瞄了她一眼,只得憋着气忍下来。
桂叶见木香不吭声了,又拉了邢德全哄了几句,将邢德全劝服住了,才向着邢芸笑道:“方才太太还说要给姑娘取小名儿呢,如今全哥儿在这儿,何不就让全哥儿给姑娘取一个?”
邢芸听了,微微一笑,说道:“让全哥儿帮着取一个也好?……等她日后长大了,若是怨着小名儿不好听,也碍不着咱们,只好找她舅舅哭去。”
几只白鹤悠闲地在池边漫步,两对鸳鸯在水中梳拢着羽毛,一个梳了双环头戴红花的小丫头蹲在水池边,一拨一拨的弄着水玩。“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其他侍候的人呢?”
小丫头不提防背后有人,慌忙站了起来,不料脚下踩着一块石子,往前一滑,一脚便迈进了水池里,身上的裙子连带着湿了大半扇。
那小丫头好悬没跌进池子里,正庆幸呢,低头见着裙子湿了,忍不住就红了眼圈,想要恨骂两句,可看着来人又不敢,只得抽泣两声,抬头看着来人行了礼,哽咽道:“翠云姐姐。”
来人正是邢芸身边的丫头翠云,见着那小丫头一副眼泪花花似被她欺负了的模样,翠云没好气道:“又没人欺负你,你哭什么,不过是条裙子,湿了就湿了,回去换一条就是了。”
那小丫头低头提着裙子,细声细气道:“这是我得的第一条新裙子,才上身就弄湿了,干妈知道了又要说我了。”
翠云也知这些小丫头不易,一时笑了笑,看了一眼那小丫头的裙子,说道:“这有什么,这裙子是细布的料子,花样也老着,便是新的也不值当什么。我记着府里分发下来的衣裳,可都是绸缎做的,怎么你竟没得么?”
小丫头低着头蚊呐般的哼哼道:“得是得了,干妈说我又不在主子跟前侍候,也用不着,就都收去了。”
翠云眉头一皱,问道:“你干妈是谁?”
那小丫头飞快的抬头看了翠云一眼,抿了抿唇,小声道:“我干妈姓……是奶屋里宋妈妈的侄孙媳妇。”
宋妈妈的侄孙媳妇,翠云寻思着,忽而一张尖酸刻薄的脸跳了出来,一时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冷笑说道:“我说是谁,原是宋海家的。怪道这么有能耐,太太三令五申的那些规矩,她都能当了耳旁风去。”
原来这小丫头的干娘宋海家的,正是前些日子那个当面讽刺翠云勾引贾琏的管事媳妇,虽然当时翠云被人劝住了,不曾闹到邢芸跟前,但翠云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折了面子,心中岂有不记恨的,如今既拿住了把柄,自然是要好好做一回文章才能罢手。
因而心中衡量了一番,翠云暂且不露声色,安慰那小丫头道:“我那还有几条裙子,原是我的份例,因我不爱那花色,所以一直未上身,过会我命人给你送来。”
那小丫头听见这话,倒很有些受宠若惊,慌忙推辞道:“我怎么好要姐姐的衣裳?”翠云拍了拍那小丫头的手,笑道:“我若不在背后唤你,你也不会弄湿了裙子?给你这些裙子,也算我陪个不是。”
说着,翠云故作生气道:“还是说,你嫌弃这些裙子原是按我的身段做的,所以不肯要?”
那小丫头越发惶恐不已,连声说着不敢,忙忙乱乱地解释道:“不是,只是姐姐给了我,自个又怎么办?”
翠云一听就忍不住笑了,掩口道:“你这妮子?我便留着这些裙子也是白放着。我虽不出众,到底是在太太跟前走动,时不时能得些儿主子的赏赐,哪少得了衣裳穿。再说,这段时日,因太太娘家有喜事,我们这些跟前人没少得好处,就是上用的缎子,太太也赏了好些下来,岂是府里的份例能比的。”
那小丫头听着翠云这么一说,很是羡慕,一脸向往道:“难怪那些姐姐们都愿意到主子跟前去,原来除月钱涨了,还有这些好处。”
翠云素来心思灵巧,听得那小丫头认了干妈,便知这丫头是外头买来的,所以才不知这府里的情况,又恐那小丫头由羡生妒,反倒不好,因而又笑道:“我得这些算什么?现放着天大的好处,你也没瞧见呢。”
说了这话,翠云瞧着那小丫头一头雾水,似有些疑惑不解,又不免细细分说道:“你守着的这院里,住着的是春柳瑞秋二位姐姐,她们俩可是太太打娘家带来的陪房丫头,你若侍候好了她们,她们在太太跟前略提你几句,比什么都中用?”
那小丫头听得这话,倒笑了,说道:“姐姐这是哄我玩呢。我干妈早就说了,屋里这两位姐姐都养了几年病了,也没见太太唤她们回去,怕是早在太太跟前不时兴了,让我远着她们些,不要没得好,反得罪了人去。”
翠云微微尴尬,只是面上不显,强说道:“你干妈知道些什么?这两位姐姐若是在太太跟前不时兴了,太太又何必打发我送东西来。你没瞧见,这府里的人但凡得了病,都得挪出府去,唯有这两位姐姐,眼瞧着得了恶疾,太太还打发人收拾了院子好生照顾着的。”
说着,翠云看着远远的有人来了,也无心思再絮叨,便直往屋里去了。
话说凤姐往贾母跟前侍候去了,平儿却不曾偷得半刻闲,原来凤姐儿这一不在,那些执事媳妇们,唯恐出了纰漏,大小事务尽烦着平儿示下,才肯发放了去。
平儿原是凤姐儿的心腹帮手,怎不知那些执事媳妇心中主意,只是她天生好性儿,又爱做些好事,不得不受些辛苦了。这一时林之孝家的进来回话,平儿便吩咐道:“方才奶奶说了,眼瞅着天气渐渐冻起来了,该做的大毛衣裳怎么没影子了,别是林大娘你事太忙,就不上心了,转头老太太若是问起来,让林大娘你自个去交代呢。”
林之孝家的一听平儿这话,再是装聋作哑,也藏不住了,忙陪笑道:“平姑娘行行好,帮我在奶奶跟前分辩分辩,实在不是我不上心,这外头不给毛皮,我便是再有本事,也变不出衣裳来啊?”
平儿一听,扑哧一声,便笑了出来,看着林之孝家的说道:“林大娘这话,好没分寸,你也是府里的老人了,这衣裳月例,皆是旧有的例,又不是我们奶奶心血来潮的主意儿,怎么又说上给不给毛皮了?亏得奶奶不在这儿,若在这儿,你也敢这么回?”
林之孝家的脸上被说得红一阵白一阵,叫苦道:“奶奶既吩咐下来,我们哪有不紧着办事的,不知催了多少遍?可外头办事的人说,今年添得用项大,偏只有出的没有进的,不比往年,存着的东西便用不完,份例上要用的毛皮,只有等着庄上送年礼来才有了。平姑娘,你说说——”
林之孝家的一语未完,就听着外头有人问好道:“翠云姑娘怎么过来了?”
平儿听见外人来了,也懒与林之孝家的计较,故说道:“奶奶何尝不知今年外头使费大,可再是饥荒也没得在这上头克扣的。趁着奶奶还没回来,林大娘且受些乏,出去再问问吧。”
“呦,今儿奶不在,平姑娘也拿起主了,好生气派呢。”
看着翠云进了屋来,平儿忙站起身来,让翠云坐,又打发了小丫头端茶来。
翠云懒懒散散的摆摆手,看着平儿道:“不用忙,我站着说几句话就走。”
平儿眼皮子一跳,忙笑道:“什么要紧的话,你且说来听听。”
翠云便将先前撞见的事儿告诉了平儿,又说道:“平姑娘,你也是有眼睛的人,以前为这些事,太太不知发卖了多少人,我我知道你是个爱做好人的,这事你必定也知道,只是别人一求肯,你就碍着脸儿不吭声了。可你也不想一想,你不吭声,我还能装不知道,别说我今儿撞见了,就是我没看见,日后闹出来,我也不能得清净。还请平姑娘你行行好,做好事前先想想我们这些无辜人?我再不得用,也是太太跟前的人,太太生气发怒,我又能得什么好儿。”
平儿被翠云这一番话直气得肝痛,要说平儿自打过了明路,一直被人捧着,就算是凤姐儿和贾琏两口子闹起来,也不曾向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叫她没脸的。
平儿何等人物,纵是谋算胜过男儿的凤姐儿,亦视她为心腹,容她在府里各处施恩,上至主子下到奴仆,无人不道她的好处,如此周全玲珑,岂只是寻常人能做到的,如今翠云欺到跟前来,平儿岂有那么容易就忍气吞声的。
只听得平儿怒形于色地吩咐丫头道:“去,把宋海家的叫来。我倒要问问她,她算什么东西,能让我替她担着?一个高枝儿爬不上的主儿,尽往坑里洞里折腾把戏的野奴才,平素勾三搭四的也罢了,如今竟拉上我了,我可是个干净人,由不得她攀扯。”
翠云存了心要借平儿的手报复一番,不料反得罪了平儿,越发没得好处,脸上也不甚好看起来。
亏得翠云心性不同寻常人,饶是被平儿指桑骂槐,只脸儿红了一红,便无事人似的,向着平儿讥讽道:“往日太太常说,奶原是个好的,就是未免太心慈了些,让着身边那些贱婢都欺到头上了。亏得她是继婆婆,眼不见为净,要是嫡亲的婆婆,只怕早抱怨上了。也是咱们家规矩松,要换了别家,那起子贱婢早不知被卖到什么地去了!”
翠云最是个不怕闹大了无人收场的主儿,横竖她是邢芸跟前人,只要抓得住理儿,闹破天去,也没人敢找她麻烦。翠云心里可拿准了,如今府里正有喜事,二房一风光,府里那起子难免眼热拢了过去,太太早有意立一立威,也杀杀二房的风头,她闹出事来,正好说是为太太出气。
至于平儿的体面,翠云全不放在心上,不过一个通房丫头,便是体面,还能体面过她这个太太跟前人。贾府里可早有规矩,长辈跟前的猫儿狗儿,都不能轻易待之,就是凤姐儿见了她,嘴里也得尊重些,何况平儿这个丫头。
好在去请宋海家的丫头婆子回转得快,倒叫翠云这一番算计都付了流水,看着平儿忍气吞声,委曲着处置了宋海家的,翠云带着些许不痛快又坐了一会儿,才慢悠悠的往回走了。
看着翠云花枝招展的摇摇去了,凤姐儿房里的丫头忍不住啐了一口,骂道:“什么太太跟前人?太太跟前,她算哪根葱啊?也是奶奶不在,欺着平姐姐好性儿,要是奶奶在这,早两巴掌赏过去了。”
平儿忍了忍气,微微一笑,翻着账本道:“你气什么,眼下再猖狂,也难保日后如何,日子长着呢?还不知谁能笑到最后呢。”说着,平儿隐约觉得话儿不对,又转了话锋,冷言道:“再说,若不是宋海家的这个没出息的,又岂有今天这桩事?她倒能干着,拿了丫头的月例不说,连衣裳也给剥了,她不要脸咱们还要体面,传出去了,好听着呢。今儿我撵了她,也算是全了情面,要是奶奶知道了,依着性子,非发卖了她不可!”
到了院中,翠云正要进去,只听屋里有人说道:“姐姐的女儿自然是金贵,京中如今又有风俗,女儿之名亦从弟兄之字命名,府里虽不讲究这些,依此取个小名倒也使得。我看,不如用瑶字,瑜字或瑛字命名……”
邢芸柳眉一皱,淡淡一笑道:“这几字做何解?”
邢德全抬头看了邢芸一眼,小心翼翼道:“孔传有云,瑶,琨皆美玉。礼记上说,世子佩瑜玉。瑛,玉光也——”
邢芸沉下脸来,打断邢德全的话,不耐烦道:“你也玉他也玉,浑似这府里得了玉的便宜,况沾上这个姓,便是美玉也和石头一般,倒不若取个别的。”
邢芸心里微微烦躁,隐隐约约有种不祥的感觉在身边环绕,本来,贾这个姓就不大好听,取再好的名,都糟蹋了,看这一府里假环假琮假琏……活脱脱一山寨批发市场,姓不好,名字再好听也无用。
一想到日后女儿一出门,人家一长口,贾姐姐,邢芸就郁卒了,这称呼和史姑娘差不了多少,难怪贾家和史家是姻亲,姓都这么有特色也不大好找。
邢德全思量了一番,又说道:“懿字如何,懿,美也,又有一说,懿,从壹,这是姐姐第一个女儿……”木香听了,拍手笑道:“这名字好,一听就是好名字。”
邢芸蹙了蹙眉,字倒是好字,可惜怎么听怎么不大吉利,邢芸记得前世看宫斗文时,谥号里有懿字的妃嫔很有许多,好像,好像,祸国殃民的西太后,以前就被封懿贵妃。
邢芸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画面,这是空间文转宫斗文的节奏吗,她很无能的,养不出什么奸妃来的,嫖皇帝找真爱什么的,实在很尤三姐好不好?
邢芸吐槽着,正想否决这个名字,可一抬眼,才发现邢德全偷偷伸手擦了擦汗,心下晒笑,她穿的这时空,西太后的祖宗还在关外当野人呢。
虽是这样想,这字到底不太和邢芸的性子,故而邢芸又笑道:“这字固然不错,你再想几个,我送去让你姐夫挑一挑,万一合了我的意,他却觉得不中听,也是不好。”
说着,便让桂叶取了笔墨来,让邢德全又写了几个字,差人给贾赦送去。邢德全一见邢芸让人取了笔墨来,便知邢芸起心要考校他的书法,也不多言,专心致志的挥毫写下几个字来。
桂叶送呈邢芸,邢芸看了一看,无非是婉,嬿,秀之类寓意美好的字眼,便也不再多看,吩咐桂叶道:“叫人拿给老爷看吧。”
桂叶撩开帘子出去,正要打发小丫头送去,翠云忙走上前来,殷勤的笑道:“桂叶姐姐,可是要送东西,我替你送去吧?”
既有人愿意帮忙跑腿,桂叶也省了心力,何乐而不为,于是笑着将东西递给翠云,温言道:“有劳妹妹了。”
送了东西出去,邢芸又让人搬了凳子来让邢德全坐下,有一句没一句的问着些家常,邢德全也就含含糊糊地答着,无非说些吃的穿的都还够,不必邢芸操心的话。
不过一会子,翠云便回来了,笑说道:“老爷瞧了全哥儿写的这些字,说用来取小名倒浪费了,取做大名还好些。从了姑娘们的字,给姑娘取名为憶春。”
憶春,还好不是咏春,或者丽春。邢芸微微松了一口气,这名字要是取成了张国师版本的金陵十三钗中那位,哭都没处哭去……因此,虽不怎么喜欢这个名字,邢芸倒也没说什么,她本就不想把女儿留在贾家,日后出了贾府,自然是要女儿随她更名换姓的,现在贾赦取的这名字,她压根没打算用!
看着邢芸脸色不大好,翠云心里一咯噔,忙又上前笑说道:“老爷知道全哥儿在这儿,还让我送了点心过来,说是宫里赐下来的,让全哥儿尝尝。今儿他还有事,务必叫全哥儿留着吃了晚饭再回去。”
邢芸知道贾赦在外人跟前这些礼数是不差的,若不是摊上贾母这样的偏心眼母亲和王夫人那般多心算计的弟媳,存着心要坏了贾赦的名声,依贾赦接人待物的行为,在京里,就算混不上端方君子的声名,也落不到好色小人的地步。昔日林黛玉进府时,贾赦不论想不想见,好歹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出来,而贾政,却是只言片语都不曾留下。二人的为人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邢芸不管贾赦心里怎么想,横竖传来的话,倒也顾全了体面,因而便嘱咐桂叶泡了茶来,劝着邢德全吃点心。
一时桂叶递了茶来,清香馥郁,邢芸接过茶来一看,见杯中飘着朵朵梅花,因而笑道:“怎么今日泡了这三清茶来?”
桂叶笑回道:“太太怎么忘了,昨儿还说想这个味呢。”
邢芸一笑,端起茶来略抿了几口,便放下了,一边看着邢德全吃点心,一边让人抱了女儿来逗弄。只是才接过女儿,邢芸心口就隐隐约约的绞痛起来,只觉五脏六腑都被人拿着砂纸使劲的擦弄,想呕又呕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又渐渐头晕眼花起来。
桂叶瞧着邢芸脸色不对,忙忙扶住邢芸,一手按在邢芸的胸口,轻揉了几下,骇然道:“太太,怎么了?”
邢芸喉咙里喘着气,咳了一声,吐了一口血,两眼翻了一翻,便倒了下去。
作者有话要说:ps:本来想写完了一齐发的,结果高估了我的存稿能力,能够全文存稿的作者真的好了不起。
另外:脚好痛,最近停水,又碰上修路,公交车绕行,我去我姨家洗澡吃饭,坐车居然还比不上走路速度快,郁卒啊!坑人的是,公交车改道了我不知道,然后又绕了一大圈走回去,于是小腿剧痛。
这么想着,再往邢德全身后看了一眼,邢芸笑盈盈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去,邢德全竟是一个人来的。
邢德全见邢芸脸色不太好,倒也极乖觉,上前向邢芸请了安,便垂手立在一旁不说话,瞧那模样,竟是连头也不敢抬。
邢芸见着邢德全这样,心里略舒服了几分,看这样子,邢德全如今还不是原著里那个只知吃酒赌钱,丑态百出的傻大舅,因而说道:“你怎么也不带个小厮长仆出来?大冷天的,外头人又多,万一叫什么人碰着撞着了,可如何是好?”
邢德全规规矩矩地抬起头,看了邢芸一眼,才闷声道:“原有一个小厮跟着,因来府里,就命他回去报信了。”
邢芸柳眉一拧,才一个小厮跟着邢德全?她知道送回去的银子不可能完完全全用在邢德全身上,但是这漂没也太过了,差一点就赶上大国印度了。
邢芸压着气,又笑问道:“前儿你二姐托人来说,你已入学读书了,在学里可还习惯?”
邢德全犹豫道:“学里……”
邢芸冷了脸,问道:“学里怎么了?”
邢德全这才说出来,原来邢德全入学得晚,又不曾怎么启蒙,进了学里,未免跟不上进度,先生虽然有教无类,但学里那些同窗多是些小孩子,懂得什么,见得邢德全年长许多,却因自幼养在家里,不大与人接触,显得呆笨,便发着性儿捉弄邢德全。
邢德全起先还谨记着家里的教训,不和那起淘气孩子计较,谁知他越是退让,越是被人欺负……邢德全也不是没告过先生,只是不告还好,一告先生,越发被人孤立欺负,先生管束也无多大用处,而且邢德全入学晚,学业也不见上进,先生也不愿多理会这些。
所以,邢德全心里一鼓气,索性就跑来找邢芸了。
只听得邢德全一边哭一边哽咽道:“我不是不想读书,可每天不是书被人撕了,就是笔不见了,我也告诉过二姐,二姐只骂我废物,连个书本也看不住……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我不想再去那念书了……”
“不去那,又去哪儿?京里的学房虽多,也不是能由着人尽着挑选的。”邢芸在前世好歹念了十几年书,也知道学校里那些事,像这种校园欺负事件,老师管得严呢,动辄请家长退学呢,倒能压服住那些淘气学生,若是老师手软呢,那些熊孩子结了伙,什么奇葩事情都做得出。
撕书打架偷东西什么的,还算是普通的,邢芸前世才念初中时,刚巧学校里出了一件人命案,死的是个初三女生,死因是自杀,不过不是因为什么学业压力,而是因为得罪了当时同年级几个混混女生,那些女生看她不顺眼,就找了几个初二和社会上的无业青年,把她□了……当时媒体不发达,受害人家长也觉得出了这样的事儿脸上没光彩,所以轻而易举便被压下去了。
但学校还是狠狠整治了一下校园秩序,那些不爱学习爱惹事的所谓坏学生,基本上都被学校劝退学了,校园风气算是有了极大的改观。
所以,邢芸的初中生活,还算平静,况且邢芸的性格也不绵软,谁要是敢欺负她,她绝对会报复回去,就算人多了打不赢,也会揪着其中一个下死手打,于是,在隔壁就是监狱和技校的普通初中,邢芸顺顺利利考上了重点高中,从而告别了以盛产不良青年和从军预备队而出名的初中校园。
因此,邢芸看在在眼前哭的邢德全,既理解又生气,理解的是邢德全的情绪,生气的是,邢德全居然这点耐压力都没有,撕书丢笔,算个屁大的事儿,打听清楚是谁撕的,谁偷的,再依样还施回去不就成了。哭有个屁用,能把书和笔哭回来不成?
至于同窗不理他,邢芸更是无语,这世上男女一见钟情的还少之又少呢,何况是别的关系,不想被孤立,自个找突破口啊,要不下死力气学习,学业上进了,自然先生喜欢,同窗想欺负孤立,都没那个胆量。
要不弄点吃的喝的,努力打入同窗中的小圈子,又不是万人迷,要人人都喜欢,有那么几个能说得上的朋友,不就成了。
情商不行,智商不行,一遇事就知道回家在家人面前哭,这样的人有什么能耐?
日后就是侥幸得了功名,做了官,衙门里的小吏不好相处,也回家哭不成?
又不是没断奶的小屁孩!难怪邢夫人在原著里心理变︶态,夫家娘家没一个能扶起的�
�邢夫人作为一个深宅夫人,除了两眼朝钱看,为自己做点老了以后靠钱度日防身的打算,还能怎么着?
脑子飞速闪过这些念头,邢芸看着邢德全掉着两泡鼻涕的模样,又说道:“本来呢,给你在家单请个先生,也不费多少银子,只是咱们家里又无管事的男子,便有那渊博雅正的先生,也未必肯上门来做西席。就是有那肯上门来的,咱们家里那些人都是些粗识文字的,先生教的好与不好,也看不出来,万一遇上个闷头讲课不管不问的,耽搁了你的前程不说,将你教成了个木胎泥雕,不通人□故才是悔之晚矣。到底要立些根基,学个榜样才好,为这个,我和你二姐才送了你去学里读书,你如今既说学里的风气不好?想必心里已有看法,要选个什么样的书塾,若说得有理,我这做姐姐大不了费些心,替你再寻个书塾,也省的日日牵心挂肠,唯恐你被人引诱坏了。”
邢芸这一番话说出,邢德全心里倒自在了几分,用袖子抹了抹脸,抽着气嘟嚷道:“我也不知道要什么样的,只要不被欺负……府上不是也有念书的地方,我去那读也一样……”
去贾府家学念书?邢德全不亏是原著里的傻大舅,提的主意也是傻到家了。
贾府家学是个什么地方?就是给贾府子弟免费吃喝,顺道着结交契弟,行那龙阳之事的场所,至于读书,用宝玉的话说,还是不提为罢,省得脏了这两个字。
当然,邢芸穿越以来,为着种种目的,也用各种方式推动着整治了几次家学。但是,就如贾府的烂,是从上到下烂透了根的,专供贾家族里子弟读书的家学,其糟糕程度也是难以想象的,要把这些从根子已经长弯了的学生,重新扳正过来,所需要付出的金钱和重视,是贾府管事的老爷们给不起也不愿意给的。
邢芸推动的几次整治,充其量,是让那些族里子弟知道,家学还是有人管着的,不敢在学里闹腾太过分而已。
正是因为清楚这些,邢芸才不让贾琮去家学念书,而是特特挪出屋子,请了先生来府里教贾琮。
贾琮这个庶子,邢芸尚如此慎重,邢德全这个和邢夫人有血缘关系的弟弟,邢芸更不可能轻忽处置。
须知邢芸一入修途,冥冥之中,便有所感,自从她得了邢夫人的肉身那一刻,便染上尘世因果,如非了结这些因缘牵扯,否则即便她心无二用,一念不生,功行之时,依旧有魔头杂念,纷至袭来,伺隙相侵,略一疏忽,轻则功亏一篑,严重时,走火入魔,元神受创,就是转世重修,亦难成就道果。
因此,邢芸才会漫使银钱,由着邢家人予取予求,在她看来,金银这等俗物,不过泥土石头一般的东西,能用金银这种人间物事,了结一部分与邢家的因果,对她而言,已是再便宜不过了……
所以邢芸是绝不肯让邢德全到贾府家学念书的,这倒无关教学的好坏,实在是家学中贾家族人太多,邢德全一去,难免生出枝节,长此以往,因果纠缠,越难了结。
“家学?”邢芸嗤笑一声,骂道:“你当那家学是什么好地方?我提起来就恶心!”
看着邢芸变了颜色,邢德全一脸委屈,拿袖子抹着眼,一副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
桂叶木香原都是邢夫人从邢家带来了,知道邢家就邢德全这么一条根,又因邢芸与贾母已是水火不容,膝下只一个女儿,若是与邢德全再一生分,真个是婆家娘家无一能靠了。
因此,桂叶忙走上前,拿出帕子替邢德全擦了擦泪,笑劝道:“全哥儿有心向学原是好事?只是府里的家学,确实不是个好去处。全哥儿你想想,太太和你是嫡亲的姐弟,万不会存心害你。”
听着桂叶说了这话,木香也哼了一声,不满道:“可不是,那学房里本就是贾家族人和亲戚附学的地方,太太原先也想着,这府里的学房到底是姓贾,倘或全哥儿在家学里念书,便是学里有什么事,太太不问也能知道些,倒比外头的书塾妥当。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家学早和个戏园子差不多了,那些儿族里的远亲子弟,若长得略好些儿,到了学里,竟成了那些粉头一般——”
“木香!”桂叶忍不住喝了一声,淡淡的责备道:“这也是你能说的。”
木香被桂叶这一打断,也醒过来自己失言了,只是她性子倔强,仍旧放低了声音,嘟囔道:“本来就是,我又没说错。先前秦家哥儿来咱们学里读书,为这些事,不是很闹了一回,听说连宝玉也打了呢?府里那些小人本就瞧咱们太太不顺眼,全哥儿若进了府里学房,不是由着人打骂吗?”
桂叶看着木香瞧着这不服输的劲儿,深觉头痛,又看着邢德全听了木香的话,很有些有些抬不起头来的模样,只得叹了口气,向着木香说道:“你没说错,可就是没半点忌讳。”
木香越发不服气,嘟着嘴就欲反驳两句,却不意邢芸瞄了她一眼,只得憋着气忍下来。
桂叶见木香不吭声了,又拉了邢德全哄了几句,将邢德全劝服住了,才向着邢芸笑道:“方才太太还说要给姑娘取小名儿呢,如今全哥儿在这儿,何不就让全哥儿给姑娘取一个?”
邢芸听了,微微一笑,说道:“让全哥儿帮着取一个也好?……等她日后长大了,若是怨着小名儿不好听,也碍不着咱们,只好找她舅舅哭去。”
几只白鹤悠闲地在池边漫步,两对鸳鸯在水中梳拢着羽毛,一个梳了双环头戴红花的小丫头蹲在水池边,一拨一拨的弄着水玩。“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其他侍候的人呢?”
小丫头不提防背后有人,慌忙站了起来,不料脚下踩着一块石子,往前一滑,一脚便迈进了水池里,身上的裙子连带着湿了大半扇。
那小丫头好悬没跌进池子里,正庆幸呢,低头见着裙子湿了,忍不住就红了眼圈,想要恨骂两句,可看着来人又不敢,只得抽泣两声,抬头看着来人行了礼,哽咽道:“翠云姐姐。”
来人正是邢芸身边的丫头翠云,见着那小丫头一副眼泪花花似被她欺负了的模样,翠云没好气道:“又没人欺负你,你哭什么,不过是条裙子,湿了就湿了,回去换一条就是了。”
那小丫头低头提着裙子,细声细气道:“这是我得的第一条新裙子,才上身就弄湿了,干妈知道了又要说我了。”
翠云也知这些小丫头不易,一时笑了笑,看了一眼那小丫头的裙子,说道:“这有什么,这裙子是细布的料子,花样也老着,便是新的也不值当什么。我记着府里分发下来的衣裳,可都是绸缎做的,怎么你竟没得么?”
小丫头低着头蚊呐般的哼哼道:“得是得了,干妈说我又不在主子跟前侍候,也用不着,就都收去了。”
翠云眉头一皱,问道:“你干妈是谁?”
那小丫头飞快的抬头看了翠云一眼,抿了抿唇,小声道:“我干妈姓……是奶屋里宋妈妈的侄孙媳妇。”
宋妈妈的侄孙媳妇,翠云寻思着,忽而一张尖酸刻薄的脸跳了出来,一时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冷笑说道:“我说是谁,原是宋海家的。怪道这么有能耐,太太三令五申的那些规矩,她都能当了耳旁风去。”
原来这小丫头的干娘宋海家的,正是前些日子那个当面讽刺翠云勾引贾琏的管事媳妇,虽然当时翠云被人劝住了,不曾闹到邢芸跟前,但翠云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折了面子,心中岂有不记恨的,如今既拿住了把柄,自然是要好好做一回文章才能罢手。
因而心中衡量了一番,翠云暂且不露声色,安慰那小丫头道:“我那还有几条裙子,原是我的份例,因我不爱那花色,所以一直未上身,过会我命人给你送来。”
那小丫头听见这话,倒很有些受宠若惊,慌忙推辞道:“我怎么好要姐姐的衣裳?”翠云拍了拍那小丫头的手,笑道:“我若不在背后唤你,你也不会弄湿了裙子?给你这些裙子,也算我陪个不是。”
说着,翠云故作生气道:“还是说,你嫌弃这些裙子原是按我的身段做的,所以不肯要?”
那小丫头越发惶恐不已,连声说着不敢,忙忙乱乱地解释道:“不是,只是姐姐给了我,自个又怎么办?”
翠云一听就忍不住笑了,掩口道:“你这妮子?我便留着这些裙子也是白放着。我虽不出众,到底是在太太跟前走动,时不时能得些儿主子的赏赐,哪少得了衣裳穿。再说,这段时日,因太太娘家有喜事,我们这些跟前人没少得好处,就是上用的缎子,太太也赏了好些下来,岂是府里的份例能比的。”
那小丫头听着翠云这么一说,很是羡慕,一脸向往道:“难怪那些姐姐们都愿意到主子跟前去,原来除月钱涨了,还有这些好处。”
翠云素来心思灵巧,听得那小丫头认了干妈,便知这丫头是外头买来的,所以才不知这府里的情况,又恐那小丫头由羡生妒,反倒不好,因而又笑道:“我得这些算什么?现放着天大的好处,你也没瞧见呢。”
说了这话,翠云瞧着那小丫头一头雾水,似有些疑惑不解,又不免细细分说道:“你守着的这院里,住着的是春柳瑞秋二位姐姐,她们俩可是太太打娘家带来的陪房丫头,你若侍候好了她们,她们在太太跟前略提你几句,比什么都中用?”
那小丫头听得这话,倒笑了,说道:“姐姐这是哄我玩呢。我干妈早就说了,屋里这两位姐姐都养了几年病了,也没见太太唤她们回去,怕是早在太太跟前不时兴了,让我远着她们些,不要没得好,反得罪了人去。”
翠云微微尴尬,只是面上不显,强说道:“你干妈知道些什么?这两位姐姐若是在太太跟前不时兴了,太太又何必打发我送东西来。你没瞧见,这府里的人但凡得了病,都得挪出府去,唯有这两位姐姐,眼瞧着得了恶疾,太太还打发人收拾了院子好生照顾着的。”
说着,翠云看着远远的有人来了,也无心思再絮叨,便直往屋里去了。
话说凤姐往贾母跟前侍候去了,平儿却不曾偷得半刻闲,原来凤姐儿这一不在,那些执事媳妇们,唯恐出了纰漏,大小事务尽烦着平儿示下,才肯发放了去。
平儿原是凤姐儿的心腹帮手,怎不知那些执事媳妇心中主意,只是她天生好性儿,又爱做些好事,不得不受些辛苦了。这一时林之孝家的进来回话,平儿便吩咐道:“方才奶奶说了,眼瞅着天气渐渐冻起来了,该做的大毛衣裳怎么没影子了,别是林大娘你事太忙,就不上心了,转头老太太若是问起来,让林大娘你自个去交代呢。”
林之孝家的一听平儿这话,再是装聋作哑,也藏不住了,忙陪笑道:“平姑娘行行好,帮我在奶奶跟前分辩分辩,实在不是我不上心,这外头不给毛皮,我便是再有本事,也变不出衣裳来啊?”
平儿一听,扑哧一声,便笑了出来,看着林之孝家的说道:“林大娘这话,好没分寸,你也是府里的老人了,这衣裳月例,皆是旧有的例,又不是我们奶奶心血来潮的主意儿,怎么又说上给不给毛皮了?亏得奶奶不在这儿,若在这儿,你也敢这么回?”
林之孝家的脸上被说得红一阵白一阵,叫苦道:“奶奶既吩咐下来,我们哪有不紧着办事的,不知催了多少遍?可外头办事的人说,今年添得用项大,偏只有出的没有进的,不比往年,存着的东西便用不完,份例上要用的毛皮,只有等着庄上送年礼来才有了。平姑娘,你说说——”
林之孝家的一语未完,就听着外头有人问好道:“翠云姑娘怎么过来了?”
平儿听见外人来了,也懒与林之孝家的计较,故说道:“奶奶何尝不知今年外头使费大,可再是饥荒也没得在这上头克扣的。趁着奶奶还没回来,林大娘且受些乏,出去再问问吧。”
“呦,今儿奶不在,平姑娘也拿起主了,好生气派呢。”
看着翠云进了屋来,平儿忙站起身来,让翠云坐,又打发了小丫头端茶来。
翠云懒懒散散的摆摆手,看着平儿道:“不用忙,我站着说几句话就走。”
平儿眼皮子一跳,忙笑道:“什么要紧的话,你且说来听听。”
翠云便将先前撞见的事儿告诉了平儿,又说道:“平姑娘,你也是有眼睛的人,以前为这些事,太太不知发卖了多少人,我我知道你是个爱做好人的,这事你必定也知道,只是别人一求肯,你就碍着脸儿不吭声了。可你也不想一想,你不吭声,我还能装不知道,别说我今儿撞见了,就是我没看见,日后闹出来,我也不能得清净。还请平姑娘你行行好,做好事前先想想我们这些无辜人?我再不得用,也是太太跟前的人,太太生气发怒,我又能得什么好儿。”
平儿被翠云这一番话直气得肝痛,要说平儿自打过了明路,一直被人捧着,就算是凤姐儿和贾琏两口子闹起来,也不曾向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叫她没脸的。
平儿何等人物,纵是谋算胜过男儿的凤姐儿,亦视她为心腹,容她在府里各处施恩,上至主子下到奴仆,无人不道她的好处,如此周全玲珑,岂只是寻常人能做到的,如今翠云欺到跟前来,平儿岂有那么容易就忍气吞声的。
只听得平儿怒形于色地吩咐丫头道:“去,把宋海家的叫来。我倒要问问她,她算什么东西,能让我替她担着?一个高枝儿爬不上的主儿,尽往坑里洞里折腾把戏的野奴才,平素勾三搭四的也罢了,如今竟拉上我了,我可是个干净人,由不得她攀扯。”
翠云存了心要借平儿的手报复一番,不料反得罪了平儿,越发没得好处,脸上也不甚好看起来。
亏得翠云心性不同寻常人,饶是被平儿指桑骂槐,只脸儿红了一红,便无事人似的,向着平儿讥讽道:“往日太太常说,奶原是个好的,就是未免太心慈了些,让着身边那些贱婢都欺到头上了。亏得她是继婆婆,眼不见为净,要是嫡亲的婆婆,只怕早抱怨上了。也是咱们家规矩松,要换了别家,那起子贱婢早不知被卖到什么地去了!”
翠云最是个不怕闹大了无人收场的主儿,横竖她是邢芸跟前人,只要抓得住理儿,闹破天去,也没人敢找她麻烦。翠云心里可拿准了,如今府里正有喜事,二房一风光,府里那起子难免眼热拢了过去,太太早有意立一立威,也杀杀二房的风头,她闹出事来,正好说是为太太出气。
至于平儿的体面,翠云全不放在心上,不过一个通房丫头,便是体面,还能体面过她这个太太跟前人。贾府里可早有规矩,长辈跟前的猫儿狗儿,都不能轻易待之,就是凤姐儿见了她,嘴里也得尊重些,何况平儿这个丫头。
好在去请宋海家的丫头婆子回转得快,倒叫翠云这一番算计都付了流水,看着平儿忍气吞声,委曲着处置了宋海家的,翠云带着些许不痛快又坐了一会儿,才慢悠悠的往回走了。
看着翠云花枝招展的摇摇去了,凤姐儿房里的丫头忍不住啐了一口,骂道:“什么太太跟前人?太太跟前,她算哪根葱啊?也是奶奶不在,欺着平姐姐好性儿,要是奶奶在这,早两巴掌赏过去了。”
平儿忍了忍气,微微一笑,翻着账本道:“你气什么,眼下再猖狂,也难保日后如何,日子长着呢?还不知谁能笑到最后呢。”说着,平儿隐约觉得话儿不对,又转了话锋,冷言道:“再说,若不是宋海家的这个没出息的,又岂有今天这桩事?她倒能干着,拿了丫头的月例不说,连衣裳也给剥了,她不要脸咱们还要体面,传出去了,好听着呢。今儿我撵了她,也算是全了情面,要是奶奶知道了,依着性子,非发卖了她不可!”
到了院中,翠云正要进去,只听屋里有人说道:“姐姐的女儿自然是金贵,京中如今又有风俗,女儿之名亦从弟兄之字命名,府里虽不讲究这些,依此取个小名倒也使得。我看,不如用瑶字,瑜字或瑛字命名……”
邢芸柳眉一皱,淡淡一笑道:“这几字做何解?”
邢德全抬头看了邢芸一眼,小心翼翼道:“孔传有云,瑶,琨皆美玉。礼记上说,世子佩瑜玉。瑛,玉光也——”
邢芸沉下脸来,打断邢德全的话,不耐烦道:“你也玉他也玉,浑似这府里得了玉的便宜,况沾上这个姓,便是美玉也和石头一般,倒不若取个别的。”
邢芸心里微微烦躁,隐隐约约有种不祥的感觉在身边环绕,本来,贾这个姓就不大好听,取再好的名,都糟蹋了,看这一府里假环假琮假琏……活脱脱一山寨批发市场,姓不好,名字再好听也无用。
一想到日后女儿一出门,人家一长口,贾姐姐,邢芸就郁卒了,这称呼和史姑娘差不了多少,难怪贾家和史家是姻亲,姓都这么有特色也不大好找。
邢德全思量了一番,又说道:“懿字如何,懿,美也,又有一说,懿,从壹,这是姐姐第一个女儿……”木香听了,拍手笑道:“这名字好,一听就是好名字。”
邢芸蹙了蹙眉,字倒是好字,可惜怎么听怎么不大吉利,邢芸记得前世看宫斗文时,谥号里有懿字的妃嫔很有许多,好像,好像,祸国殃民的西太后,以前就被封懿贵妃。
邢芸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画面,这是空间文转宫斗文的节奏吗,她很无能的,养不出什么奸妃来的,嫖皇帝找真爱什么的,实在很尤三姐好不好?
邢芸吐槽着,正想否决这个名字,可一抬眼,才发现邢德全偷偷伸手擦了擦汗,心下晒笑,她穿的这时空,西太后的祖宗还在关外当野人呢。
虽是这样想,这字到底不太和邢芸的性子,故而邢芸又笑道:“这字固然不错,你再想几个,我送去让你姐夫挑一挑,万一合了我的意,他却觉得不中听,也是不好。”
说着,便让桂叶取了笔墨来,让邢德全又写了几个字,差人给贾赦送去。邢德全一见邢芸让人取了笔墨来,便知邢芸起心要考校他的书法,也不多言,专心致志的挥毫写下几个字来。
桂叶送呈邢芸,邢芸看了一看,无非是婉,嬿,秀之类寓意美好的字眼,便也不再多看,吩咐桂叶道:“叫人拿给老爷看吧。”
桂叶撩开帘子出去,正要打发小丫头送去,翠云忙走上前来,殷勤的笑道:“桂叶姐姐,可是要送东西,我替你送去吧?”
既有人愿意帮忙跑腿,桂叶也省了心力,何乐而不为,于是笑着将东西递给翠云,温言道:“有劳妹妹了。”
送了东西出去,邢芸又让人搬了凳子来让邢德全坐下,有一句没一句的问着些家常,邢德全也就含含糊糊地答着,无非说些吃的穿的都还够,不必邢芸操心的话。
不过一会子,翠云便回来了,笑说道:“老爷瞧了全哥儿写的这些字,说用来取小名倒浪费了,取做大名还好些。从了姑娘们的字,给姑娘取名为憶春。”
憶春,还好不是咏春,或者丽春。邢芸微微松了一口气,这名字要是取成了张国师版本的金陵十三钗中那位,哭都没处哭去……因此,虽不怎么喜欢这个名字,邢芸倒也没说什么,她本就不想把女儿留在贾家,日后出了贾府,自然是要女儿随她更名换姓的,现在贾赦取的这名字,她压根没打算用!
看着邢芸脸色不大好,翠云心里一咯噔,忙又上前笑说道:“老爷知道全哥儿在这儿,还让我送了点心过来,说是宫里赐下来的,让全哥儿尝尝。今儿他还有事,务必叫全哥儿留着吃了晚饭再回去。”
邢芸知道贾赦在外人跟前这些礼数是不差的,若不是摊上贾母这样的偏心眼母亲和王夫人那般多心算计的弟媳,存着心要坏了贾赦的名声,依贾赦接人待物的行为,在京里,就算混不上端方君子的声名,也落不到好色小人的地步。昔日林黛玉进府时,贾赦不论想不想见,好歹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出来,而贾政,却是只言片语都不曾留下。二人的为人处事,由此可见一斑。
邢芸不管贾赦心里怎么想,横竖传来的话,倒也顾全了体面,因而便嘱咐桂叶泡了茶来,劝着邢德全吃点心。
一时桂叶递了茶来,清香馥郁,邢芸接过茶来一看,见杯中飘着朵朵梅花,因而笑道:“怎么今日泡了这三清茶来?”
桂叶笑回道:“太太怎么忘了,昨儿还说想这个味呢。”
邢芸一笑,端起茶来略抿了几口,便放下了,一边看着邢德全吃点心,一边让人抱了女儿来逗弄。只是才接过女儿,邢芸心口就隐隐约约的绞痛起来,只觉五脏六腑都被人拿着砂纸使劲的擦弄,想呕又呕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又渐渐头晕眼花起来。
桂叶瞧着邢芸脸色不对,忙忙扶住邢芸,一手按在邢芸的胸口,轻揉了几下,骇然道:“太太,怎么了?”
邢芸喉咙里喘着气,咳了一声,吐了一口血,两眼翻了一翻,便倒了下去。
作者有话要说:ps:本来想写完了一齐发的,结果高估了我的存稿能力,能够全文存稿的作者真的好了不起。
另外:脚好痛,最近停水,又碰上修路,公交车绕行,我去我姨家洗澡吃饭,坐车居然还比不上走路速度快,郁卒啊!坑人的是,公交车改道了我不知道,然后又绕了一大圈走回去,于是小腿剧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