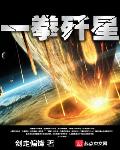第二章??远客归来自天涯
若是换做平时,无论旅人之间发生什么争论,胡掌柜概不参与,也不准手下的伙计们参与。既然拿了鱼龙骨架做生意,就一定要保持龙骨的神秘性,如此,大伙赚钱才能赚得更长久。可今天,他却宁愿冒上钱不能继续赚的危险,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朝当年斩除鱼怪的少年恩公们头上污水。
“就是,自己是个窝囊废,眼睛里就容不下任何英雄!捡个鱼龙尸体?有本事,你下水去捡一个给大伙看?”早就忍无可忍的伙计们,也都翻了脸。丢下酒碗,酒坛,开始从桌子下掏家伙。
与胡驿将一样,他们心里,也始终念着四位少年的恩。特别是后来听说四位少年,都死于太行山中的消息之后,更容忍不下,有人再诋毁破坏恩公的形象。虽然,虽然四个少年未必记得他们名字,在“黄泉之下”,也看不到他们今日的作为。
众旅人正说得高兴,哪里想到胡掌柜会突然翻脸,一个个顿时又羞又恼,气喘如牛。而那最先挑起事端的书生,却是个老江湖。见双方马上就要冲突起来,连忙收起了怒容,大声谢罪:“哎呀,还真的是英雄屠龙!怪我,怪我!?平素出门少,见识浅了,难免胡言乱语。这位官爷,各位公差,息怒,息怒!各位父老乡亲,也别认真。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今晚大伙儿所有酒水钱都算在我身上,该给伙计们的辛苦钱也加倍,全算我的,大伙天南地北能聚在一起都是缘分,没必要为一点小事儿生气!真的没有必要!”
“萍水相逢,怎好白吃你的酒?!”众旅人出门在外,原本也不愿意多惹事儿,既然有了书生给的台阶,赶紧迅速往下溜。
“可不是么,几乎话而已,犯不着认真!”
“算了,算了,都是无心之失!”
……
胡掌柜和他麾下的弟兄们,却依旧愤怒难平。撇了撇嘴,陆续说道:”辛苦钱加倍就算了,免得说出去后,让人觉得咱们是在欺负你!但给那鱼精为赞的话,切莫再提!它不配!当年受害者,也还没都死绝!”
“就是,那鱼精活着的时候,日日以过河的行人为食。如今它死了,你们反而来给他作诗,真不知道良心长在了哪边?”
“就是,就是,想显摆文彩,你倒是给那几个杀了怪鱼的英雄写上几句啊,你又不是鱼的孙子,凭什么替妖怪说好话!“”
……
那书生自知理亏,所以也不还嘴。只是笑呵呵地作揖赔罪。待掌柜和伙计们的气都小了,才清了清嗓子,小心翼翼地解释道:“各位勿怪,我一个外乡人,哪里对这黄河古渡口的事情,知道得像你们一样清楚。见到那鱼的骨架甚是巨大,难免惊为神物。又见贵号名叫鱼龙客栈,就以为此鱼曾经施惠两岸……”
“它如果曾经施惠人间,我们还会让它的骨头被日晒雨淋?!”胡掌柜狠狠瞪了书生一眼,没好气地说道。
“我们拿鱼骨头架做招牌,是要它赎罪!你以为世人皆像你们这些读书的一样没良心?”众伙计也撇着嘴,冷嘲热讽。
话虽然说得损了些,但书生始终笑脸相迎,大伙也不好真的赠之以老拳,所以骂过之后,也就各自又去忙碌,没心思再跟此妄人纠缠不清。
但是那书生,却被胡掌柜和伙计们的激烈态度,勾起了好奇之心。像只闻到肉味的狗一样,跟在胡掌柜身边,转来转去。直到把胡掌柜转得又竖起了眼睛,才终于停住脚步,带着几分讨好的味道询问,“这位官爷,您,您刚才有六位少年英雄跳到黄河里,跟那怪鱼斗了三天三夜……”
“不是六位,是五位,四男一女,老子刚才都被你们气糊涂了!”胡掌柜将算账的竹筹再度朝柜台上一拍,气哼哼地回应,“也没有打上三天三夜,要真打那么长时间,饿也饿死了,哪有力气打架??总计也就打了小半天而已!但你也别觉得少侠们很容易就斩杀了妖怪。在那之前,怪鱼已经为祸多年,两岸官府都制它不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为所欲为!”
“哦,这么厉害,那几个少侠莫非都身负绝技?或者师出名门?”书生听得心痒难搔,一边大声赞叹,一边继续刨根究底。
“不身负绝技,怎么可能除得了妖怪?”胡驿将存心想要替恩公正名,忽然把声音加大了数分,清楚地回应,“至于是不是师出名门,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太学生!那次出来,是从长安押运物资去冀州的救灾的。当时冀州闹了盐荒,他们心怀百姓,不肯绕路而行,直接撑船冲进黄河中,将那怪鱼唤了出来,阵斩于水面!”
“我的娘咧,居然敢主动冲进河里跟水怪叫阵!”一个河北口音的汉子惊呼道,“这胆子,岂不是比芭斗还大!”
“此乃大勇。”先前跟书生争执的酒客,大叫着拍案,“心怀拯救苍生的大义,所以无所畏惧,伟哉,伟哉!”。”
“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另外一个旅人也拍打着桌案,大声附和。
客栈里的气氛,顿时一变,很多人加入进来,七嘴八舌地夸赞当年那五个少年英雄的大义大勇。更有甚者,干脆用筷子敲打着酒碗,引亢高歌,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对传说中的英雄那份敬意一般。
唯有坐在角落里的一对青年男女,始终没有受到感染。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什么都事不关己,偶尔低着头互相说几句话,也把声音始终限制在仅有彼此能听见的幅度,唯恐打扰了周围的热闹。
“来,来,来,上酒,上酒,为那当年的五位英雄,浮一大白。账算我的,大伙一起饮盛!”书生肚子里诗兴大发,却一时半会儿写不出更好的句子,干脆直接以酒相代。
“那怎么使得?!还是各自付各自的好!”众旅人纷纷辞谢,但耐不住书生热情,一个个很快便接了伙计送上的酒水,喝得个兴高采烈。
胡掌柜见书生知错就改,心中对此人顿时生了几分好感。立刻命令伙计,从厨房又撕了几条干咸鱼,免费送给大伙佐酒。众旅人有酒有菜,喝得更加痛快,不多时,就有人酒意上了头,舌头开始不受控制。
“掌柜的,不是我吃人嘴短。刚才分明是你没及时告诉大伙,怪鱼曾经袭击旅客。反倒怪我们不通情理,只夸鱼怪不夸杀了它的英雄!”?一个分明喝得脸色赤红,却非得强装清醒的汉子,大声叫嚷。
“我是怕吓着你们,明天没胆子过河!”胡掌柜肚子里火气已经全消,不想跟一个醉猫计较,笑了笑,大声打趣。
“嗤,走南闯北之人,怎么可能被如此小事儿吓倒。”红脸汉子撇撇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你要是真心感激那五个英雄,就应该在鱼骨头旁,给他们五个人塑像,然后把他们当日的义举编成故事,每天人多的时候出来讲一次。保管咱们听了,不会替那怪鱼说好话,并且还要主动把几位英雄的名姓四下传播。”
“是啊,是啊,胡掌柜,你为何光摆个鱼骨头,不给英雄们塑个像呢。照理,他们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朝廷应该行文各地以示表彰才对,怎么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事儿,也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姓?“有人接过话头,大声补充。
胡掌柜的脸色,以大伙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暗。半晌,也没有再做一句回应。最后,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走到屋子角,自己拎了一坛子老酒,大口大口对着嘴巴狂灌。
“怎么了,莫非是有人窃据了他们的功劳不成?”?书生的感觉非常敏锐,立刻从胡掌柜的表现上,看出了事情反常。
“估计是了,这年头,什么怪事没出过?唉!”其他旅人脸上的笑容也迅速变冷,摇摇头,长吁短叹。
“要是只窃据了他们的功劳,还算好了!”胡掌柜用手抹了下嘴巴上的酒水,咬牙切齿,“他们秋天时过的黄河,说是赶时间去冀州赈灾,结果才入了冬,太行山那边就传出了消息,有一支运送精盐的队伍,遭到了土匪堵截。连押车的官兵带赶车的民壮,没逃出一个活口!”
“啊——“众旅人打了个哆嗦,额头瞬间冷汗滚滚。
经常走南闯北之人,当然知道太行山的凶险。可盗亦有道,土匪为了避免涸泽而渔,通常只会让商队交出两到三成的货物做买路钱,很少将一支商队中所有人都斩尽杀绝。而一旦大开杀戒,要么是受了其他人背后指使,要么跟商队中某个领头者有过不共戴天之仇。
几个从长安来的太学生,当然不可能跟太行山里的土匪有旧仇。那样的话,答案就非常明显了,有人花费重金买通了山贼,让他们豁出去商路彻底断绝,将五个刚刚离开校门没多久的年青学子,葬送在了太行山中。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都跑不出来?胡掌柜,胡掌柜先前还说他们武艺超群,连鱼怪都能杀掉!”?只有请大伙吃酒的书生,因为隔行如隔山,没想清楚其中弯弯绕,兀自皱着汗津津的眉头,喃喃质疑。
“那鱼怪只有一头,而山贼,却是成千上万!”?胡掌柜满脸悲愤,又灌了自己几大口酒,继续低声补充“况且,出手的还未必是山贼!附近上下百里,只有这一个渡口,在他们渡河之前,还有人带着百十名家丁,用牛羊贿赂了怪鱼,大张旗鼓地乘船而过,胡某人可记得一清二楚!”
“你是说,有人带着家丁公然与山贼勾结,截杀朝廷命官?”?书生的脸色立刻变得无比严肃,站直了身体,低声追问。
“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说,看到有人带着家丁朝太行山去了。结果他们没回来,恩公也没回来!”?胡掌柜激灵灵打了个哆嗦,铁青着脸摇头。
“原来如此!”?书生愤怒地以手指敲打桌案,发出一连串的沉闷的声响,“那五名学子姓氏名谁,你可记得清楚?!”
“当然!”?胡掌柜将酒坛子朝桌案上一丢,大声回应,“带头的姓刘,单名一个秀字,大伙都称其为刘均输。另外三名男姓少侠,分别唤作邓奉、朱祐和严光。那名女子,应该是刘秀的未婚婆娘,姓马,大伙称他为三姐,或者三娘子!”
“那提前几天,带着家丁过河的人呢,你可知道他们是谁?”?书生皱着眉头,将五个名字努力记在心中,然后继续大声询问。
“掌柜,柴禾,柴禾不够了!”一名伙计冲上前,拖着掌柜的胳膊,用力朝后厨扯去,“你赶紧看看,柴禾不够烧了,真的,再这样下去,明天就得吃夹生饭!”
“柴禾不够烧,你们不会自己去砍?”胡掌柜不知道今天是受了刺激,还是喝酒喝晕了头,居然连如此明显的提醒都没听出来,一晃肩膀甩开了伙计,然后大声向书生回应:“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知道他们都姓……”
“掌柜,掌柜,锅漏了,漏了!”又一名伙计匆匆上前,拼命用话堵胡朝宗的嘴。
胡朝宗今天却彻底豁了出去,一巴掌推开伙计,大声嚷嚷,“滚,自己去想办法。当年山头让老子装哑巴,老子看在俸禄的份上,不得不从。如今朝廷都一年多没给老子发俸禄了,老子还替它遮哪门子丑?!过河的那俩王八蛋,都姓王,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一个排行二十三,一个排行二十七,是如假包换的长安口音。他们带着那么多明晃晃的兵器,肯定不是去太行山剿匪。老子当时就怀疑过他们,后来直到恩公们出了事儿,才终于明白过几分味道来!”
原来又是长安王家人,书生愣了愣,身上的不平之气,顿时消失得干干净净。其他旅人,也纷纷摇头,随即抓起酒碗,大口狂饮。恨不得立刻将自己灌醉,也暂且躲入梦乡,暂时不看这世间污浊。
人的胆子大小,这会儿立刻就表现了出来。当所有人都叹息着开始买醉,先前跟书生争执的那么酒客,反而推开了手边陶碗。笑了笑,大声道:“这就清楚了,英雄除得掉水怪,却过不了长安王家这道鬼门关。怪不得近年来,各地百姓揭竿而起,绿林、赤眉、铜马攻城拔县,势如破竹,原来有本事的才俊,都被王家自己杀干净了。剩下全是些窝囊废和马屁精,当然被义军揍得屁滚尿流!”
“是极,是极,朝廷对不起英雄,现在不知道可否后悔!”
“后悔个屁,他们都住在长安城里,义军一时半会打不过去!
“早晚会打到,长安城里,可不产粮食!”
大部分旅人,对朝廷早已彻底绝望,加上恨他们黑白不分,七嘴八舌地咀咒。
“可那义军,杀起人来,也丝毫不手软!抢钱抢粮,刮地三尺,比官府没强哪去!”也有人在旁边大声感慨,恨世道太乱,前脚送走了老虎,后脚又迎来了狼群,。
“那不一定,赤眉和铜马军的确走到哪抢到哪,可绿林军,据说军纪十分严明!”?立刻有人免费为义军张目,大声在旁边反驳。
“即便赤眉军,也比官军强许多吧。我在路上听人说什么,‘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这太师指的便是王匡王太师,更始就是更始将军廉丹。这句话是说,赤眉是山贼土匪不假,但他们最多就是抢点东西而已,而朝廷派来的王太师和廉将军可就不一样了,但凡他们经过的地方,那都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话匣子一打开,跑题是再正常不过,几乎眨眼之间,对义军纪律的指控,就变成了对官军的声讨。
“是啊,是啊,赤眉那伙人,都是活不下去才起来闹事的苦哈哈,在我们老家那边,声势浩大。但乡里乡亲的,他们也不好把事情做得太绝!“一个操着曲阜口音的旅人,摇着头大声感慨,”而官兵就不同了,都是些外乡人。抓不到赤眉军,却急着向朝廷交差,砍百姓的人头来冒充赤眉,是常有的事情,几乎每天都能听闻!”
“可不是么?河东那边,也是一样!”只听刚刚从黄河以北过来的旅人,叹息着大声附和,“说是防范铜马军,实际上铜马军根本没过太行山。然后就官兵就开始让地方助粮助饷,谁敢不给,立刻扣一个通匪的罪名!”
“再这样下去,就不怪大伙投靠绿林了!”?一个操荆州口音的旅人,立刻大声接过话头,“至少他们比官军讲道理,并且看起来能成事。去年,绿林军大败了荆州牧,今年初,他们又火速攻入了南郡、南阳和平林,三支队伍遥相呼应,直打的朝廷的军队节节败退。如此下去,用不了五年,也许这大新朝的江山就得换……”
话说到一半儿,他忽然又意识到胡掌柜是个官员,匆匆打住。但众人已经皆知他真正想要说的是什么,纷纷低下头,窃笑不止。
“放心,老子就是个驿将,才不会把手伸到秀衣使者的一亩三分地儿!咱们这种不上台面的馆子,也没有绣衣使者愿意光顾!”?胡掌柜被笑得好生尴尬,摇摇头,大声承诺。(注1:绣衣使者,朝廷密探,类似于后世的锦衣卫,权力极大。)
话说得虽然满,他却忍不住瞪大了眼睛,在客栈内迅速扫视。结果,不看还好,一看之后,,额头上顿时冒出了大颗的冷汗。
他发现,就在客栈的角落里,有一对青年男女,跟周围众人的表现格格不入。先前自己光顾着招呼书生、酒客和一众旅人,根本没多余的精力放在这对小夫妻身上。而现在,却忽然注意到,这一对伉俪的模样,竟与记忆中某两张早已经逝去的面孔,依稀相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