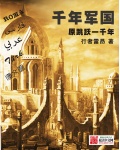次日,天空飘散起零星小雪,营地罗开先主帐内却热气奔腾,话语不停。
“时下定难军主分七部,每部五千人正编,由南向北分守韦州、会州、盐州、宥州、夏州以及石州和银州,说是五千,实则每部编制总有出入,会州、盐州、宥州和石州稍多些,余者人数均不足五千之数……”李德明端坐在皮榻上,认真向罗开先诉说着河西之地的军力分配,“夏州这里除某拓拔家族兵,尚有别部族兵数千,因多了将军派来王难和卢守仁帮忙镇守,才免于乱象!最近几月,某正在新召兵力,拟用将军所设灵州军制编练新军,不知可否由将军派参军或教习助某?”
“各州分驻军兵,是否会兵力分散?且与各种民众一起,军兵纪律和训练如何保证?各军可有轮换机制?若无,恐军令难以下行……”遇事则喜,说的就是罗开先这种人,挑剔了好些要点,才有些恍然——这是一个兵为将有的原始时代,再抬头看见李德明因窘迫而涨红的脸,他也消饵了计较之心,随机换了话头,“德明兄弟预设新军……此为明智之举,某无异议,只是参军与教习,从王难与卢守仁军中选拔即可,他们自有决断之权,德明兄弟何必亲自问某?”
货怕比较,人也怕比较。
只是几句话,李德明就感觉到自己麾下的军队不值一提,窘迫得恨不得在地上打一个洞钻进去,好在对面的长人适可而止换了话题,他才稍感自在,“王难与卢守仁所部……原为某部汉人附军,新军中人多有熟识,恐难为人接纳,故……”
“嗯,既如此,某……”罗开先沉思了一下,接着说道:“待某从宋地回返,于各营选拔精锐之士来夏州赴任,可否?”
“大善!悉听将军所命!”李德明闻言大喜,他不怕罗某人派人“指手划脚”,恰相反,看过了灵州众的表现之后,他更希望自己手下能有那样的部众,唯恐罗某人“敝帚自珍”。
罗开先却做自若状,心里暗乐不已——先不说灵州军制不过临时所设,未来必将进一步完善,就说派遣之人尽心教授夏州新军,这所谓新军就能和灵州相提并论吗?
绝无可能!
只是有一点这时人根本不晓得的事情,一旦灵州军人在夏州这里确认了强悍的形象,必定难以磨灭,未来一旦有所冲突,军心谁属?
罗开先此刻心中得意之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北方的朔风从帐外呼啸而过,虽未吹透帐篷,却从外面传来一阵士兵匆忙的脚步声,显然是什么东西被吹倒了。
没人过来禀报,自然不用罗某人出帐探看,不过他悠然的心境却荡然无存,看了看闷声在心中计较的李德明,他朗然开口道:“德明兄弟适才通述诸州现状,似不曾说起石州与银州,不知那方现况如何?”
李德明恍然,遂接之前所说继续道:“石州有坚城,并三千精锐镇守,不虞有失,只如今于东面镇守银州之兵力羸弱,分驻几部人马,均重商事逸于兵事,好在与赵宋协议开设了榷场,短期勿需担心……”
罗开先沉吟不语,心底对照着记忆中的历史思考了半天,才开口评述:“听闻宋帝赵恒自与北辽契丹人檀渊之盟之后,渐生自满之心,亲佞臣重道事,治政则重文轻武,欲行以文抑武之策……故,某断语若宋不改策,则东路宋军绝不敢妄起战端,德明兄弟若不想族人枉死,切记约束各部军兵,莫与宋人开战之凭依……”
长人侃侃而谈,李德明默然聆听,类似之语他也曾从张浦那里听过,却绝没有罗某人话语中那般果决断然。而长人话语中所透露的内容,也让他心中警然——灵州众初落脚不满四月,竟连宋帝日常也知晓得如此清楚,莫非有人向他通风报信?或者这长人早派人为前探,查明各路消息?
他当然不会想到罗某人来自后世,所说不过凭借记忆推断边境现状。
罗某人的话语却并未因为李德明脸色变幻而停歇,“然,宋人治政,以文抑武,而非以文制武,武人若执意发难,文人又能耐若何?榷场可交通有无,实为善事,但若大贾涉入,钱财纠纷却可乱人心智,故,德明兄弟须防宋边将私开战端,需知彼等胜,则宋庭必将视为开疆拓土之功,若败,才有私开边衅之过!”
“喏!谨受教!”话不说不明,罗某人的话尽透宋人边将心态,李德明越听便觉心中越是明朗,欣喜之下冲着罗开先深揖一礼。
“德明兄弟毋须如此!”入乡随俗,罗开先也觉得自己变得儒雅了许多,连忙伸手拖住对方手臂,“你我虽于孛罗大战一场,却不打不相识,往日仇怨,毋须记怀,能于今日坐论族人来日,实为幸事!若能携手共进,率领诸族营造一处安宁祥和之地,则不枉空活百年,且必将名留史册,留子孙念诵铭记!”
说至动情处,罗开先也免不了流露出些许真情绪,声音难免激昂了起来。
“德明愿随将军冀尾!”或是受到情绪感染,或是心中也有同样心志,共鸣之下,李德明也高声随喝。
“呵呵,可惜某不愿饮酒坏了心智,否则此情此景你我当共浮一大白!”话了之后,罗开先也有些哑然,“帐内只有这奶茶,来来来,就以此代酒,饮胜!”
“饮胜!”至此,李德明已视罗开先为自己指路之人,行止间也是亦步亦趋。
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志向仿佛,眼下又确有合作之机,自是饮水如酒,话语做羹,酣畅淋漓。
又说了半天军机琐事,帐外朔风越发急迫之时,罗开先开口说道:“明日,无论是否大雪,某将率队继续东行,祖地绥州,某必前往祭之,赵宋之地,汴京,某亦必往探之。”
“将军何必如此急迫?待到雪晴之日,再走也未尝不可……”话越说越畅快,思路也越发明晰,李德明真的不舍得这种酣畅。
“兄弟何必如此儿女之态?”拍拍李德明的手,罗开先说道:“兄弟知某率众行军数万里,区区风雪,岂能阻我?且东去赵宋又是数千里,夏州有雪,岂知东方有雪乎?”
“倒是德明矫情……”被人说做儿女之态,年纪已经二十六岁的党项大统领李德明也免不了赧然。
“哈哈……”罗开先没想到这时节人的脸皮竟然如此薄,不由得满是笑意,这在他来说可真是难得之事,半响见李德明的脸愈发红似猪肝,才勉强而止,拱手连连,“好,某失言,德明兄弟莫怪,莫怪……”
李德明红似猪肝的脸皮才稍稍退减。
“不瞒德明,某之灵州,粮草足够众人吃食至明年初秋,但,虑之春后必将有人往投,唯恐粮草不足,某此次去汴京,旨为购粮。余者皆为顺路之事!”罗开先朗然开口继续说道:“然,顺路之事也为必须之事,探看来日敌手,为将者必行也。耳目再灵,莫若亲眼一观,德明兄弟莫要阻某!”
“将军……”这等事必为军中机密,乍闻之下,李德明也免不了乱了手脚,感叹一句,随即试探问道:“将军不怕某派人通告赵宋,劫杀于你?”
“哈,信某者,某亦信之也!君,信人否?”学着这时代的文人,罗开先掉了两句酸文,才接着说道:“若德明兄弟乃阴密之人,怎能得某实言相告?若德明兄弟真失信于某,怎知某定会丧身赵宋?某,帅十万众行进数万里,损人不过千,灭敌却过十万,君若失信于某,就不怕某来日卷土重来,尽灭河西?”
一番话语,前面还兴致高昂,后面的自述话语却隐隐透着森寒,杀气重重。
若说李德明一点没有因忌讳而告密赵宋的想法,那绝对是假的,但罗开先这一段话之后,党项大统领的后背上悚然冒出了一层冷汗,忙解释道:“将军休恼,德明失言!德明在此向长生天,向拓拔列位祖上,向党项大族所崇信各位神明起誓,绝不会外泄灵州大将军罗开先丝毫信息,如若有违,天灭之,地覆之!”
誓言对这时候人的约束力远超与后世,李德明话语过后,就深深后悔自己不该妄动念头,这罗姓长人的厉害,自己早在孛罗城就已经见识到,怎如今还像毛头小子一般不知深浅?他的誓言不单是说给罗某人听的,同时也是警醒自己,切莫得意忘形,这罗开先对已对敌完全是两个态度,绝不含糊其辞。真若变成敌人,自家这大统领虽说号令百万民,能抵对方多少时日?
罗开先言罢再不提东去赵宋之事,反而接着与李德明细论榷场琐事。两人对话,气氛虽不如之前浓烈,却答问有序,少了之前的客套虚词,多了务实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