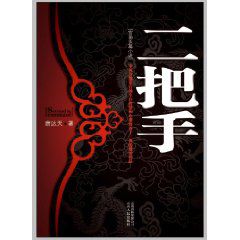官场小说及其他
我向来排斥前言和后序,觉得有话就写在内文里,读者自会明了,题外的话,不免絮絮叨叨,招人烦。可是,这部却不同,写完了书,还觉得有话要说,只好写了《官场小说及其他》,权作后记。
有人说,二把手就像古时的“二房”,是一个尴尬的角色,上要讨好一把手,下要应对三四把手,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个人以为,不仅如此,二把手是每个官场中的人走向高处的必经之路,二把手的目的是当上一把手,一把手的目的是当上更高层次的二把手。世上没有永远的二把手,也没有永远的一把手,有的,只是永远的权力。二把手的处世哲学和政治智慧,几乎囊括了整个官场的全部图景,悟透了二把手,等于悟透了官场,也悟透了人生。在这个意义上说,要写透这一个层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这里有我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我无法超越自我,更无法超越时代,我只能尽力地、无限可能地去接近事物的本质,去触摸人的灵魂,能达到几成,不是我说了算,读者自有感悟。小说写的人生,而人生就像茫茫丛林中的跋涉,你只能感觉到前面的方向,却看不清前面的路。小说中的主人公何东阳如此,我也是如此。正因为前面的路上有许多不可确定性的因素,才有人迷失了方向,有人半途而废,有人掉入陷阱,更有人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而何东阳呢?此去经年,异地为官,这不仅仅是一次升迁,更是一种人生的挑战与超越,他将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他能否经得起金钱美色的诱惑?能否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求得平衡,能否凭他的政治智慧化解各种矛盾与难题?正因了我对他有这么多的牵挂,才深感忐忑,也许,这也奠定了我有续写的可能。
我每写完一部长篇,心都要跟着人物走一会儿,把人物送上一程,心才能渐渐地淡定。我知道,那是一种牵挂,是一种情感的需要,有时候是由不得人的。就像老友来看我,把酒相待,分别时,直到远去的车离开了我的视野,心跟着他走一会儿,才肯离去。文学是现实的翻版,当你对小说中的人物产生了情感后,离开时总是恋恋不舍。这使我想起了“文学就是人学”这句名言,这话虽然老了一点儿,却也老得深刻。凡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无论你写何种题材、何种领域,都离不开写人,只要把人写活了,写出了人的情感与灵魂,写出了人物的命运,就是好作品;否则,凭你说得天花乱坠,也无济于事。在《二把手》中, 我力求走进人物的心灵,从他的灵魂深处寻找他的行为逻辑,不想只把它写成道德小说,不想只对人的行为标准进行是非判断,仅仅停留在怎样“做人”的层面,更要考虑的是如何“立人”,写出官员灵魂深处的痛苦和挣扎,以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正因为如此,我写得也很纠结,在人物面临的每一次选择中,我都想从他的文化心理、价值判断中找到一种合理性,并且,力求从现实矛盾中引发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与读者一起思考。
我始终认为,中国的精英大多都聚集到了官场,从每年的公务员招聘录取中便可看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好的岗位,竞争率可达千分之一或者万分之一,其中不乏硕士和博士。这种趋之若鹜的表象背后,还是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和公务员铁饭碗的优越性所致。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从文学的角度引发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就是说,为什么反映社会精英的官场小说往往受到诟病,被文学界视为通俗文学,而写农村的、普通农民的小说,反而被视为纯文学?如果从人的精神层面来分析,一个官员的精神取向、文化程度,远远大于一个乡村农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这无疑是一个悖论,不知是官场小说本身出现了问题,还是评论界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
就目前的官场小说而言,的确也有许多受到诟病的地方,比如类型化、简单化、复制性越来越严重。纵观近年大量涌现的官场小说,可谓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这种原因的造成,主要是因为官场小说有着很好的市场潜力,才引发了好多人都来写。会写小说的也写官场,不会写小说的也写起了官场,在官场中混过的人在写,没有官场经验的也在写,甚至于一些落马的贪官在监狱里待着没事了,也写起了官场小说。一时间,官场小说一下子充斥到新华书店的货架上。有的官场小说实在卒不忍读,打开书看不到两页,就感觉到非常别扭,书中的官场人物所言所行,根本不像官场中的人,一看就知是作家凭空想象出来的官场及官场人物。从写作范围上讲,几乎党委和政府所管辖的各个部门都被人写过了,几乎所有的官衔都被命名过书名,比如《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市长》《县长》《镇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环保局长》《纪检组长》《文联主席》《电视台长》,还有秘书、司机、保姆等等,不一而举。从写作层面上来讲,许多小说还仅仅停留在故事的表层,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更没有触及到体制和社会的更深层,只故弄玄虚地以官场教科书、公务员必读之类为噱头来抢夺市场。如果读者对他们所悟出来的“官场秘笈”信以为真,照本宣科付诸实际,则定然会误入歧途。这些是与官场现实严重脱离的作品,整体格调灰暗,给“官场小说”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也误导了读者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现实中的官场生态并非一些所谓“官场小说”描述的那么灰暗,官场即是职场,争斗在所难免,但也并非没有阳光,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来报考公务员。
官场小说如何摆脱类型化、模式化、表面化的困境?恐怕是每个官场作家都在思考的问题。谁不想超越自己和他人,谁不想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谁不想带来更好的市场效应?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你想超越就能超越得了的,这与作家个人的见识、心灵、气质、思考、价值观,以及对社会的认知程度、文学修养、政策水平都有很大的关系。就小说创作而言,我觉得没有题材优劣之分,只有作品的高下之分。不是写了农村题材的,你就是纯文学作家,就是真正的作家;写了官场商战,就低俗,是通俗小说作家。相对而言,政治小说、官场小说更需要作家对现实生活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思考,你写不出独特的东西来,想让读者叫好也是不容易的。摆放在货架上的官场小说很多,不是每本都有可观的销量,有的也只是卖个几千册上万册而已。货架上的农村题材小说,也不是全卖不动,销量达数万册甚至几十万册的有的是。任何事情并非绝对,如果作家综合能力上不去,你写什么也不行,要想超越自己和他人,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
我曾与一位编辑做过深入的探讨,就现在的官场小说,从境界上分,不外乎三种:一种是以揭秘和往上爬为中心,里面充满了升官之道的披露,完全是满足读者权力欲和窥私欲的厚黑学读本。时下名目繁多的官场小说,大多都还停留在这一层面。第二种境界稍高,能站在人性、权力和现实的层面写出为官者的真实心理和复杂纠结的思想意识,写出这一群体的真实生存现状,对官场文化、官场生态、权力规则等作出比较深刻的阐释和解读。而能达到这一层面的作家也不多。第三种更深一层,能够站在儒道传统文化、权力更迭历史、官本位心理和中国民众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境况里,探讨为官者更深层的精神习性、为官哲学和理想追求等。在时下,能达到这一层面的作家更少。这里存在着作家认识上的局限性问题,也有时代的局限性的问题。往往,近距离地观察社会,认识上虽然很感性,却也失去了全面俯视生活的理性。要想产生真正触及到社会深层结构,触及到政治文明和文化心理结构,触及到人的灵魂深处的大作品,也许需要大的社会变革,需要远距离的观看,需要几代作家的努力。
这里便出现了一个文学界老生常谈的问题,作家需不需要参与公共事务,需不需要社会担待?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不应该回避社会矛盾的,更不能放弃对社会的承待与责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说:“作家有义务介入公共事务。”如果这句话不是略萨说的,而是一位普通的中国作家说的,一定会引起中国的另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的嘲笑:说这是功利文学,或者说作家要远离政治事务,否则,就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文学。可是,略萨不仅这么说了,而且他还用他的文学实践传达了他的这一思想,这让那些想嘲笑的人没有了资格去嘲笑,或者是没有胆量去嘲笑。略萨在诺贝尔获奖感言里还说过:“我是作家,同时也是公民。在拉丁美洲,许多基本的问题如公民自由、宽容、多元化的共处等都未得到解决。要拉丁美洲的作家忽略生活里的政治,根本不可能。” 事实上,社会现实、社会政治是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事务,介入社会、介入现实,是文学最主要的使命,一些真正的和不朽的文学,都是生根在社会生活的事务之中的。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里,要谈公共事务,要谈政治,就不可能回避官场。官场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是社会矛盾最为集中的场所,更是社会最敏感的细胞,谁要是真正写透了官场,也就写透了社会和人生。可是,这样的认识在当下很少能得到主流文学和评论家的认可,正因为作家介入公共事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讥笑与排斥,才导致了反映社会问题的官场小说在圈内备受冷落。如果把时光拉近五十年,像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这样反映现实的作品,恐怕也会被划为通俗文学的行列,很难得到应有的关注。而《州委书记》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却被列为内部参考书,它对当时的领导决策起到了别的小说无法替代的作用。
我不敢肯定这是不是我们认识上的局限,但至少也算是认识上的偏差和过激,才导致了眼下的官场小说冰火两重天:一边是市场的热棒,一边是评论界的冷淡。而读者喜欢的,评论家总是不喜欢;评论家喜欢的,读者又非常冷淡。评论家总是与主流文学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非主流的文学总是与广大读者团结在一起。这是不是文学界的又一种悖论?
事实上, 官场小说中也不乏优秀之作,如果悉心品读,它的文学性,它所转达的社会信息量,绝对不亚于那些所谓的纯文学作家写的农村小说。固然,写官场小说的人很多,免不了泥沙俱下和粗制滥造,正如农村题材的作品中也有粗制滥造之作一样,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这种类型的写作,更不能因为一触及到官场,一畅销就认为它不是文学。文学大师司汤达有一句名言:“如果有这样一位作家,在马德里、斯图加特、巴黎和维也纳等地,靠翻译赚钱的翻译家都争相翻译他的作品,那么,这位作家可以说是已经掌握了时代精神的趋向。”如果把他的话做一个中国式的改写,就应该是这样:“如果有这样一位作家,出版公司、书店老板、靠出书卖书的人都争相出他的书、卖他的书,那么,这位作家可以说初步掌握了时代精神的趋向。”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更加理性地认识我们当下的创作和纠正我们曾经的偏执?为什么不能用更加宽宏的心态来看待他人的创作,非要先入为主地妄加排斥?一位在圈内很火的中年作家曾在报纸大骂官场小说都是垃圾,并且公开申明他不会看这些垃圾的。我正为他偏执的骨气暗暗称赞的时候,没想到他竟然也出了一本被他贬为“垃圾”的垃圾。而且在“垃圾”的封面上公开印上“官场小说”的字样。遗憾的是,他的“垃圾”没有像别人的“垃圾”那么畅销,几乎在读者中没引起任何反响就被别的“垃圾”淹没了。看来,官场小说也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好的,畅销书也不是谁想畅销就能畅销的。正如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所言,纯文学作家想挤进畅销书的行列难,畅销书作家想挤进纯文学的行列也难。还有一位获过国家级大奖的作家说,幸亏我的作品没有畅销,否则,我就完了。我不觉暗想,幸亏他完了,没有畅销,否则,畅销书作家中又多了一个不真诚的人。
作家这个圈子,言不由衷者实在太多了,性格拧巴者也不少。作品离读者太远了,他说是写给后代看的;放到书店里没人买,他说他拒绝市场写作;读者不愿意看他的书,他说读者素质太低;写得太离谱了,他说是探索;谁的畅销了,他说是垃圾。他们总是有理由,自欺欺人又想欺骗他人。有时候,你骗自己容易,骗他人却不容易。一本书的好与坏,作者讲再多的理由也没有用,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读者,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消费群体。一个眼里没有读者的作家,你可以获奖,可以评高级职称,可以当作协领导,读者却不买你的账。一本书放到书架上,就像蔬菜进了菜市场,你去买菜,肯定要挑新鲜的自己喜欢吃的来买,决不会买那些腐烂的发霉的。将心比心,道理就这么简单。
在我的博客里,有一位作家曾经隐姓埋名地恶骂道:“你们这些官场小说作家,写的都是垃圾,都是浪费国家的纸,要不了两年,就成了纸浆。”我看着这样的话,仿佛看到了那张因嫉妒而变了形的脸,被阴暗的角落里反射过来的光照得越发阴暗。可是,无情的现实给了他最有力的回击,我十年前的书,并没有成为纸浆,现在已经出到了第三种版本,而且照样有人买。嫉妒与诅咒,只能将自己气出病来,却丝毫奈何不了别人。我不知道我从没有谋过面的这个人为何对我这么仇视?我究竟在哪些方面得罪了他?经过一番反省,才恍然大悟,知道他恨的不是我,而是官场作家这一个群体。我能理解他的苦衷,他辛辛苦苦写了一本书,求爷爷告奶奶,印了两三千册,出版了没有人买,又拿不到稿费,看到别人一本书动辄就是数万册,甚至十多万册地拿版税,心里一时失衡也在所难免。
我不知我何时也被划分到了官场小说作家的行列?对官场作家这样的称呼,最初我多少有些不适。一是我并非只写官场,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在《十月》《小说》等刊发了《沙蚀》《荒天》等一系列乡土小说,出版过中篇小说集《悲情腾格里》,还写过都市情感的、创业的。这些小说中,最能代表我水平的,当属长篇小说《沙尘暴》,而非官场小说。二是这种称呼,要在圈外,仅仅是称呼而已,没有别的意思,如在圈内,便多少有些排挤的不认可你的成分。其实,对小说题材的过分细化本身就有很多争议。如果追溯下去,来划分四大名著的话,《水浒》应该是官场黑道小说,《红楼梦》是青春文学,《三国演义》是军事小说,《西游记》就是玄幻小说了。试想想,要是真的这样来分类,这四大名著还是四大名著吗?好在没人这么去划分,也就少了无聊的争议。至于对我的称呼,久了便也习惯了。官场作家也好,乡土作家也罢,不论是哪个领域,能写出自己满意的、让读者喜欢的好作品才是关键,否则,神马都是浮云。作家的尊严是读者给的,不是作家自己装腔作势装出来的。
前几年,就有人断言官场小说只不过是一阵风,刮上一阵就完了。现在,又刮了好几年,还没有刮完。我觉得,小说作为反映生活的一种形式,它的存在与否与社会现实是密不可分的,只要官场还存在,只要腐败一天不根除,反映社会现实的官场小说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也必然有它的土壤与市场,这是谁也挡不了的,除非他有本事让贪官们不腐败,让执政者做到真正的透明公正,让现行体制非常完善。这当然是谁也做不到的,也不是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作为反映现实的官场小说,也不会是一阵风,除非国家下了禁令,否则官场小说还会继续火下去,因为读者需要反映现实的作品,现实也需要真正的文学。
我相信,官场小说一定会产生真正的文学,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