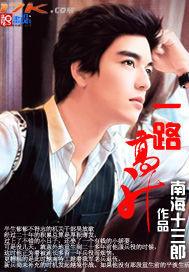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来得比以往要晚了许多,直到四月中旬份的时候,桃花才刚刚泛红,但是此时的江城却是一片的兴盛,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而最令人瞩目的一项工程,自然当属此时正在武昌蛇山与汉阳龟山之间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这座大桥已然牵动了全中国人民、甚至于全世界华人的观注,万里长江第一桥,也将是沟通中国南北的重要通途。而此时,刘兴华便作为湖北省主抓长江大桥的建设的负责人,要配合着大桥建设委员会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便是在节假日期间,也无法得到一丝半点的清闲。
王金娜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见到刘兴华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却觉得好象他们之间已经分别了有三年一样久,虽然很想找个机会与老朋友坐一坐,聊一聊,但是却也知道刘兴华的工作很忙,不方便打扰,她也知道,如果刘兴华有空的时候,一定会过来看望他们,不为别的,也会为了他的干儿子小虎。这一段时间里,倒是熊卓然会隔三差五地过来一趟,每一次手里面都不会空着,王金娜也知道,这位熊领导看的并不是她,而是住在她这里的两个孙子。
实际上,她的工作也千头万绪,因为是新到一个单位,又开始了大学教学的生涯,她还带着十几个从全国各地精挑细选而来医学研究生,当了一名导师,繁杂的事情也自然会多出不少。好在大学和医院里都十分体谅她的身体,生怕她的精力不够,所以除了每星期固定地有两天上午必须要到医院里坐诊和要去大学上三节课之外,其它的时间由她自己进行安排,并不强求。尽管如此,王金娜却也没有倚老卖老,还是象以前一样,把很多的时间投到了医务工作中来,为老百姓解决一些疑难杂症。
这一段的日子对于王金娜来说,过得太过充沛了,便是回到家里的时候,也要面对除了包括小虎在内大大小小五个孩子的教育,虽然在这方面徐小曼也能够担负起家长的职责,毕竟她也是两位孩子的母亲,但是王金娜却觉得同样作为一个母亲,她不能够完全放任自流。由于工作的繁忙,她请了一个姓秦的保姆,以照顾家里这些孩子的日常起居和生活。值得一提的熊英和熊雄这两个兄弟虽然顽劣,但是却非常听从小虎的调派,也许孩子与孩子之间沟通起来,要比大人与他们沟通起来要容易得多,在他们搬到家里来住之后不久,这两个孩子便成了小虎的跟班,结成了死党一样,便是上学和出去玩都很少分开过;如此一来,倒是令王金娜又省心了不少,有些事情她与熊家兄弟讲不通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张小虎来要求,竟然也达到了十分好的效果。这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成绩也还不错,这也是唯一让王金娜感到宽心的地方。
前些日子的时候,徐小曼带着儿子小强和女儿小红去了东荆县和张义住了一个多星期,可是她回来的时候却没有一丝的兴奋,相反,还感到忧心忡忡,直到两个孩子都睡了,她才来到了王金娜的屋里,满怀不安地向自己的大嫂叙述着心头的担忧。
“我真得害怕张义会出问题!”徐小曼一脸得惶恐,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王金娜放下了自己正在编写的教案,与徐小曼面对面地坐好,问道:“小曼,你慢慢说,你到张义那里去都看到了什么?他在那边工作得不好吗?”
徐小曼犹豫了一下,一时之间又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想了想,还是道:“我到那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就看到他跟县委书记吵了三次架,你说叫我还怎么在那里住得下去呀!”
“吵架?”王金娜愣了一下,她知道在工作中因为观点不同,而产生争辩,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往往是对事不对人的。而从徐小曼的嘴里说出来,就仿佛张义根本不是在跟县委书记谈工作,而是真得在吵架一样。她当即笑了笑,道:“你也许太过紧张了,张义这个人我知道,认准对的事情,就会一根筋走到头,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在这一点上,他跟他的大哥真得有些象!呵呵,说得好听,这就执着;说得不好听,就是不识实务!”她说着,又劝解着道:“你也不用这么担心,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只会为工作发生争执,不会吵架的!”
“要真得象你这么说就好了!”徐小曼叹了一口气道:“我也想这么想呀,但是真得就象你说的那样,张义就是一个不识实务的家伙,中央都有了政策,他只要按着做就行了,他的上面还有县委书记呢,他一个小小的县长争个啥呀!”
听到徐小曼这么说,王金娜不由得来了兴趣,忍不住地问道:“小曼,他和县委书记到底争是什么问题?”
徐小曼道:“我也问过他,他倒是没有瞒我,跟我说了。”她说着,停下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这才又接着道:“上面不是一直在强调要对农村和城市里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必要的社会主义改造吗?就连上海、天津的那些大资本家都拥挤公有化,这也是我们国家大的方向。他们东荆县正在全县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变,按县委书记的想法,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项工作,在全省充当先进;但是张义却跟他唱反调,你说他这不是在找麻烦吗?”
王金娜怔住了,虽然她对于农村的问题并不太懂,也不怎么关心,但是还是从报纸和广播电台里知晓一些事情。所谓的生产合作社,就是为了提高生产水平,把单人从事生产的农民联合到一起,组成的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初级社,就是在这种联合生产的时候,所有的社员把土地交出来,由集体进行统一的经营,生产物资和设施等生产资料也由集体统一使用,社员参加社内的劳动,但是却还相应地保留有部分的自留地,并且也可以经营其他的家庭副业,而这些家庭副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都归社员自己;而所谓的高级社,自然是又进一步,要求社员把所有的私有土地无代价地转为集体所有,便是连社员的耕牛、大中型农机具也规集体所有,有的地区允许社员保留生活用品,零星的树木和家畜、家禽、小农具;而有的地区这些物品都要转为公有。高级社的社员由集体统一安排生产,并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生活物资。
“张义不同意他们县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吗?”王金娜不由得问道。
徐小曼摇着头,道:“也不是,他只是对于有些作法有意见!第一次我听他和县委书记争的时候,好象是县委书记要求全县要在三个月内完成这项任务,他却提出反动意见,认为不可能完得成,说最少要一年!”
“这是在争的时间,事关老百姓的事,是急不得的!”王金娜道:“看来,他们的县委书记是个很急躁的人。”
徐小曼点着头,又道:“第二回,我听他们争的是自留地的问题,县委书记要求不允许社员保留自留地,认为那样会滋生小资产主义;而且他还认为社员连鸡、鸭都不能养,如果那样的话,集体的利益就会受损;但是张义却说现在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会令社员消积怠工,他认为自留地可以慢慢地转变,用两年到三年来逐渐取消;而关于社员养鸡养鸭这件事,他认为没有必要加以限制!”
王金娜皱起了眉头来,点着头道:“这一点上,我觉得张义是对的,老百姓要是连养鸡养鸭都不行,那他们跟旧社会给地主家当长工有什么区别?他们还叫农民吗?”
徐小曼愣愣地看了看王金娜,也许对她的这个比喻有些不赞同,但是她还是没有说什么,接着道:“第三回,我听到他们争的是要不要取消东荆县里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县委书记认为必须取消,所有的乡镇都不允许赶集,因为这样会让社员产生投机主义思想,去投机倒把,不重视社里的劳动;另外,他还认为不取消集市,县供销社就没有权威,集体利益也会受损;但是张义坚决反动,他说老百姓赶集,那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就流传下来的传统,没有必要取消,而且赶集也可以加快物资的流通,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跟供销社的作用并不冲突。”
听着徐小曼说完,王金娜沉默了起来,如果单单从徐小曼的描述上来看的话,她反而觉得张义的话是句句在理,但是她也知道徐小曼担忧的不是没有道理,在东荆县里,张义毕竟还只是一个县长而已,并非是县里的一把手,作为下属的他与自己的顶头上司对着干,那纯粹是在玩火;而此时中央的政策,就是在进行公有化运动,如果张义还是这般得执着,死钻牛角尖,那么将来只怕吃亏倒霉的肯定还是他自己。
虽然王金娜有一百个理由觉得自己应该支持张义,但是看看徐小曼这张担惊受怕地脸,她还是屈服了,于是想了想,对着徐小曼道:“小曼,你也别着急,张义真得是太倔强了,我知道你肯定劝不动他来,我也劝不动他的!这样吧,明天我抽空去找一下刘兴华,也只有他可以把这头牛拉回来了!”
听到王金娜这样的回答,徐小曼点了点头,她其实就想到了准备让刘兴华去说一说张义,但是却又觉得自己的分量不够,而王金娜的建议也正是她所希望的。
也便是因为这个原因,王金娜觉得必须要来见一见刘兴华了,因为她相信,不管刘兴华现在有多忙,他也一定不会放任张义而不管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