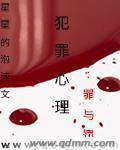生与死
“不许动!警察”“不许动!”“不许动!”此起彼伏的喊声吓了正在交易的众人一跳。他们显然没想到,自认为安全的交易地点其实早已经在警方的布控之下,瞅准时机给他们来了个瓮中捉鳖。
“跑啊!”正愣神的众人被不知道谁发出的一声吼叫惊醒过来,对啊,此时不跑更待何时?这里四周都没有人烟,只要他们跑快一点跑远一点,这些死条子还想抓他们,哼哼,就得让他们有来无回,他们腰里别着的可不是烧火棍!
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反正以他们的罪名,被抓到肯定是一个死字,怎么死都是死,还不如拼一拼,还可能会趁着夜色杀出一条生路来。
毒贩凶悍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现场有些混乱,仅靠几束强光手电筒已经不能准确地追踪所有毒贩了,他们也很聪明地利用了警方照明设备不足这一点,开始四散奔逃,时不时回身射击,也不看打没打中人,继续闷头逃窜。
埋伏在附近山坡上的狙击手一点没客气,在这些人不服从命令缴枪投降,反而准备逃跑后,他们开始精准点杀,率先击毙了九名驾驶员,以免他们驾车逃逸,难以追踪。
狙击枪的动静在混乱的夜色中依然清晰无比,正准备上车的一小部分人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发现昔日的同伴已经死在眼前,额间绽放开的血色之花正汩汩流出红白相间的液体。他们吓得呆了一呆,却又立时反应过来,知道如果现在上车抢占驾驶室,在对方有狙击手虎视眈眈之下,也肯定不可能让他们驱车逃窜,唯今之计,只能靠双腿了。
于是除去了九名司机后还剩下的十六名毒贩开始寻找掩护,狼奔豕突,因为警方的人已经离他们很近,两拨人遭遇到一起,狙击手不敢再随意开枪,每一个目标都在时刻移动,速度极快,夜视仪下分辨敌我双方的人员比白天效果要差很多,为避免出现误伤,他们只得坚守在岗位上,紧盯着有没有从棉纺厂跑出来的漏网之鱼。
最激烈的巷战打响,双方人马你来我往,子弹乱飞,时不时有惨叫声响起,那是双方被流弹击中后发出的呼喊。
警方准备充分,死守住了各个缺口,将一帮毒贩围在厂区里慢慢消耗他们的弹药和精力。拖时间对警方是有利的,所以他们一直打得很稳,轻易不会露头,两两结组,交换射击,不给毒贩喘息的机会。而毒贩压根没想到,那么多大风大浪他们都经历过来了,却在这小小的一次交易中栽了跟头,哪怕今天来的这些人中真正算得上大兴帮的骨干高层的很少,只有唐哥一人,这点小小的损失,大兴帮完全负担得起。但是他们也知道,警方能一直在这里埋伏等着他们自己跳进包围圈,很可能是他们的内部组织出了问题,不是出了内鬼就是交易网络不再安全,可惜,唐哥再没有机会将这个消息传出来。
果然所谓的帮派保密制度在关键时刻是坑死人不偿命的。大兴帮在江湖上最高调的时候,引起了不知道多和层级公安系统的注意,也是他们那个时候过于张扬,办了些很招人眼球的事,于是麻烦来了,他们帮派内部不知道进来多少条子的卧底,有好几次他们的交易行动都不得不临时取消,才算惊险无比地躲过了被警察全歼的命运。
那段日子,也是大兴帮里人心最散的时候。因为没有人知道谁可以信任,谁是条子派来的,也许昨天还跟你把酒言欢的兄弟今天就摇身一变拿你下大狱了,人人自危的日子过得久了,谁心里都不舒服,很多人选择了离开,便是彪哥和他上面真正的头目大兴哥都踌躇过要不要解散了大兴帮,换个地方,另起炉灶,重新开始。
可是M市是他们经营了多年的地盘,他们的根在这里,他们秘密贩运货物的地点就在附近,换得远了,别的都好说,一条安全的线可不是那么好找的。作为帮中元老之一,唐哥仍然记得,创帮之初他们七八个人从一穷二白到后来的财源广进究竟都付出了什么,那条安全的走私线,是他们许多的好兄弟与命换来的,他们今天的好日子过得舒心了,难道就能在面对一丁点困难的时候放弃掉曾经为之奋斗过的一切吗?让那些已经死去的兄弟又情何以堪?
唐哥想的是,如果大兴哥想要换地方,他小唐就脱离大兴帮自立门户,一定要守在M市这片有他兄弟撒过血的热土上。好在他没看错人,大兴哥是个有勇有谋的汉子,最终没有像丧家之犬那样夹着尾巴逃跑,而是迎难而上。
好,警察不是一直派人来吗?找出谁是内鬼不容易,让内鬼接触不到核心机密还不容易吗?只要抓不到他们的小辫子,警察又有什么了不起,跟卡了壳的枪也差不多,看着吓人,其实没什么鸟危险。于是大兴帮摇身一变,成了长兴进出口贸易集团,表面上也开展了不少完全合法干净的生意,至于这些生意挣不挣钱无所谓,能掩饰住他们内里真正的秘密就够了。这是一方面。
内鬼一日不抓清,人心一日不会完全稳下来,而他们这些出来混的,其实比普通人更需要讲义气靠得住的兄弟帮衬,独木难支,谁没个困难的时候,如果谁都不敢相信,长此以往,帮将不帮啊。所以大兴哥想出来的点子,就是信息保密制度。
比如说第二天有交易任务,头天晚上,只有骨干人物才知道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交易量和对方的基本情况,等到第二天了,骨干开始给自己手底下人分派任务,接到任务的人从知道具体情况的一刻开始,手机等通讯设备就会被没收,他本人也必须服从骨干的安排,去某个安全场所先呆着,不能随意离开,等到时间差不多了,再统一出发。这一队负责去现场交易的人,多则七八十,少也得六七人,这些人中,只有带队的一人身上有通讯设备,负责紧急情况下与上面联系,听从指示。
这样一来基本上切断了警察传递消息的路径,哪怕他们信错了人,让个便衣去参与了交易,那又如何?他没有办法通知警察现场抓人,人赃不并获,哪怕后期警察再想找他们麻烦,对不起,下回请早。
慢慢的,大兴帮里的卧底都被揪了出来,这些人会像其他与大兴帮有过节的人一样,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无踪无影,没有尸体,警方在立案上都困难,更别提想破案了。
那个时候,唐哥认为大兴哥就是个天才,才会制定出这么完美的制度,后来更是一切讯息上网,保密级别再次提高,他们再进行交易时无一出错,到现在已经有五年时间了吧。
人总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唐哥打光了枪里最后一颗子弹,满是遗憾地向着棉纺厂门口望去,他怎么就一点忧患意识都没有,把唯一能跟外界联系的手机扔在了他的车里呢?现在那辆车与他直线距离不过二十来米,却因为警方全面火力压制而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一直认为自己不怕死,如果有朝一日真的与警方火拼,他也一定会是抵抗到底宁死不屈的那一个。
可是为什么,事到临头,他感觉到四周围乱飞的子弹,和不远处时不时会响起的警方的呼喊:“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不要再负隅顽抗。”突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渴望过自己是个走正道的好人。
他不想死,就这么简单。一年前,他不再孑然一身,他有了娇妻,也算成家立业了,妻子是本地人,知道自己在长兴这个本地人谈之色变的地方上班,却也还是义无返顾地爱上了他。他们那场盛大的婚礼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也可以正大光明地站在阳光底下,而不再是地沟里见不得光的肮脏老鼠。一年的普通夫妻生活,朝九晚五上下班,每天到家就有热饭菜,真是神仙般的日子。他以前总想着,要出人投地,要挣大钱不再让人看不起,但是这一年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让他们平常的小日子一直这么细水长流下去。
他想到了退出。但是他不敢跟任何人说,别看彪哥和大兴哥表面上看起来都很讲义气好说话,对兄弟的困难和要求尽力帮忙,那是有一个大前提的,就是他们这些做兄弟的,首先要忠于大兴帮,为大兴帮卖命。然后他们才有闲心去演一出兄友弟恭的戏。唐哥可以想象得出来,如果他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心声,希望从大兴帮这条贼船上平安下去,等待他的也许是全家灭门之祸。
想想还未出世的孩子,想想什么都不知道的妻子,唐永凡就再也淡定不下来,他死不足惜,这么多年坏事做得也不少了,但是他的家人是无辜的,凭什么就因为跟他在一起便要连整个人生都赔掉?他如何舍得让自己心爱的人受伤害。
他开始慢慢想着脱身之法,甚至连假身份都买齐了,只等时机成熟,便带着老婆远走高飞,山高水远的,大兴哥总不会还千里迢迢派人去追杀他吧?他一没有出卖他们,二没有吞了他们的货自己闷头发大财,只是想要换种活法罢了。他唯一觉得头疼的,是如何说服妻子跟他一起走,他是孤家寡人一个,可是妻子的父母亲人却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他们一旦选择离开,便要隐姓埋名过一辈子,永永远远都不能让大兴帮的发现,自然也不可能跟亲人有联系,以妻子的性格,让她甘心情愿跟他走的可能性低于零。
唐永凡一直踌躇到现在,在跟妻子坦白与不坦白之间纠结,直到今天。
他有些时候,发现命这个东西,还真不能不信。可是让他就这么什么也不做屈从于命运,以他的性格又绝对做不出来。他想与警察同归于尽,就算做不到,也不想让他们活捉了他,但是当他枪里的子弹打光,周围的同伙一个又一个惨叫着倒下后,他没有勇气端起已经没有子弹的枪站出去——这是最快的自杀方式,只要他敢露头,一定会成为警方的集火对象,死亡会是注定的结局。
可是他死了之后,从别人嘴里得知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的妻子,是否会后悔爱上他嫁给他,是否会在他死后一辈子恨他?他不敢去想,只要一想到这种可能,他就有种心痛得无法呼吸的感觉。哪怕他坏得脚底流脓头上长疮,也依然希望在爱的人心目中善良高尚得像个天使。
可是现在苟延残喘又如何?妻子还是会知道直相,她能接受得了这个打击吗?自己深爱的枕边人根本不是她想象中有样子,她可是怀了六个月的身孕啊!他不想让她有一丁点的差错。
生或者死,他都不想选!却夹在纷飞的炮火中,生死都由不得他!
罢罢罢,他束手旁观,就算最后被警察捉了,至少还有机会跟妻子解释,自己当初是如何幼稚地上了条贼船,哪怕无法求得她的原谅,多看她一眼,再见她一面,也是好的。
枪声密集地响了近半个小时,双方的子弹都消耗得差不多了,不再像一开始那样随意放空枪,变得谨慎起来。
可是一开始被警方打了个措手不及的他们早被冲散,有三三两两想要从缺口逃入夜色中的倒霉蛋已经被活捉,剩下被围在厂房里的也死的死伤的伤,像唐永凡这样毫发无伤的也就两三个。
他们被打得可以说斗志全无,事实上在大兴帮无法被警察抓住狐狸尾巴的神话破灭的瞬间,他们内心早已经开始叫嚣着注定失败的结局。
又过了十分钟,当他们手中的最后一颗子弹被打光,终于开始有幸存者忍不住想要喊投降了。哪怕最终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也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也好过在荒郊野岭像条野狗般被打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