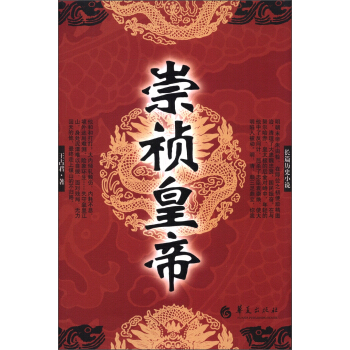崇祯没有答话,他已被曼妙的琴声所陶醉。而且下意识地用脚和着琴声的节拍,身体也轻轻地摆动起来。
周皇后心中涌起一股醋意:“皇上,既然如此钟情于琴音,何不进人承乾宫听个够。”
崇祯抬脚进门,承乾宫的太监高声传禀:“万岁爷驾到,田娘娘接驾呀。”
田妃忙不迭地迎出,在庭院中跪拜:“妾妃见驾,圣上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千岁!”
“爱妃平身。”崇祯将田妃搀起。
帝后妃三人步入正殿,崇祯望见了居中摆放的古琴:“爱妃,朕是被你的琴声吸引,还要续弹才是。”
“遵旨。”田妃人座,屏神静气少许,又舞动纤纤玉指,按动宫商,在琴弦上拨弄起来。
崇祯听罢,不由得问道爱妃,此曲莫不是坊道五曲?”“皇上圣聪岂可蒙蔽,此正是万岁所作之曲。”田妃有意谦虚,“只是妾妃尚不谙熟,有损皇上大作。”
“哎呀爱妃,朕涂鸦之作,不过随意而为,竟被你演奏得如此动人,真是难得的乐师。”
“万岁夸奖,妾妃愧不敢当。”
崇祯转对周皇后:“皇后出身世家,想必对抚琴也是婉熟。”
周皇后嘴角现出一丝冷笑:“妾妃儒家,自幼父母教习养蚕织布女工针黹,从未涉及游乐,无此雅兴。”
“皇后系名门之后,自是家教甚严,不会抚琴也罢。”
“臣妾不比田妃,能与琴师接触,实为幸事,望尘莫及。”周皇后显然这是讥讽田妃家教不严。
崇祯也就皱起了眉头是啊,爱妃向何人学会弹琴,男女授受不亲,这接触想必是颇为亲密。”
田妃明白崇祯这是吃醋了,她跪倒答话:“禀万岁,妾妃母亲自擅宫商,抚琴是母亲所教。”
“噢,原来如此。”崇祯便释怀了。
周皇后却不依不饶:“皇上,左都督田皇亲之妻精通音律,臣妾从来未有耳闻,何不见识见识。”
崇祯原本对田妃琴艺就已生疑,这一提倒正中他的下怀,便吩咐身后随侍的太监王承恩:“宣左都督田弘遇夫人立刻进宫。”
周皇后与田贵妃二人,谁也没想到崇祯竟连夜召田妃之母进宫,周皇后尤觉魈尬:“皇上,是否改日再召。”
“不,朕要一饱耳福,一睹田夫人的琴技。”崇祯主意巳定,因为他最爱的女人是田妃,如果田妃与其他男人有过亲密接触,这是崇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人夜之后,田夫人被召进内宫,她的确有些诚惶诚恐,心中忐忑不安。心想莫不是女儿生了急病?及至见到女儿立在一旁,悬着的心始得放下。但还是对人宫摸不着头脑,她俯身叩拜:“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
“平身。”崇祯紧接着问,“田老夫人,你可会抚琴?”
田夫人不明白这是何意万岁,我会。”
“你现场为朕抚一曲《髙山流水》。”
“遵旨。”田夫人就现场女儿的瑶琴,端端正正弹奏了一曲,弹得是音律纯正余音不绝。
“朕再问你,田妃的琴艺莫非也是出你的调教?”
“皇上,老身笨拙,自幼教娘娘弹琴,还算是粗通一二。”田夫人一直蒙在五里雾中,“怎么,田娘娘她弹琴出了差头?”
“老夫人无须多虑,现在没什么事了。”崇祯发话,“你可以出宫了。”
田夫人始终不知进宫所为何事,带着懵懂的心情叩谢离开:“吾皇万岁,老身拜辞。”
崇祯得意地看着周皇后:“皇后,可还有疑虑?”
周皇后当即跪倒:“万岁,臣妾不该心生妒念,致使万岁夜招田妃之母进宫,甘受惩处。”
崇祯语带责难之意:“皇后,朕待你一向厚过田妃,不当再存争风之举“臣妾知罪。”
“国事常令朕忧烦,这家事你自当为朕分忧,一国之母更当虚怀若谷,怎能也小家子气?”
“万岁教导的是,臣妾再不会让皇上为家事分心了。”周皇后俯地再拜。
田妃主动上前把周皇后搀扶起来:“皇后不要过分自责,上次多蒙皇后娘娘成全,使妹妹得以同皇上重修旧好,皇后决非鸡肠小肚之人。”
周皇后与田妃携手言好,崇祯心中也觉畅快。王承恩看准时机,上前奏道:“万岁爷,边关有两份军情急报,请圣上御览。”
“呈上来。”崇祯看的头一份是,三边总督洪承畴的喜报。当他看到西北匪患尽平,主要匪首悉数歼灭,真的是龙心大悦。特别是看到曹文诏英勇追击,以三千关宁铁骑,连破十倍于己之敌,更是赞叹不已:“我朝有这等猛将,何愁不能尽除匪患。”
周皇后顺着崇祯的意思:“皇上,对有大功之臣,自当重赏,并委以要职,使其忠心报国。”
“这是自然。”崇祯打开第二封边报,看着看着,脸上的笑容便不见了,“陕甘匪患洪承畴道是业已根除,可这山西又多处告急,多处州县失守,莫不是陕甘的土匪蹿到了山西?”
“如此说是太原吃紧了。”田妃已领悟了崇祯的弦外之音。“土匪攻打太原甚紧,太原已是危在旦夕。”崇祯显然忧心忡忡,“太原乃山西首府,如太原有失,则山西全省不保。”
“万岁,既然曹文诏勇冠三军所向无敌,何不调他率军前往太原救援。”周皇后提议,“同时也可就此擢升曹将军。”
“曹文诏倒是可用的人选,只是陕甘刚刚平息匪患,曹文诏一走,恐那里死灰复燃。”崇祯不是没有忧虑。
“皇上田妃也发表了见解,“陕甘已无匪患,况且洪承畴仍在,便有余匪也闹不起来。”
“却也有理。”崇祯吩咐,“王承恩拟旨。”
“遵旨。”王承恩提笔等候。
“擢升曹文诏为山西巡抚,挂兵部侍郎衔……”
秋风卷着黄叶漫天飞舞,黄土高原上刮来的尘沙,把大地铺上了一层黄色的土面。义军的营帐,布满了太原城外的山冈村落,由于队伍支系太多,到处呈现出一片杂乱无章的景象。大大小小的头领,正逐一向紫金梁王自用的大营中汇聚。王自用本是王嘉胤的侄儿,在王嘉胤战死后,其残部便奉他为统帅。而眼下各营义军,也唯他这一支人数最多,他自然也就成了义军的核心。
帐门的传令官不时地报告着来人的名号:“闯王高迎祥到,八大王张献忠到,曹操罗汝才到,闯塌天刘国能到,闯将李自成到不过一刻钟,便有三十六营的头领来到了王自用的大帐。王自用对大家拱手施礼:“各位头领,以往我义军在陕甘接连失利,主要原因就是大家没有拧成一股绳。此后,只要我等一心团结,打败官军就不在话下。”
李自成率先接话:“王大哥所言极是,我建议从现在起,我们各营都奉王大哥为统帅,一律听他调度指挥,合力攻下太原,打开一个新局面。”
“有理,有理。”张献忠表态我老张赞同闯将的意见。”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赞同:“愿听王大哥调遣。”
王自用眨眨眼睛光这口头上答应不算数,我这有三道令牌,无论是谁家兵马,见了令牌就要听调听招。”
“要是不听调呢?”张献忠问,“谁又能把谁怎么样呢?”
李自成提议如果不听号令,造成军机丧失,或者重大损失,三十六营中是谁的责任,就让该营的头领受罚。”
“怎么个罚法?”张献忠刨根问底,“要是轻描淡写的,还不是脱了裤子放屁白费事!”
“军纪就要严明。”李自成提议,“不遵军令者,杀无赦。”
“怎么,斩首?”张献忠难以相信,“办得到吗?”
“如果三十六营全都同意了,那就办得到。”李自成深有感受,“以往我们各路人马败就败在不能相互援助上,往往是只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没有严明的军纪,岂不还是重蹈覆辙。”
罗汝才终于开口了,他的绰号曹操,也是名副其实的,一向奉行宁可他负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负他:“咱们又不是官军,干吗非得各营上边还安个总督。大家说好,以后如有难处,各营互相救援就是高迎祥倾向李自成的意见三十六营聚会,要定就定个规矩,否则今天这个会不是白开了。”
刘国能含糊其辞地表态:“反正王大哥的令牌只要我见到,我这一营人马保证听调听招。如若失言,五雷轰顶。”
其他各营的头领,也无不效仿刘国能,全都起誓发愿信誓旦旦,言称保证遵守令牌的调遣。始终未能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意见,这难得召开的三十六营大会,其实还是无果而终。
散会归营的路上,李自成无限感慨地对高迎祥说:“高闯王,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却不能更正,看起来义军多少人也是一盘散沙,要想成气候,我们还只能靠自己才行。”
髙迎祥深有同感:“令牌不过是虚设罢了,没有哪个头领会听调听招,我们也不能为了别人贸然出兵。”
“高闯王的意思是,也要保存实力?”李自成眉头紧锁。
“我军当然不能为了帮助别人,而不顾自身安危。”高迎祥断然决然,“我们这一万多人就是我们的本钱,不能干亏本的买卖。”李自成默然,他没想到自己最尊敬的高闯王,也没有大局观念,而是以保存实力至上。义军全都这样,还能打胜仗吗?
紫金梁王自用,对三十六营军事会议的结果大为失望。他长叹一声对弟弟王自有说:“看这个光景,我们这些所谓的义军,是难成气候了。”
“大哥,大明气数巳尽,光我们这三十六营就有二十万大军,何愁不能消灭官军,依小弟看足有八分胜算。”
“咳!”王自用完全没有信心,“你可知道,明朝的皇帝崇祯,已经把曹文诏调到山西了。”
“大哥,那曹文诏不就三千马军,就算他全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咱们有两万人马,还怕他不成。”
“此人绝对不可轻视,神一魁手下四大头领,全都死于他的手―中。”王自用对曹文诏了解颇为详细“他虽说兵力仅仅三千,可他们每人全都备有两匹战马。一匹累了,再换另一匹。因而速度极快,犹如狂风闪电,战斗力特强我们最好避开他。”
王自有将信将疑:“看大哥你都把他说神了,您说得对,我军还是尽量避免同他交战。”
曹文诏上任到达太原,知府见他只有三千人马,热盼的劲头一下子变冷:“曹大人,应抓紧从各地调兵,敌军有二十万,正准备攻城,我们可千万不能做俘虏啊!”
“哼,看你那个胆怯的样真给皇上丟脸。”曹文诏总是满怀信心,“看我如何破敌。”
“曹大人,城内滚木磘石奇缺,箭矢灰瓶不足,敌人攻城,难以防守,要尽快想办法才是。”
曹文诏报以冷笑最好的防守办法是出击。”
“什么,就凭你三千人马,去出击二十万敌军,那不是去送死吗?”知府简直不可思议。
“给我准备好饭菜待我军饱餐后,即刻出城对敌发起攻击。”曹文诏更明确地指示一定要有肉,吃肉才有力气,方能多杀敌人。”
“好吧。”知府官位小,只能听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