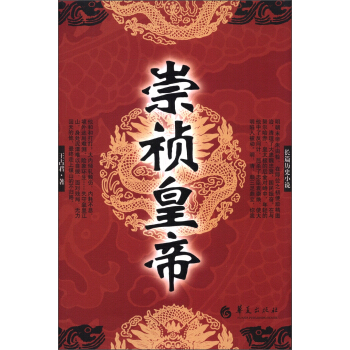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金色秋日,崇祯驾坐乾清宫中,他准备例行上朝处理政务。曹化淳瞄见崇祯身边无人,悄悄靠过来:“万岁爷,奴才有事禀报。”
“昨夜可有收获?”崇祯布置曹化淳,要暗中留意魏忠贤和王体乾二人的动向,并及时奏报。
“万岁,昨夜奴才是跟着王体乾出宫,见他进了侯国兴的府邸。奴才等了片刻将要离开,魏忠贤竟也去了。”曹化淳不敢看崇祯的眼神,“奴才见此情景,就没再离开,直到一个多时辰后,他们才先后出来。新的发现是,崔呈秀也从侯府鬼鬼祟祟溜出。”
“好,继续你的暗中监视,朕是不会亏待你的。”崇祯脸上毫无表情,“传王体乾来见。”
王体乾应召来到,跪倒叩拜:“圣上呼唤奴才有何驱使?”
“王公公一向很是忙碌啊!”
“奴才近来还算轻闲。”
崇祯冷笑一声:“轻闲得夜间偷偷出宫。”
王体乾一下子怔住了,他没想到崇祯竟然掌握着自己的行踪。情急之下,扑通跪倒:“万岁爷,奴才有罪。”
崇祯有意含而不露侯国兴府邸,你大概是找不到吧!”王体乾不知是谁泄露了他的行踪,也不知何人是崇祯的内线。如今他也顾不得许多了,先设法保住自己要紧:“万岁爷,奴才一直屈从于魏忠贤的淫威,昨夜到侯府暗中相会,进行了密谋。”他把各人的说法和态度,一五一十地如竹筒倒豆子全给抖搂出来。
崇祯似乎毫不在意:“看来你还可以救药,全都说了实话,别以为你们是铁板一块,你焉知何人巳向朕表明忠心。此后凡有内情,你要及时报与朕知,早说早记在你的功劳簿上。”
王体乾吓得全身颤抖:“万岁爷,奴才决意同魏忠贤决裂,只求皇上饶过奴才的狗命,允奴才归乡务农。”
“少时金殿之上,朕自有决策。”崇祯起身乘上抬辇在徐应元、曹化淳等人的陪伴下,登上了金殿的龙椅。他心中暗说,好阴毒的魏忠贤,自己与周皇后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面对眼下的局势,越发要稳住阉党。
“宣王体乾上殿。”崇祯发出谕旨。
“奴才见驾,”王体乾上殿跪倒叩首,“万岁,万万岁!”
“王公公提出年老体衰,请求辞宫还家。”崇祯有意顿了一下,看看魏忠贤的表情,“王体乾在宫中服侍先皇多年,劳苦功高,理当养在宫中,所请不准。”
“奴才谢主隆恩!”王体乾叩头不止。
崇祯瞥见,魏忠贤放心地笑了。他则在心下冷笑:“着王体乾仍留在朕的身边当差。”
“奴才定效犬马之劳。”王体乾起身立过一旁。
“宣崔呈秀、李养德、陈殷、朱童蒙上殿。”
崔呈秀等四人应声出班跪倒,叩头罪臣听旨。”
“四位爱卿,杨所修大人参你们夺情失孝,此事可是有的?”崇祯发问,语调并不严厉。
四人低头回答确有其事。”
“本朝以孝立国,对堂上慈严不孝,其实即为不忠。但念尔等为国夺情,事有可原,着令李养德、陈殷、朱童蒙三人回家守孝三年,期满之后官复原职。”崇祯顿了一下惟崔呈秀身居要职,不得离京,仍在兵部任用。待边关宁静四海升平,朕再准其还家补尽孝道。”
四人齐齐叩头,齐声回应臣等谢主隆恩!”
魏忠贤心下感到,崇祯决无害己之意。按理说这四人中崔呈秀乃兵部尚书,握有兵权,崇祯正可借机把其放逐回家收回兵权,可竟然独独留下兵权在握为己死党的崔呈秀,这不是明明向自己示好吗?魏忠贤实实没想到,接下来的事情足以令他震惊。
“宣宁国公魏良卿上殿。”崇祯再传口谕。
魏忠贤当时就懵了,尽人皆知太监魏公公无子,而魏良卿是他的嫡亲侄子,等于是他的亲儿子。崇祯怎么突然想起宣他进见,莫非要拿他开刀?魏忠贤心情忐忑,惴惴不安。
魏良卿也是心中揣着小鹿一样突突乱跳:“微臣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魏卿身为国公,一向勤于政事,为大明之栋梁柱石之臣,功高山岳,光照日月。为旌表卿之大德善行,特颁赐免死铁券,着礼部即日加紧制作,以保魏卿富贵千秋。”
一时间,满朝文武全都怔住了。魏良卿本人也好像听错了一般,呆呆地竟没有任何反应。王体乾也犯起了嘀咕,莫非这个魏忠贤也得到了皇上的信任,这个老不死的真有道,先皇听他摆布,崇祯又和他一个鼻孔出气?他暗自谢天谢地,幸亏自己及时向皇上投降,要不然还不是得掉到屎盆里。
魏忠贤见侄子发呆,急得他连连低声提醒:“良卿,赶快谢恩,别发呆呀,向皇上谢恩。”
魏良卿这才反应过来:“臣受之有愧,谢万岁天大皇恩!”
“不用谢了,只要忠心事君保国,朕愿足矣。”
“臣便万死也不能报皇恩之万一。”
“众卿,朕少年登基,一切仰仗百官忠心视事。而今先皇已去,朕只愿天下稳定,四海升平。臣子无论官职高低,只要忠贞为国,朕决不吝封侯之赏。”崇祯等于当朝宣布,他求的是朝中安定。
文武百官齐声应答:“万岁少年英俊,睿智聪颖,我大明百姓有福,社稷有幸,中兴有望。”
当晚,月明星稀,皎洁的月光把大地照得一片银白。按说这不是阴谋聚会的好时候,可魏忠贤等人又迫不及待地在侯府相见。大概是魏忠贤心中有底了,今夜还增加了一个死党,就是吏部给事中陈尔翼。魏忠贤环视一眼在场的同盟军,见众人无不以虔诚尊敬的目光望着他,只有客氏有些洋洋不睬。他意气风发地对在场的人说还是老夫判断正确,如何?崇祯不会同我们闹翻的。”崔呈秀也打消了造反的念头干爹就是见解高明,看崇祯的举动,他是怕我们闹事,才千方百计安抚我们。”
“说得是,平常皇上也从未对厂公有一丝反感。既能两安,还是不要冒险为上。”王体乾心中暗暗向崇祯使劲。
“你们哪,是一群混蛋!”客氏气得骂了一句,“怎就不想想,崇祯的举动有多么反常,他偏偏留下崔呈秀,又平白无故要给魏良卿颁免死铁券,这不明摆着使的是稳军之计。”
陈尔翼有点附和客氏的倾向:“崇祯的所作所为,属实有悖常理,让下官也觉可疑。”
“要我说,多余费尽心机讨论这些,管他崇祯是真心还是假意,我派两名高手,将他刺杀了事,免却后顾之忧。”侯国兴还是站在他妈的立场上,“厂公再随便找一个小孩,让孩子挂名当皇帝,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王体乾以见证者的身份发言:“皇上也不是那么好刺杀的,咱家见他格外小心谨慎,登基头两天,连觉都不睡。万一失手,再把我们供出来。那可就是偷鸡不着,反而蚀把米了。”
“胡说,弑君之举岂可轻动。”魏忠贤当即予以否决。
客氏冷笑几声,看似对儿子,实则一语双关捎带着魏忠贤:“不听老娘言,吃亏在眼前,早晚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魏忠贤也给说得有点生疑,他也是为了安抚客氏:“陈大人,明日你上疏弹劾崔呈秀,我们再试试崇祯的底牌。”
“再试,崇祯不还是那一套,表面上必定要夸奖崔呈秀。”客氏不以为然,“纯粹是多此一举。”
“老夫还有办法,不信就试不出崇祯的真实内心。”魏忠贤不肯再明说了,知道是他有妙计在胸。
公元167年九月二十五日,来京述职的江西巡抚杨邦宪向崇祯上书,历数魏忠贤的十大功绩要求给魏公公在北京城建一座生祠,让百官和百姓好有奉拜的场所。
这下子明显是在将崇祯的军,如果同意,将会给反阉党的群臣多么大的打击,表明崇祯对魏忠贤是完全信任的。如果反对,那么也就暴露了崇祯的真实意图。崇祯虽说年轻,但应对政治斗争还是有一套的:“杨大人所请还请魏厂公自己谈谈看法。”
魏忠贤明白这是把球踢给了他:“万岁,此事万万不可,以往各地建生祠奴才都是反对的。先皇批准,奴才也无可奈何。其实这是折杀奴才,哪有活人建生祠的道理。”
“既然厂公也反对,朕也就不违背厂公的意愿了。还没修的就不再修了,正在修的也不能半途而废,要把它接着修成。”崇祯颇为客气地问,“厂公你看这样做可否?”
“万岁爷皇恩浩荡,奴才感激涕零,没齿不忘大恩。”魏忠贤不住地叩头,他彻底放弃了造反的念头。
但客氏始终是冷眼旁观朝中发生的一切,她见魏忠贤不再到侯府来,便主动约其来相见。
魏忠贤觉得对客氏过于冷落了,虽说心下不愿,还是应约前来:“客妈妈,这一向少来问候,身体可好?”
“小魏子,不是我危言耸听,还遑论什么身体好坏。不出一个月,你我的人头都要落地了。”
魏忠贤笑了:“你呀,认准了崇祯必然会加害我们,巳是走火人魔,这念头难以化解了。”
“崔呈秀听你的,他这兵部尚书,崇祯铁定是要动他。趁眼下兵权在手,干掉崇祯还来得及。”客氏几乎是在恳求,“看在你我对食一场的分上,让崔呈秀发动兵变,保住我们的性命。”
“客妈妈,你说得太容易了,兵变岂是轻易可以发动的,我说过多次,一且失手,九族倶焚。”
“咳!”客氏长叹一声,真正地绝望了。
魏忠贤走了,侯国兴眼见客氏泪花盈眶,禁不住问道:“母亲,难道我们的行动,必须得魏忠贤同意吗?”
“我儿此言何意?”
“母亲无须受制于人,别再乞求崔呈秀兵变。儿手下有两员武功盖世的暗杀高手,派他二人去将崇祯除掉,不就万事大吉。”“兴儿,你说这二人真的能行?”
“出手必成,十足把握。”
“唤他二人来见。”
“遵命。”很快,侯国兴把二杀手领来。
“拜见客妈妈。”二人躬身见礼。
客氏细细打量,见二人身躯矮小,体态精瘦,一身黑衣,薄底快靴。侯国兴逐一介绍母亲,这位是来无踪,这一位叫曲无影。”客氏眼中闪出疑惑:“怎么没见他二人带有武器,难道是赤手空拳就能置人于死地?”
侯国兴笑了:“二位,把武器展示一下。”
来无踪把腰带一抽,一柄软蛇剑现在手中。而曲无影则是从靴帮上取出两把短刀在手妈妈请看。”
侯国兴补充说母亲,他们身上的暗器多着呢,什么飞镖、袖箭、迷魂吹管、三步倒毒药,杀人的东西应有尽有。”
“好。”客氏还有担心,“皇宫不比别处,倘万一失手行刺不成,甚至负伤落入对方之手呢?”
来无踪回答:“我们从未失手过,只要出马就是必胜。”
“我是说万一落人敌手,又当如何?”客氏盯住问。
曲无影回答得相当干脆:“我们不会落人敌手。”
“你们就这样自信?”
来无踪做出明确的回应:“我们一旦遭遇即将被擒的局面,会咬碎衣领的毒药丸自尽。”
客氏放心了这就好。”
“母亲,让他们行动吧。”侯国兴请示。
“可以。”客氏同意,并向二杀手许诺,“祝愿二位马到成功,事成之后,我有千两黄金谢仪。”
“谢过客妈妈,请等候我二人的捷报。”两杀手拱手一揖,闪身出房,即刻不见了踪影。
是日,云南道御使杨维恒进京,他本就是阉党的人,也在当暗来拜见魏忠贤。看见他送来的厚礼,一个主意忽地跃上魏忠贤的心头。“杨大人,远道来京,还带这许多礼物多有不便。”
“哪里,孝敬厂公自是下官分内之事。”杨维恒小心翼翼,“云南地处偏僻,些须薄礼都难上眼,实在不好意思。”
“杨大人过谦了,咱家其实用不着礼物。而今我巳不为皇上所用,倒是王体乾仍为皇上青睐。杨大人可将这些礼物送与王公公,以后凡事他可对你有个照应。”魏忠贤来了这样一番话。
杨维恒可是受不了啦:“厂公,你错怪下官了。我可不是见风使航的小人,厂公待我天高地厚,王体乾他如何受宠,下官也不会抛下厂公向他投靠,这是万万做不到的。”
“杨大人,倒是你误会了。”魏忠贤说出他的本意,“咱家是要你上书弹劾崔呈秀。”
“这,崔大人是您的义子,身任兵部尚书,是厂公的得力助手,与下官也颇交好,怎地要弹劾他?再说,这又与王体乾何干?”
“弹劾上书交与王体乾,能尽快上达圣聪,且他能助一臂之力,将崔呈秀问罪拉下马来。”
“下官这就不明白了,几次有人弹劾崔大人,皇上都保他无事,不也是对厂公的保护?他若不保,厂公不也就首当其冲?”
“杨大人有所不知,近来弹劾崔呈秀的奏疏已多达十数件。”魏忠贤显出无奈崔呈秀只怕是不保了。”
“厂公已不是总管太监,这绝密消息又是如何得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