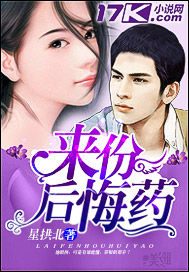其他孩子是闹着玩,而小休一副玩儿命的架势,最后居然把他们都给吓跑了,当然,也有可能是被他流的那些血吓跑的。
妈妈遗弃了他,爸爸又常年不在身边,曲南休常常被镇子上的大孩子欺负。
他气极时,简直像头被激怒的小公牛,斗志昂扬,挂彩自是家常便饭,只要不让奶奶看到就好,不然她得心疼得犯病。
如果他能拉下脸来服个软儿,昧着良心说几句讨好的话,也许局势就不会那么糟了。
可这孩子偏偏是个犟骨头,脾气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要他服软儿,那比让蚂蚁踩死大象还难!
以往受了伤,自己简单处理下,挺挺就过去了。这一次,伤得貌似有点儿重,因为一块板儿砖不偏不倚,正拍在了他的颈动脉上
“小休,出来吃饭了!”
奶奶明明就在外屋喊他,可听着却好像隔了十万八千里。听觉已有些模糊。
他拼尽全身力气喊了句:“奶奶,我困了,睡一会儿再吃!”
“哦,你睡吧睡吧。”
奶奶倒也没多想,宽心地到隔壁做针线活去了。
血,越流越多。小休感到头越来越沉,眼皮越来越重,逐渐感觉不到自己躯体的存在了。眼前是瘆人的黑暗。
他开始后悔,刚才干嘛那么冲动?要是咬牙忍一忍,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个局面了!
“唰——”
一道突如其来的白光,如刀如剑,笔直刺破无边的暗夜,给了小休一些积极的刺激。他拼命挣扎着想看清,那光来自哪里。
白光纵横快速延伸,表面趋于清晰,最终亮出了一台巨大的老式座钟!钟壳通体红木,样式极简不带任何装饰,唯有隐隐流动的光泽,彰显着它的不同凡响。
“滴答,滴答”
那是时间在流逝!
一个垂死的人听到这声音,有如生命进入倒数,触耳惊心!
小休的身子在剧烈颤抖,呼吸已经微弱得快要没有了!
“要死了吗?我还有那么多事没做,那么多话没说!我每天都干了些啥呀?真后悔没好好学习,把时间浪费在和人打架上。如果老天爷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
悔恨的泪水接连落下:“不,我不能死!不能让奶奶和爸爸,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也不能让棱花守寡!(虽然他俩八字还没一撇!)”
想到这里,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和灵感,他挣扎着跌跌撞撞来到大钟跟前!
那钟比他还要高,奇怪的是,刻有罗马数字的表盘部分,并没有通常那层玻璃罩,以至于他可以触到指针。
忍着剧痛,拼命踮着脚尖,小休用尽所有的力气,将那指针胡乱地扳了几圈,最后累得瘫倒在地上!
然而针并没有停下。被人工干预了之后,仍以同样的速度“滴答,滴答”有条不紊地走着,向世人彰显时间的公平和稳重!
“唰——”
白光一现,四周似乎又恢复了原样小休起身行走如常。
诶,屋子怎么好像比以前小了似的?
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惊见苍老了十几岁的父亲,略显佝偻地迎面走来,而自己比他已高出一个头!
“爸,你”小休瞠目结舌,自己发出的,已然是陌生成年男性的嗓音,“奶奶呢?”
眼见着父亲的眼圈渐渐泛红,缓缓拍了拍儿子说:“爸知道,你从小是被奶奶带大的,你跟她有很深的感情,她老人家走了,你受了很大的刺激,但是人啊,谁都难逃这一天”
晴天霹雳!
到底发生了什么?!
“唰——”
还是那道诡异的白光,总在不经意间颠倒乾坤!
见鬼!不是明明正走在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么?自己依旧还是那个九岁的少年!
是梦,还是幻觉?
难道奶奶还健在,爸爸还没老?
方才那一幕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因为太恐惧失去至亲,眼泪不自觉地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他不顾一切向家奔跑,飞起一头发风。
路上又遇到了那几个大孩子,他们嘲笑他,侮辱他,上一次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但这回,小休硬是忍气吞声,无论怎么受气,只管捂着耳朵跑开。于是相安无事。
原来,退一步真的可以海阔天空。
万幸,奶奶健在,爸爸还没老,一切就如同刚刚按了“回车键”一样神奇!
当然,那时的曲南休还不懂回车键,因为他还没摸过计算机。
很久后他才琢磨明白,什么跟人打架受伤,什么拨动座钟的时间、看到十年后的家——原来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仅仅只在自己的脑海中上演过!
可为啥会如此逼真、如此合乎逻辑呢?
九岁的少年百思不得其解,去请教他崇拜的“什么都懂”老师。
董老师耐心听完,担忧地望着他说:“如果不是梦,那可能是幻觉,曲南休同学,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头一次听说“幻觉”这个词,曲南休一门心思想搞懂它:“老师,什么是幻觉?”
“就是明明不存在的东西,明明没发生的事情,你却看见了。有可能是睡不好觉或精神压力大,造成精神方面”
老师不忍心说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
“哦,幻觉,幻觉”
满脑子都是这个新鲜词儿。曲南休预感到,这也许就是解开所有疑问的钥匙。
当他向别人提起时,招来不少“神经病”之类的嘲笑。
唯独当年十三岁的棱花,从不怀疑他所说,一如既往用自己的方式袒护着他:“南休,你说的我都信。对了,董老师不是说过,不明白的时候应该多看书,书里什么答案都有吗?”
少年望着骨肉匀称、笑容甜美的“姐姐”,坏坏地想:真的什么答案都有吗?那我想知道,长大以后,你会不会变成我的媳妇儿呢?
“南休,你在笑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嘿嘿嘿。”
“我觉得,你肯定没想什么好事。”
“绝对好得不能再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