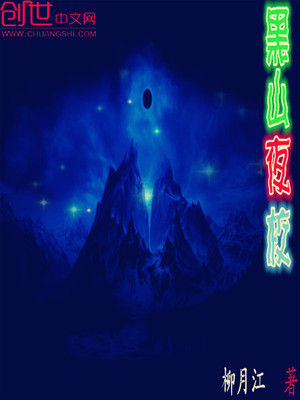金棕色衣衫的少年,正是谢安莹的二哥谢安闰。
此次他与大哥谢安瑶一同北上京安城,是因为收到了祖母的那封书信。
——祖母的意思,一来是想让兄弟二人回京准备春闱,二来便是说起妹妹的婚事。
孟家在南郡正是以诗书传家,家族中无论男女皆是熟通文墨,只是家风淡薄不争名利,否则春闱这等事情,怕是要被孟家子侄沾满了金榜的。
谢安闰与谢安瑶兄弟二人,自小就在外祖孟家教养长大,故而对他二人而言,春闱赶考也是胸有成竹却并不热衷。
只是他们到底是姓谢的。
祖母一封信,外祖看过之后施施然道:“去瞧瞧也好……”
外祖看淡一切,考与不考都不强求拘泥,想着既然来信了便也是缘分使然,当即命孙管家备了车马日用,这就送他二人考试来了。
外祖家与谢家都要他们来参加春闱,但对于谢安闰来说,他却更想借此机会,见见自己那素未谋面的妹妹。
北地京城,女子的婚事说得较早,他与大哥还不急着婚事,谢家就已经开始张罗妹妹的了……
谢安闰想想都觉得很奇妙。
不过祖母来信着实奇怪,按说妹妹留在京城应该能嫁得更好,却不知为何要托付给外祖家,就算南郡有得是好儿郎,但远嫁毕竟有远嫁的难处。
连他都能想到,祖母怎么会想不到呢?
不过这些事情,就不是他该操心的了。
谢安闰昂首马上,迎着渐落的夕阳继续前行,他的脑海中,现在全是对自己妹妹的想象。
他幼年时就被父亲送到外祖家,对谢府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是到了孟家,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位红颜薄命的大美人——母亲容貌过人,据说美艳至极,可惜生下妹妹不久就去了。
谢安闰在舅父舅母家长大,舅母待他犹如生母,所以他从来也不觉得缺少母亲的关爱。
这一路走来,她只是对妹妹的容貌格外好奇,想着或许能从妹妹的相貌上,一睹自己生母的样子,这才一心想要快点见到才好。
谢安闰一边走着,一边回头去看谢安瑶。
今日也不知怎么回事,往常在马上从不输给他的兄长,今天却走得特别慢。
“兄长,哥哥,谢安瑶!你要是不想走咱们就住下来,你要是想走咱们就快点走!”谢安闰是个急脾气,说话的功夫,两条漂亮的剑眉便已经皱在一处:“这么磨磨蹭蹭的,别说明天了,再多三五日也到不了啊!”
谢安闰的话丢出去半天,才听见谢安瑶慢吞吞地答了一句。
“恩,那就先住下来。”
谢安瑶是长兄,即便是在外祖家和舅父家,他也是年纪最大的孩子。
他被谢家送走的时候,已经年近五岁,该记得的,不该记得的……他都记得了。
他记得那些往事,甚至记得柳氏……只是那时年幼,还分不清许多事情的是非对错,只是像纸上看不懂的文字一样,浅浅地记录了下来。
而后,随着年纪的增长,当他再度将往事翻出来回味时,却品尝出了不一样的酸涩。
父母失和,母亲病逝,为娶新妻,将两个儿子送往外祖家……
虽然谁都没告诉过他这些话,但他却知道,这可能才是最接近真相的真相。
至于那位妹妹谢安莹,他是见过的。
妹妹还没出生时,母亲就忽然得了一种治不好的怪病,整个人一下子瘦弱得没了人样,每日除了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
后来,母亲拼了命生下了妹妹,谢安瑶到现在都记得他第一次看见谢安莹的样子——身体小小软软的,皮肤白白嫩嫩的,眼睛又黑又漂亮,却不会看人。
谢安瑶也记得母亲说过的话,母亲说,每个孩子对于她来说都一样,妹妹和他们兄弟二人也是一样的,她应该到这世上来看一看。
可是她看不见……
想起这个妹妹,谢安瑶的心情总是十分复杂……也不知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从小时候起,只要想起自己二人被远远地送走,而妹妹却能被留下,谢安瑶的心中很是有些吃醋的。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谢安瑶渐渐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却又觉得留在谢府也许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两种情绪反复互相纠葛,连他也弄不清楚到底哪一种才是对的。
谢安瑶面无表情地继续前行。
这一路,眼看离谢家越来越近,他心中的各种回忆和感触也开始上下涌动,这样的情绪对他来说更像是一种负担,压迫着他的脚步,令他无法毫无顾虑的面对。
谢安闰听见兄长这样说,又看见他一副落落寡欢的模样……谢安闰哀嚎一声,将马头拨转了回来:“既然要住下,还是别往前走了,方才那块地方扎营就不错,我们停下来,正好等等后面的孙叔和马车。”
谢安闰在小事上跳脱胡闹,可大事上,他却是极为尊重自己的大哥的。
当他看出谢安瑶似乎有心事的时候,他果断放弃了自己看美人妹妹的心思——大哥这一路上都十分不安,或许他们也应该停下来好好谈谈。
至少也该让自己知道,即将到达的平阳侯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
谢安莹还不知自己的婚事已经被抛给了外祖家,李承霆当然更加不知——若是知道的话,恐怕谢老夫人那封信绝对走不出京安城。
李承霆将文书送到的第二日,就听说海晏楼动工了,他前去查看了一圈,见一切井井有条十分稳妥,便以此为借口,又跑来找谢安莹说话。
李承霆的银子和心,都已经交给谢安莹保管,现在他人来了,谢安莹自然也不会拒绝,只是吩咐红提将院子里其他人支开,莫要被人瞧见就好。
李承霆轻车熟路地找了椅子坐下,不远不近地打量着谢安莹,越瞧越是喜欢,直到瞧得他自己都觉得过分,这才收回目光道:“陈家十分尽心,这间酒楼盖起来,当是京安城之最了。”
谢安莹要的便是这个“之最”。
凡事只要做到精湛,做到极限,哪怕本是见不起眼的小事,也会因此而变的伟大起来。
酒楼更是如此。
京安城第一酒楼,与第二第三的差距,何止万里?
谢安莹微微低头,避过李承霆那微粘的目光,笑道:“我不但外头要最好的,里面要要独一无二的。我与陈家知会过了,让他们给我将每个雅间都做成不同的样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