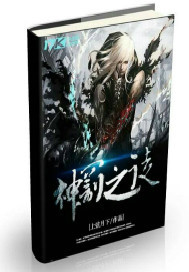血脉的行走,暗合了某种规律,如果能够掌握这道规律并且烙印出来,无疑会是一记强大的符文力量。
可血脉行走的路线太过晦涩玄奥,唐松无法在此刻对它参悟成功。
黑沉沉的夜空也在这时迸射出一道光芒,好像黑色的幔子从中撕裂。亮光里出现一道模糊的身影,似男似女无法分辨性别。这道身影身披金甲,背有四翼,脸庞之上燃烧着烈火。金甲人语气*,对着唐松说道:“吾乃神灵手下众子之一,因你神灵有感特来贺喜。”
明明只是这一个人在说话,声音却好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好像人山人海都在云端之上呼喊。
这金甲人又道:“神的国度只为神的众子和侍奉他的人而居。那些不敬畏神灵话语,或是敬畏了话语却又不做神所命下的事,这些人必将承受来自至高神的愤怒。现赐予你七神符中的第一符,此符又唤作善恶符。但凡被你种下此符的人,心中恶念多深,他的心魂就遭受多大的痛楚。直至在神荣耀的名下被感召解脱。”
接着又有沁人的馨香和宏亮的梵唱从那云端上传来,唐松觉的这香味和歌声似乎曾经在哪里见过,可是想细细回忆时脑海中就猛然疼痛起来。
金甲人重新回到云端之上,而耀眼的光芒也随之消失。夜色苍穹再次幽蓝深沉,好像刚才那一幕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唐松,你怎么了?”帕隆晃了晃唐松的身子,焦急地问道。
唐松也从迷惘中回过神来问道:“帕隆大叔,刚刚……刚刚你有没有看到天空中有道亮光?”
“亮光?”帕隆疑惑地道,“什么亮光?”
“哦,没。些许是我看花眼了。”唐松笑道。可是额间神恩之灵却波动了一下,唐松内视而去,发现神恩之灵附近的血气已经固定地按着一条路线缓缓运行着……
神恩符文!那个金甲人说有神七符,这善恶符只是第一道符文。
原来自己的神恩血脉,并不是像塞缪尔说的那样只有一道可以让世人免受神罚的希望符文!
只是血气的运行虽然已经有了规律,可是唐松还没有对他参悟成功,也没有能力在此刻就烙印出这道神符。
但唐松还是很开心,这几个月来的修行自己的武技和天启之灵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可是这神恩之灵却一直没有动静。没想到今夜的一个想法居然能够激发神恩血脉的力量,而随着这缕血气的运行自己的灵气也在悄然提升。
“大叔,我们回去吧!”唐松从青石上跃下,话语中都多了一分喜悦。
帕隆不清楚唐松的心情为何突然明朗起来,不过这终归是件好事,他也就没有细问。
.
时令已迁,现下也不再是西风夹寒的季节,温度也回暖到了二十来度。即使唐松所住的地方处在近郊,但夜里也是温凉怡人。
唐松开着窗门,*着上身盘膝坐于地上。原本就小有规模的身材也在这两个月多的时间里锻炼的更为健壮。
“凝!”唐松右掌微缩,灵气在血脉之力的作用下向着右掌聚合。
淡淡的金光萦绕在掌纹上,随着唐松逐渐急促的呼吸声这道符文变的更为清晰。
可就在符文凝聚到将近一半的时候,金光一跳,灵气没来得及续上,这道符文立马涣散了。
从唐松开始摸索出一些门路后,这已经是第十四次尝试凝聚神符而失败了。
没有选择放弃,凭着骨子里的那股执拗唐松再次闭上双眼滋养自己的神恩之灵,体内原本稀薄的灵气重新变得浓郁……
熹微初露,天边泛起淡淡的鱼肚白,一夜的时间也在不断的尝试中悄然度过。
当第一道晨光从唐松胸前抬升到他的脸庞时,唐松睁开了他的双眼。这一次闭眼的时间是他一夜中最长的一次,甚至如果旁人在他身边的话都说不定以为他已经睡着了。
此时他睁开双眼,天边正透出一丝微弱的紫气。目光与日光相聚,唐松自信的一笑,伸出手来轻声道:“善恶符,凝!”
一缕缕灵气从他体内各处剥离而来,在他掌心凝聚为灿烂的金光,这一次金光没有散去并且活跃的程度远超前面几次好几倍。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分钟,唐松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濡湿,眼眸中同样出现了疲乏之意。
“善恶符,你还不出来!”唐松低喝一声,颅内神恩之灵鼓荡将全部的血脉之力激发出去,血脉之力化为一涓灵气溪流融入掌纹之中。
随着这最后一股灵力的输出,唐松终于山穷水尽。幸运的是手中的神符也凝聚成功,金光暗淡下去不再闪烁,在掌纹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图案。
一颗心脏,分为两心室和两心房,这颗心脏周围的动脉也清晰可辨。稀奇的是,这颗心脏不是单纯的血色,而是鲜红中带着微黑。在两心房和两心室上各自插着一把利剑。
善恶符缓缓沉入掌心之中,唐松的手掌恢复了原状。唐松知道自己掌中已经拥有了一道善恶符,虽然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还不能将这道符文凝结到极致,但好歹也是成功地凝结出来了。
长吁一口气,唐松拍了拍自己的双腿,准备起身去洗个澡。
刚站起身,唐松的身体就晃动了下。
是太累了吗?摇了摇自己的脑袋,唐松没有在意这个细节迈步走向浴室。
“哐当!”一声,客厅里一个骨瓷杯子从柜子上掉落在地。而更为剧烈的一次晃动也从地层下传来……
.
“地震啦!”一道高分贝叫喊声从罗茜卡的房间内传出。下一刻就见帕隆和翰迪穿着一套睡衣从房间内匆匆忙忙地跑了出来。罗茜卡更为干脆,直接打开自己房间的阳台小门,纵身一跃跳到了楼下花园中。
十几秒后,浴室大门打开,唐松拿着一条浴巾遮住自己的裆部同样火急火燎的跑下楼去……
.
一场破坏力巨大的地震,几乎毫无征兆地发生在华夏时间凌晨六点十三分的大地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