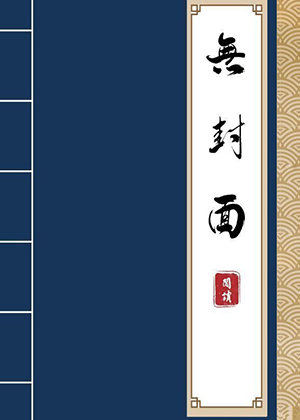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快得像流水,我恍惚以为深山里这样刻板的生活已经过了一辈子那么久,但是忽然又想起,隐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山来了。
习惯是那样一种东西,人在的时候并不觉得,忽然不见了,心里会空出老大一块,老大一块的空白,空空落落的,叫人慌张,我觉得我有必要下山一趟——当然不是为了隐歌,而是因为……盐吃完了。
正碰上赶集的日子,人来人往,小小市集竟也喧哗热闹,卖什么的都有,也有闲聊和纯粹看热闹的,我买了盐往回走,忽然听见一段对话——
“……她要出嫁了?”
“就是呀,那姑娘不愿意,和家里斗法,我家不是离得近嘛,被整得死去活来,一早起来,看见满院子的鸡都口吐白沫瘫了一地,那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结果第二天开门一看,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又都活蹦乱跳了。我们那一片的鸡呀、鸭呀、兔子呀……都死去活来好几回了。”
“怪不得你们村今天来人最多。”
“是呀,好不容易那姑娘被关在家里了,趁这空当,赶紧把东西卖了是真……”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那姑娘就是隐歌……也许并不是,会使毒的唐门女弟子那么多,即便退一万步说,那个被逼着出嫁的姑娘就是隐歌,又和我有什么关系了?难道我要插手唐门的家务事?
想得这样通透,可是一双脚偏偏不听使唤,拖着我就往唐门方向走,也罢,不去看一眼,总不会心安。
我不愿意承认,但是对那个麻烦的小姑娘,我忽然生出一种叫牵挂的感觉,想起时有一点头痛,也有一点,暖暖的怅意。
赶到唐门时,天已经快要黑了,我远远就看见数十个唐门弟子举着火把团团围住,我攀到附近的树上,居高临下,一眼就看见了被围在中心的人——是隐歌。
自然是隐歌。
她仍穿着那套可笑的竹绿色衣裳,面色惨白,更惨白的是她手中的刀,她将刀比在自己颈上,大声道:“你们再逼我,我就……”
一咬牙,素手往上一推,恍惚一道刀光过去,寒气森森的凛冽。
一行鲜血从她颈上流了下来,竹绿色的衣裳染了血,颜色格外触目,火光将夜照得亮如白昼,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的眼睛,看到她眼中的颜色,那样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就想起她对着一地焦黑的兔子问我,“如果我走了,你会不会想我?”
那时候她眼中的神情,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倔强和刚强?
她像是随时都会有眼泪落下来,但是并没有。
反是我,全身的热血都往上涌,然后我就落进了包围圈,落在她的面前,只一伸手,猝不及防,她的刀就落到了我手中。
“你……你怎么来了?”隐歌一惊,看清楚是我,惊诧全变成了欢喜,那样多的欢喜,在刹那间照得我的眼睛也亮了,就仿佛是烟花盛开,又或者流星划过夜空,那样迅疾,但是那样璀璨。
眼泪终于掉了出来。
我微微笑了一下,替她擦掉,“你有事,我怎么会不来?”
“你有事,我怎么会不来?”多年之后我想起这句话,想起当时的神情,当时欢喜,当时如烟花。
你知道吗,烟花那样美,也开不过一个瞬间。
“你救了她吗?”陆茗抿了一口酒,笑吟吟地道,“隐歌既然功夫不济,想必唐门也不会过于重视,以叶兄弟的身手,要带她走,想来不难。”
我点头,另倒了一杯酒,说了一个“是”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