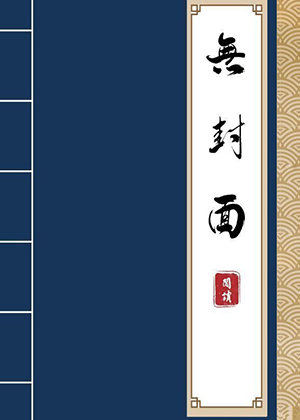忻禹落座,从旋丝玛瑙盘中拈起一块糕,并不入口,却漫不经心说道:“阿微疫了。”
疫了。太后虚应一声,仿若空茫无所依,许久才回神来:“各地藩王都进京来吊丧了吗?”
忻禹回道:“都来了。”
太后凝视他:“你这孩子,怎吗连母亲也骗起来了——勤王和瑞王也来了?”
忻禹也不意外,“母后明鉴,六哥和十一弟没来,不过都有正当理由,西北边不安宁,十一弟走不开。”
“那勤王呢,他也在边境吗?”
“六哥病了,禁不得舟车劳顿。”
“那倒是真的,”太后微叹了口气,“病来如山倒,再怎吗要强的人也禁不得病,你多派几个御医去慰劳吧。楚地民风剽悍,你明知你六哥身体不好,还让他去操那个心,他若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教我如何同先帝交代。”
忻禹悠悠地道:“母亲教训得是,孩儿疏忽了。可是楚地,非六哥那样的能臣不能治啊。”
太后微微一笑,“他在楚地吃苦也够了,让他换个舒服点的地方——虞地如何?”
容郁双腿麻木,正寻思他们母子不知还有多少话要说,猛听到“虞地”二字,不由吃惊。楚地民风剽悍世所共知也就罢了,到底山明水秀,还有个去处。可是虞地,别人不知道,容郁出身虞地,却是再清楚不过,目之所及山穷水恶,有道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从来民怕官,此地官怕民”。
这太后,绝不是好易与的人物啊——是了,好易与的人物又如何能护着非嫡非长的皇帝从先皇诸多子嗣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荣登大宝?
却听忻禹道:“母亲说得是。不过我们兄弟许久不见,他若回京,就先在京城住上一阵吧。六哥外出为王这么多年,想必也想家得紧。”
太后微笑,“后宫不干政,你拿这些事来与我老婆子啰唆什么。”转了目光向容郁看过来,却不问她,反道:“洛儿进宫了吗?”
“自然,这几日都在兰陵宫守着呢。”
太后哦了一声,“这孩子,奈何姓柳。”言中憾意拳拳,一顿,又道:“行了,我今儿也乏了,皇儿你告退吧——这孩子……不错。”
忻禹行过礼,回头同容郁退了下去。容郁没敢多问,看着忻禹的脸色,知道自己算是过了一关——只是太后那“不错”两个字吗?关睢宫住的那些女子,是不是也都去觐见过太后?她又说了什么?太后与皇帝谈论政事并没有避开她的意思,许是以为她听不懂,许是她听懂了也无关紧要,真的,一个深宫中没有外戚撑腰的女子,知道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或者,他们根本就把她当了死人。
关睢宫的女子都没有死,比死人也只多一口气,她们是不能走出关睢宫的,外面的人也不许走到关睢宫去,甚至连关睢宫在哪里都无人知晓。关睢宫是一个传说,亦是一个代号,幽冷,寂寞。时间、生命、美貌,以及金钱权势这些尘世中追逐的东西,对关睢宫毫无意义。
容郁庆幸自己躲过这一关,却也知道,自己最终的归宿是逃不过的。
是夜忻禹留宿翠湖居,容郁亲手煮了碧粳粥给他当夜宵。忻禹喝了一口放下,问道:“膝上还疼吗?”容郁心中微暖,答道:“长者赐,不敢辞。”忻禹嗯了一声,续道:“你……莫要怪她。”
“陛下言重,容儿担当不起。”
忻禹低头看折子,容郁以为没事了,蹑手蹑脚要退下,忽忻禹道:“前儿朕给你的寒冰刃呢?”容郁一愣,意识到他说的是那日给的碧玉匕,心下一紧,这当口却也没什么可以搪塞的,只好老老实实回道:“臣妾随身带着呢,陛下——要看吗?”忻禹抬头来对她微微一笑:“你先收着吧。”
容郁退出几步,长长出口气。
月明星稀,翠湖居里一树一树的木槿花盛开如雪,容郁忽然想起来,皇后这样喜欢木槿,可是兰陵宫里一棵木槿树都没有,莫非是忻禹明令不许?
怔怔地想着,不提防露水打湿衣裳,凉飕飕的风,转身要进屋,忽地树后闪过一道黑影,觉惊叫出声,知棋抢过来问:“娘娘什么事?”容郁轻轻答她:“方才……恍惚有个穿白衣的女子,像是皇后的模样,想是皇后生前爱极了木槿花,如今去了,心里仍是舍不得,常常回来看望的缘故吧。”
知棋一愣,安抚道:“娘娘眼花了,外头风凉,还是先回房吧。”
容郁不理她这话,只怅怅道:“把这一地落花都收拾起来,锦囊装着,明儿我到皇后娘娘灵前烧了寄去。”知棋应声“是”,却听得忻禹在屋里说:“容儿多心了。”
字字萧瑟,如斜阳夕照。
容郁无可辩驳,心想:夫妻廿余载,他竟是一点情分也无吗?心自寒了去。
她不出声,忻禹自然猜得到她所思所想,正要开口,忽然徐公公传话:“禁卫军统领武训求见。”忻禹面色稍暗,吐出一个字:“传!”
容郁知趣,转去侧院。
屋里又静下去,熊熊的火焰吐着蓝色的舌,可是仍让人觉得冷,冷得刺骨。武训跪在地上,字字都惊:“勤王瑞王进京见过平郡王。”
勤王也就罢了,瑞王守在边境要地,手握七万大军,一旦有什么异动,天下即时就乱了。忻禹却并不十分在意的样子,只笑道:“不要紧。”也不传人,坐下来疾拟一道密旨,交与武训:“三日内,无论用什么手段,把这个交到瑞王手中,其余你就不必管了。禁卫统领之职暂由副统领白诚接管,叫白诚来见我。”
武训应诺,要退下,又被叫住,站定,良久,方才听皇帝缓缓说道:“平郡王柳洛,若是无可恕处……一并处决了吧。”
武训躬身应下,心中却是纳罕:皇后一死,平郡王内无强援外无兵权,是三王当中实力最弱的一个,要杀要剐一句话的事,如何竟要皇帝如此郑重?!正想,迎面一盆水泼了过来,武训抹一把脸认得是知棋,诧异道:“知棋姑娘这是……”
知棋惶惶道:“统领恕罪!”
武训摆手表示不介意,可是低头看自己一身湿透,不由为了难,这样的天气,走出去非结冰不可。知棋何等通透之人,自是明了,忙又道:“我刚做了套新衣,是给我哥做的,身量大小与统领仿佛,统领若是不嫌弃,暂且穿了去如何?”武训自无不依之理,换过衣裳,取出忻禹手书,忙忙去了。
知棋转进屋里去,怨怼道:“娘娘就知道拿奴婢穷开心。”
这话放在平日,已经是大不敬,可这时候容郁只是笑,“武统领年轻有为,尚未娶妻,若得了这机缘,你感激我还来不及呢——就这么心疼你的衣裳吗?”
知棋不语,半晌道:“娘娘说笑了,知棋哪有这等福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