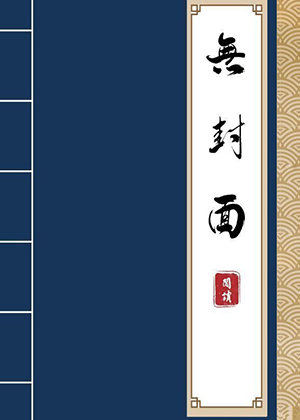柳洛身边有近侍十八人,皆身手利落之辈,也许是柳洛事先有交代,都离两人甚远,除非是传令,否则轻易不与她们说话。近侍有轮班守夜制,但是容郁与朱樱不参与,纵是如此,每日行路过久,仍然让容郁大感疲惫,幸而她幼时随父母吃过很多苦,身子强健,虽然辛苦,却还能支撑下去。
出了京城,景物渐变,行至徐州竟然下起雨来,阴雨连绵,湿热的天气教人极不舒服,但是一路竟开了碗大的花,色泽鲜红,香气浓烈,见所未见,后至越州,又看见一种身量小巧的鸟儿,尾羽极丽,叫声竟空旷如洪钟大吕,若非亲耳听到,简直不能相信是这样秀气的一种鸟发出。
容郁进宫之前也算是到过几处地方,竟从未见如此奇景,她一路贪看新鲜,竟也解去不少忧愁。有时候想起璇玑公主也曾走过这一路,就想:不知道她当初想过些什么呢?那样尊贵的身份,被流放到这么远的地方,这一路行来,不知道有没有自伤身世?
大概是不会吧,容郁想起那个女子刻印上的剑舞,虽有女子柔媚之态,但同时刚强到让人侧目。黑袍人也曾说过她与琳琅交锋,琳琅亦不敢对她出手。
她想到黑袍人,秀眉不着意一挑,她不在宫中,他那么多的思念与追悔,又同谁说去?
容郁一路胡想,队伍已经行至江南,夜色晚了,就歇在扬州。
扬州在江南一带大有名气,论富庶,当时有语“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寻常街面上就有罗绮珠矶无数,豪奢非常,到夜间挂起华灯,处处流光溢彩,连京城都大有不如;论景致,扬州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的美称,又有廿四明月,玉人吹箫,与苏杭算是鼎足三立,互不相让。
容郁隐约听侍从说起,此处行商之风最盛,多大户,多豪门,以商为贵,不以诗书为念,不由诧异,要知道大宇王朝以诗书取士,士工农商,商为最下品,不想竟有以商为贵的地方,却也大大引起她的兴趣。
柳洛是代天子使,自然架子十足,到别处州府无不是府兵清道,一路景然肃然,各州府的长官也巴结到了十分,不想进这扬州,府衙只开出小小一条道来,街边看热闹的寥寥无几,都各行各事,仿佛司空见惯,他面上没有发作,心中却甚是不服。到了官邸休息一夜,第二日要启程,柳洛忽道:“都说江南繁华,别处多有不及,何不多留一日,也让小王开开眼界?”
从官位上说,柳洛是正使,秦祢是副使,从身份上来说,柳洛身为平郡王,秦祢远有不及。秦祢精通世故,自然不肯驳他,只道:“连日累到王爷了,休息几日也是应该。”
柳洛在朝廷中是个让各方势力都头痛的人物,扬州知府是恨不得立时将这小煞星远远打发,但是他既然发了话,也只好应承道:“难得王爷有此雅意,下官自然当尽力而为。”他要找精通本地之人陪同前去,却被柳洛拒绝,柳洛道:“何必这样大张旗鼓,我随便带个下人走一趟便是。”当下点了一个近侍,正是容郁。
两人换过装束,柳洛作一般富家公子打扮,容郁扮作书童,施施然出门去,两人出了门,并不朝瘦西湖那些景点去,反是在街面闲逛。
这一日天气尚好,也有日光,但是并不如何毒辣,倒有暖风一阵一阵,教人心旷神怡,山立得很远,只能隐隐看到天底下一线黛色,街面十分干净整洁,青石板铺就的道路缓步行来,仿佛有千年古韵幽幽。
有鸽子轻盈地飞过去,清远的鸽哨在风里盘旋。
柳洛漫不经心地道:“江南景致果然胜过京城。”
容郁信口答他:“江南有江南的精致,京城有京城的大气,绿水与青山,哪有什么可比的。”话出口才发觉自己放肆了,也许因为远离京城的缘故,又也许是受了两人平民装束的影响——她有多少年没有心口如一地说过话了?容郁苦笑一声,心中恻然。
路边有许多小摊小贩,陈列的商品并不如何贵重,却都玲珑可爱,小巧扇坠,精致头钗,荷包,头巾,等等等等,容郁入宫多年,早已练就喜怒不轻易形诸于色,但是乍见新鲜,也不免多看几眼,想道:怪不得母亲生前一直念叨说江南富庶,原来确是如此啊。
正闷闷中,忽然听柳洛道:“我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容郁心想这些粗陋的东西堂堂平郡王如何看得上眼,定睛看去,竟都是自己多看了两眼的东西,荷包,扇坠,还有一个憨态可掬的泥娃娃。他正低头掏银子出来付账,从容郁的角度看见他侧面的容颜,端的是俊秀无比。
容郁微微一怔,想道:他这样刻意讨好又是为着什么原因?
柳洛买了这些物事并不交给容郁,而是放入袖中,两人默默然前行一段路,有人在街口卖画,见柳洛的派头,知道是个有钱的金主,便拦下他道:“公子,留一幅画像吧。”
柳洛看他两眼,本要拒绝,忽然心里一动,道:“你给他作一幅画吧。”
容郁一惊,已经被推上前去,画师赞道:“好俊的小哥!”容郁心想:我这样子,有什么好俊的!因知是街头常用伎俩,也不与他计较。
那画师技艺不错,不过一炷香工夫,容郁的形容跃然纸上,容郁方要看时,柳洛伸手截了,评道:“有其形而无其神。”
画师不服气,又以为这锦衣公子要赖账,便道:“公子若能在这街面上找到比我画得更好的,这画我就拱手相送了。”
柳洛微微一笑道:“那就烦请你替我磨墨。”
画师乜斜着眼睛看他,果然给他磨了墨汁,柳洛提笔,刷刷几下,竟比那画师更快,他放下笔,将画纸递与那画师看,画师一看之下面色惨白,道:“公子果然高明,小人……小人……”他靠作画为生,原本就只能勉强糊口,那“拱手相送”四字竟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了。
柳洛笑道:“倒不至于赖你这点润笔费。”容郁知他未出口的下句必是:只怕你无福消受。
画师一闻此语,如逢大赦,赔笑道:“公子高才雅量,原也不同我等一般见识。”容郁见他这般模样,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怜。
她原以为柳洛要将画给她看,但是并没有,他展画看了半晌,折好了放入袖中,竟像是要珍之重之。
容郁越发摸他不透,只跟在身后亦步亦趋,忽然听他问道:“我劫你至此,你是不是很恨我?”
容郁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提起此事,那回答却很伤脑筋——如果严词斥责只怕性命难保,要软语求饶,这一刻,却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于是略一沉吟,只道:“我只是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柳洛闻言,微微笑道:“你自然不知道。”只说了这六个字便不再言语,容郁也不问他,两人闷头走路,不知道绕了多少弯子,那路是越走越见荒凉,容郁担心,便道:“平郡王这是要到哪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