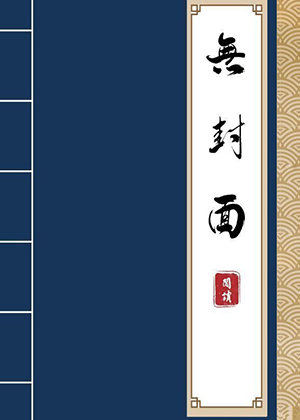忻禹在心里轻叹一声:如果他再等一等,输的或者就是自己,或者。
柳洛怒道:“勤王爷!”
他身后,余年按一按他的肩,秦祢道:“平郡王少安毋躁。”
柳洛之觉得肩上一麻,说不出话来。他在院子里外都安排了自己的人手,奈何相隔甚远,这时候被制却是意想不到。
勤王却不理他,他原本就只是借柳洛之力引皇帝上钩,对这个生在京城,长在京城的公子哥们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所以直接对忻禹道:“既然陛下这么着急想要退位逍遥,又这么着急想要为我大宇王朝新找一任明君,那么愚兄不才,就勉强受了陛下的美意吧。”
忻禹道:“还是六哥深谋远虑,洛儿到底年轻,不是六哥的对手。”
勤王面上有得意之色,道:“陛下过誉,平郡王若有陛下当年一半的心计,今日站在这里的就不是六哥我了。”
忻禹提笔在砚上舔一舔墨,道:“那么朕写了。”
当真眉也不皱,挥毫便写了数字,忽又道:“不知道六哥登基后准备赏赐哪些人呢?秦相奔劳忙碌,居功至伟,应该比户部那些人赏赐更多一点吧,可惜秦相官至一品,再要寸进只能封王了,我大宇王朝总共不过封了三任外姓王,竟有两任逼宫,六哥怕是再没有封王的心思了,那秦相岂不是白费一番工夫?”
秦祢脸色稍变,退一步道:“王爷明鉴,下官愿跟随王爷绝不为区区封王。”
勤王尚未开口,忻禹笔下一停,道:“秦相连王爵都不在眼中,莫非也是想要乾安殿的位置?这可教朕为难了,诏书上新任帝君的名字填哪个才好。”
他摆明了挑拨离间,但是字字都在理,勤王脸上青气一盛,想道:柳洛这小子太嫩,迟点收拾也不要紧,可是秦祢人老成精,拥戴之功确实至高无赏,留下来迟早都是个祸患,总要找机会解决。
秦祢又何尝不知忻禹所言必然是勤王心中隐忧,奈何他的江湖出身与唐门恩怨实在不足对外人说,又想:一旦得到宝藏,管他谁当皇帝,他都可以逍遥去做陶朱公。这时候却说不得,一旦让勤王知道宝藏事还不疑心更重,当下只好道:“王爷莫要听他胡言,此事一了,下官必然挂冠而去。”
他不这样说还好,这话一出勤王疑心更盛,面上打一个哈哈道:“秦相多虑了,我这七弟狡黠成性,二十年前我就已经领教过,如何还会上当,秦相只管放心与本王共治天下,便是封个王爵又有何不可?”又转身对容郁道:“陛下这般多话,还请容娘娘相助一臂之力,娘娘放心,本王必然保证娘娘与皇子安危。”
容郁低声应道:“还请王爷放皇上生路。”
勤王道:“自然,本王与皇帝是亲兄弟,难道还能加害于他不成?”
秦祢听了这话,只觉得彻心冰寒,想道:勤王爷口蜜腹剑,连这等明明白白的胡话都拿来糊弄容妃,难保不同样糊弄我,陛下说得不错,我功至高而无赏,岂不和当初柳氏一样?当初柳氏势大皇帝才不敢动他,忍了二十余年,我论财论势哪点能和当初平懿王相比……说来我确实已经位极人臣,为那虚无缥缈的宝藏而跟着趟这趟浑水,又何苦来着。他心中隐隐已有悔意,又想到柳洛这一路拉拢,便向一旁余年打了个眼色,余年虽然不解,却也还是动手解了平郡王的穴道。
因动作至微,勤王的心思又都在忻禹与容郁身上,竟然让他疏忽过去。柳洛心中自是大喜,表面仍装作被制模样,手底下悄悄放出一线香,这香也奇怪,既不见半点火星,也没有任何气味,却以极快的速度四下蔓延。
这时候皇帝正按着容妃所言笔走蛇龙写道:“嘉祐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容郁念到“让位与”柳洛忽然出口道:“勤王爷,这样不好吧。”
勤王想不到这时候他尚有开口之能,不由向秦祢与余年看去,心里早将他们全家抄斩了十七八遍,只恨这当口发作不得。秦祢装作没看见他的目光,心里却是七上八下,不知今日到底鹿死谁手。
容郁闻言停下来,忻禹也茫然地睁着眼睛看住他,柳洛慢悠悠地道:“勤王财雄势大,柳洛也有耳闻,所以柳洛虽然托大,却也不敢在勤王面前摆谱。勤王若是不信,不妨召几个人来问问,看谁如今还能拿得起刀,舞得动剑。”
他话音方落,只听见围墙那边“咚、咚”,人倒地的声音不绝于耳,勤王只觉得自己的身子也越来越沉,越来越沉,竟是控制不住地软下去,再看四周,秦祢与余年固然没能幸免,容郁也瘫倒在地,连正握笔疾书的皇帝也慢慢软下去,笔落在石桌上,将绢帛污了老大一块墨迹,不由心中想道:平郡王竟是不分敌我通通都迷倒了,那么安插在平郡王府的人手也一时不能作为……这小子年纪轻轻,行事倒狠。
忻禹原本神志不清,被此毒一冲反倒醒了过来,虽然不能动弹,言语却是无碍,他喃喃道:“竟然是……飞花吗?”
无边丝雨,自在飞花,原本是唐门极出名的两样毒,也是琳琅最爱用的毒。自琳琅死后世上已经再无一人能够配制,柳洛所用,只怕还是多年前琳琅封存的旧物,想不到今日自己不但是栽在琳琅的儿子手中,而且还栽在她亲手所制的毒药中,这……算不算是报应?他苦笑一声。
柳洛取了解药喂过容郁,却不给忻禹服用,而是道:“娘娘继续。”原来中了两心知的人完全由蛊母操纵,忻禹虽中了飞花之毒,但在容郁的操纵下便可以行动无碍。
容郁果然听话,继续道:“让位与皇子琅轩……”
柳洛怒喝道:“娘娘什么意思?”
容郁一停,转脸来回道:“平郡王明鉴,皇上无子之时传位与平郡王尚且说得过去,如今皇上有亲身骨肉在,又怎吗会传位于一个外人,平郡王即便能叫容郁改口,又怎吗堵得上天下悠悠众口?”
勤王闻言笑道:“容娘娘果然好见识!”
柳洛道:“天下人是天下人,谕旨是谕旨,娘娘这时候若想反悔,怕是迟了些。这时候……皇上那边娘娘是没有退路了,勤王爷吗,娘娘莫看他说得好听,要是他得了诏书不杀皇上,我柳洛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的,至于其他王爷大臣,娘娘自问,又有谁敢和娘娘合作,还能答应娘娘的条件,保证皇上不死,保证小皇子不死?”
容郁面色如常,道:“容郁并没有后悔,容郁只是替平郡王着想——难道平郡王不觉得先做摄政王比较能教天下人信服吗?琅轩只是个才满月的孩子,平郡王要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平郡王何虑之有?”
柳洛心道:她说的话也不错,自己长期困守京城,要收服外官还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先任摄政王,将人心收拢,能用的用,不能用的就除去,假以时日,天下臣服,这时候再废掉琅轩称帝也不迟,反正容妃一介妇人,即便城府比一般女人深些,没有外戚权臣可以依靠,又能翻出什么波浪来,皇帝的废立都不过在自己一念之间罢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