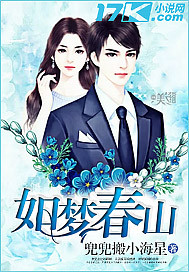女孩顿时惊醒,捂着先落地的肩膀,顿时哭哭啼啼。
少年无奈下了骆驼,扶起她,说:“别哭,马上就到了。”
她马上噤了声,看了眼他,委屈地埋下了头,只是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掉。
随着眼泪的滑落,女孩脸上被污迹遮住的皮肤,更多露出了原本的颜色。
少年不知道为何,忽然抬起手,擦着她的眼泪。
他的手,比她的要干净很多,抹了几下,她脸也没那么脏了。
看着眼前初现白皙的脸,少年忽然想起,以前班上的女同学来。
那些都是温室里千篇一律的花朵,而脏兮兮的小草虽然又瘦又小,他却知道她的模样,其实很好看。
不同于汉族的深刻轮廓,一对眼睛尤其漂亮,还有在戈壁里风吹日晒雨淋都未曾变黑过的白皙肌肤。
如果逃出了这地狱,如果回归到了正常的社会,这小丫头,该有多耀眼?
往日的磨难终究会过去,他们俩还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坚持下去。
少年精神更加振奋起来,第一次觉得自己带她逃出来,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事。
少年忽然兴起,指着自己,说:“知道我是谁吗?我,莫春山。春——山——”
他拉长了声音,想教会她自己名字的发音。
女孩眨着清凌凌的眼睛,试着重复他的发音:“……春……山……”
还是别扭又生硬。
她重复了几次,发音还是没有丝毫改善,忽然生气了一般,嘟起小嘴一言不发,似乎在懊恼自己的笨嘴拙舌。
少年笑了,也就不再勉强她。
天边有一丝光亮,月色西沉,眼见就要天亮。
喝了水,吃了点东西以后,他们再一次上路。
老骆驼似乎要撑不住了,少年不住地鼓励它:“加油,马上要到了。”
心底却没来由地泛起一丝不安。
还没来得及想那究竟是为什么,就听到女孩的欢呼:“那……那……”
少年回头:“哪里?”
女孩满脸兴奋,指着前方,目光灼灼。
漫无边际的戈壁似乎到这里中止了,少年隐隐约约看到前方一片房屋的轮廓,一瞬间的功夫,已经快要哭起来。
他知道,那是生的希望。
他兴奋地驱赶着骆驼向前,却不知道为何,短短的一段路,似乎特别漫长。
接着,他听到了背后驼铃的响动。
惊愕中一回头,他看到了背后的阴影,和映红半边天空的火光。
“快跑!”他兀自惊叫,蹬着脚蹬,想让骆驼跑快一些。
老骆驼却越跑越慢。半个晚上,它驮着两个人,横穿了一大片戈壁,体力已然消耗殆尽。
少年手脚并用,驱赶着骆驼,却无奈没有丝毫的效果。
他焦急不堪,背后忽然一空,刚才紧紧抱着他腰的女孩,已然坠落。
他惊愕地回头,看到女孩跌落在地,仰着头,朝他大喊:“跑!”
“小草!”莫春山大叫一声,从床上坐了起来。
房间里一片寂静,窗帘没有拉上。
窗外的苍穹清朗无云,却也不见星光,只余银盘似的圆月,悬在空中。
月光如水,洒在他身上,没有一丝温度。
莫春山苦笑,抬手抹过了眼角。
于是掌心里湿润冰凉,有他刚才在梦中滴下的一滴泪。
十五年了,她终于再度入梦来。
十五年前,小草到莫春山身边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正式的名字。她就是那帮子刀口舔血的恶徒,在大漠里随手捡来的小女婴。
小草也是命硬,刚出生就被遗弃在戈壁里,一天一夜竟然没有死亡——但,那时候她的顽强,却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运。
那帮子人随口叫她小草,取意便是沙漠里少数能生存下来的植物——灰扑扑不起眼的盐生草,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
可再顽强,也终究是草——命如草芥的草。
童年的时光懵懵懂懂也就过了,小孩子总是惹人爱的。
但到了十几岁的光景,一个女孩子在一群穷凶极恶的男人中,会遭到怎样的对待,可想而知。
刚到那片戈壁的时候,晚上,他时不时会听到她被侵犯时无助又凄切的哭声,甚至大白天的,也看过她被拖入一处杂草堆。事后,看到她满脸泪痕血迹,身上的衣物被撕得破破烂烂,抱着膝盖蜷缩在一处帐篷的阴影下,眸子黯淡。
莫春山早就知道,她根本就是那群人随意玩弄的布偶娃娃,她的命从来由不得自己。
也许哪一天就惨死,被弃尸荒野,白骨被黄沙淹埋,留不下一点痕迹。
就像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只是他那时候自顾无暇,也从没有自视甚高,把自己当成别人的救世主。
后来,那个人从那帮子人手里高价买下了小草,用来照顾莫春山——因为那时候他老是逃跑、寻死,必须得有人时时刻刻盯住他。
从此小草灰暗的生命里似乎出现了一线光亮,她的眸子一下子鲜活起来。
但,那人救她出了火坑,也发下了话——如果她看不好让莫春山死了或者跑了,她也得陪葬。
于是生存的本能让小草把莫春山看得比自己还重要,所以莫春山心灰意冷后一次次地寻死,又一次次地被她拦下来。
莫春山不肯吃饭,她没办法逼他吃,就守在他旁边,趁着他饿到意识模糊的时候,给他灌面糊米汤,一次次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他不止一次受伤生病发高烧,都是她衣不解带地照顾,通宵地给他擦拭身体降温。
遇到大旱,老天不下雨,水很珍贵没办法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时候,她也会把自己的留给他,自己去大漠上刨草根解渴。
甚至在那帮人对他拳脚相加的时候,她还给他挡下不少拳脚棍棒,在身上留下无数的伤痕。
他很恨她,讨厌她,但她看着他的时候,眸子比星星还闪亮,不管他怎么骂怎么打,也不会离去。
所以那晚上,他本可以一个人走的,却终于还是带上了她。
一是看在那些她为了保护他,她以自己羸弱身体扛下来的伤;二是,她当时那对带着泪、可怜又无助的眼睛。
终究还是他心肠不够冷硬。
他甚至觉得,在茫茫戈壁里,在一群比狼还凶狠的所谓同类中,她和他,是唯一的两个人。
于是他成了她唯一的信仰和依赖,他如果走了,她不仅仅是会被那群毫无人性的恶徒迁怒,被*甚至丢了性命的问题,她失去的,将是对生命最后的一点信任和渴望。
多少年过去了,他以为自己已经长大,已经足够强大到那帮人再无法控制他、伤害他,毁掉他看重的东西。
然而这一夜,这一个残破的梦,却让他意识到,脱去金钱带来的浮华外表,他的内里依旧软弱——一如十五年前的少年一样。
他自以为坚硬的躯壳,在“曾经”面前,再一次化作齑粉,他经历过的种种残忍和不堪,一一浮现在他面前。
当年他能带小草走的机会,其实根本就是那些人故意布下的陷阱。
甚至,从一开始就是故意放这样一个卑微可怜的女孩在他身边,然后让他亲眼看着她因为他的缘故被毁掉。
他看到,他自以为的善良给她带来灭顶之灾,她不仅没能开始新生活,死前还备受凌虐。
他看到,因为自己的弱小和无能,保护不了任何人,反而再一次害死一个命运悲惨却又无辜的女孩。
那一夜,他彻底被击溃,从而坠入深渊,再不敢反抗。
十年过去,他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和那段不堪的过去划清界限,甚至以为,他就是一个正正经经的商人,所谓的“过去”不过是阳光下的阴影而已,只要他跟紧太阳,所谓的曾经,就再无法伤害他半分。
然而有些浸入骨髓的东西,终究无法抹去。
莫春山闭上眼,梦里小草那对让他一时心软的眼睛,犹在眼前。
莫春山又想起了,何莞尔那对,让他折返三百公里的眼睛。
难怪他那时候放不下。
原来,那一日他所见到的眼睛,和十几年前让他无法狠心离开的那对眼睛,几乎一样。
难怪从第一次见到何莞尔那次,他就脱口而出小草两个字。
那不是他的错觉,而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何莞尔很美,从第一次看见她,他就知道——只不过,一开始他是无动于衷的,直到后来一次次的相遇、巧合。
他渐渐了解了她,也确认她不是小草——却又被她和小草相似的那么一点点特质吸引,一点点地让他生出别样的情绪,一点点地,让他无法将她轻易地放下。
但是,他却必须放下。
他不该一响贪欢,放任自己偏离了轨道。
也不该得意忘形,忘却了自己的曾经。
他有自己的宿命,生不见得是幸运,死也未见得是解脱——所以何必,把她也拖进这深不见底的深渊?
更何况,他不是仅仅是身在深渊而已。
他,就是深渊本身。
莫春山收紧了手心,然而掌中的泪迹并未干涸,混着手心逸出的冷汗,湿滑一片。
月光下,他摊开了手心,看着微微轻颤着的手掌,再次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