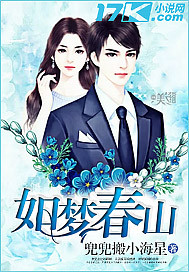何莞尔睁开眼,看着四周的一片沉黑,只觉得身体似乎被什么轻柔的力量包裹着,又能感受到止不住下沉的趋势。
眼前渐渐亮起,她终于看清楚身边泛起了一串串的气泡,随着水的压力变幻着大小与形态,还微微反着光。
视线里,又出现了头顶上荡漾着的淡绿涟漪,一圈圈地荡漾扩散,涟漪之上,是灰蓝的天。
又是这个梦——何莞尔想着,身体一动不动,等待着人脸、血红的眼睛出现。
似乎很久没有做过这个梦了,但她记得,等那一声小草以后,梦境便会结束。
等一等,似乎这个梦上一次又有了变化。
她看到过一道银白色的光影落入了水中,带动着水波荡漾,不知是鱼,还是刀。
这个渐进式的梦,每做一次就会多一点点的内容,而且她就像一个旁观者一般,静静地等待一帧帧不知道是存在于现实还是幻想里的图像出现,等到了某个时间点,一切结束,恍然一梦。
这一次,又会发生什么呢?
何莞尔静静地等着,可是,却什么都没有看到,就连头顶的涟漪也在渐渐地消失不见,四周的光线逐渐暗淡。
“又变了吗?”她微怔。
可是,身体的感觉并没有变。
她仍旧在被水包裹着,却止不住下沉的趋势,而随着视野越来越窄,耳朵里能听到的声音,却愈发地清晰。
有涟漪细碎的响动、气泡爆裂时轻轻的一声“啪”、甚至还有那银白色光影入水时候的闷响。
借着最后一丝的光亮,她看清楚了那银白色的东西的长短和形状,却依旧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视线渐渐黑暗,似乎梦境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可似乎还少了些什么。
何莞尔怔怔地想着,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她感受着涌进呼吸道水带来的窒息,以及满口的血腥味,一动不动。
她等了好一阵,终于等到了那一声悲悯绝望的呼声。
“小草!”
那声音沙哑异常,带着哭腔,但她却能从那囫囵一团的发音里,辨别出一丝丝独属于少年的稚嫩。
像是被这声喊叫击中脑海里的某个部位,她忽然想要挥动双臂开始挣扎。
然而脑子里下了这个指令,四肢却没能做出丝毫的反应。
她一动也不能动,只觉得四周的水紧紧地挤压着她的身体,将最后一丝的空气从她肺里挤了出去。
又感觉到水声渐渐消退,好多人在她耳边说话,却又一句都听不清。
何莞尔喊不出也动不了,呼吸越来越微弱。她用力地想要呼吸,依旧抵不过铺天盖地的窒息感,紧接着心口骤然一疼,黑暗与水波带来的压迫感,顿时烟消云散。
何莞尔坐起身来,手紧紧地按住心口,大口地喘着气,呆呆地看着窗外半亮不亮的光线,脑子里一直回闪着那个奇异的梦境。
算起来,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重复做同一个梦了,而且,在此之前,这个梦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了——上一次出现的时候,还是在顾念坠楼死亡后不久。
那一次,这个梦的重点是最末尾的银白色物体,从水面坠落进水里,一直往下面沉着,她当时就在推测,那是一条鱼,还是一把刀。
这一次,她看清楚了——不是鱼,但却也不是一把刀。
准确地说,很像是一把刀,可是刀柄和刀身的长度,严重失衡。普通的刀,都是刀柄短刀身长,然而这东西如果是“刀”的话,刀柄却比刀身长很多。而且那刀身似乎还在慢慢地缩短,画面非常诡异。
诡异归诡异,何莞尔却觉得这一次的梦的重点,并不在那“刀”身上,而是在最后的那一声喊叫。
又是那一声“小草”,又是似乎失去了全世界的悲伤,但是这一次,她听清楚了声音。
她能肯定哭喊着小草的人是个少年,声音里还带着变声期未完的那一丝孩童的稚嫩和尖细,非常独特的质感——她甚至能根据那声音推断出,少年的年龄在十五到十八岁之间。
但,这少年,又是谁呢?那一声小草,又代表什么呢?
何莞尔撑着头想得出声,浑然不觉时间的流逝,等察觉到隐隐约约靠近的脚步声,这才醒过神来。
她看着周遭陌生的装修和家具,好一阵子才想起自己是和莫春山在外赴宴,此时此刻应该在阜南省省会雒都两百公里以外的一处山里。
对了,她睡在别墅的主卧,犹记得睡前是关了窗户和第一层窗帘的,但因为嫌太闷所以并没有拉上完全遮光的那一层衬子。
而这时候厚实绵密的窗帘已经被外面的光线映成了柔和的香槟色,可想而知时间已是不早。
何莞尔下意识摸起手机看看,发觉屏幕上方显示着9:45的数字。
“啊,起晚了啊。”她喃喃念着,脑子里警铃大作,却死活想不起来自己漏掉了什么事。
下一秒,门口响起三声叩门声,以及莫春山冷冽的声音:“起来了吗?管家送早饭来了。”
何莞尔一个激灵,忙翻身下床,一分钟前铺天盖地的窒息和惊恐全被抛到脑后,再没空去管。
这一顿早饭何莞尔吃得很慌张。
被莫春山掐表看着时间吃饭,她五分钟的吃掉了两人份的生滚鱼片粥,不仅被烫到了,还噎得慌。
是的,她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喝粥也可以噎死人的。
十点半,何莞尔好容易把自己拾掇到能见人,临到出门的时候,她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穿上了所谓十厘米的超高跟。
毕竟是要跟着莫春山到山顶上去露露脸的,好歹不能失了“莫太太”的威风,鹤立鸡群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呵,想必仗着身高,来找她寒暄打发时间的太太们也会少很多。
山路蜿蜒,有了之前的经验,何莞尔自然而然地挽着莫春山的臂弯免得崴脚,顿时觉得自己的小算盘实在太精明——反正也没肌肤接触,这种让莫老板里子面子都有的事,还是可以做一做的。
也许老板大发慈悲,可以少嘲讽她少气她几回,也可以多活好几年的。
何莞尔偷偷地弯起了眼,无声地笑了笑,却不知道某人眼睛里得逞的小火苗,也正烧得旺旺。
不过一晚上时间,楼顶的别墅已是大宴宾客的派头。
郑洪洲一身改良的唐装,拄着拐杖精神奕奕地立在门前亲自迎宾,住在山上各栋别墅出来的贵客也纷纷露面,还有直升机起起落落,络绎不绝送来的客人。
“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和主人家打过招呼后,何莞尔陪着莫春山坐在二楼阳台上茶座,手里捧着杯普洱茶,哆哆嗦嗦看着楼下的宾客如云,还有心情调侃一番。
“别人冷了就加衣服,你冷了就说风凉话,”莫春山勾起嘴角一笑,“你就不怕郑洪洲听到了不送你下山?”
何莞尔眼睛一亮,看着莫春山:“大佬,你竟然看过红楼梦?”
她刚才说的那一句,是红楼梦里秦可卿说元春省亲时用的形容词。那一场奢靡的盛事以后,贾府逐渐走向败落,所以后来又有烈火烹油必不长久的说法。
“翻了一遍而已。”莫春山回答,嘴角淡淡勾起的弧度,让何莞尔认为他是在显摆加得意。
她还没来得及回怼他,却发现莫春山的视线落在了她的身后。
“莫总,莫太太,你们好。”
身后响起的声音让何莞尔皱起眉——特喵的,郑童敏,又是这个变态!
莫春山已经站起身,何莞尔也不好干坐着,只好站起身来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做着心理建设让自己表情不那么僵硬,这才转身回答:“二公子您好。”
却在说话之后才发现,郑童敏竟然不是一个人。
老爹的大寿,郑童敏自然穿得人模狗样,头发梳得溜光比莫春山还夸张,手里还挽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莫总,莫太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关骁,我女友,”郑童敏半笑着说,又拿右手食指比划了一阵,“骁勇善战的骁。”
说完,继续介绍:“这两位是莫春山莫总,和——”
他皱了皱眉,歪着头似乎在努力回想何莞尔的名字一般。
“叫莫太太就行了。”莫春山挑了挑眉,不动声色地回击。
“莫总,莫太太,你们好。”
关骁出声,听起来是在友好地打招呼,但脸上却没有一丝笑。
“莫总和莫太太是我爸的贵客,从庆州远道而来,也是我爸重要的生意伙伴。骁骁,以后我们两家人来往会很多,你和莫太太现在就可以多聊聊。”
“好。”关骁点着头,只回答了一个字。
何莞尔看着郑童敏夸张的表演,心里嘀嘀咕咕。
这色胚,不是说前几天才带了两个女人来这里胡搞瞎搞乱搞吗,怎么转眼就有了个看起来正正经经的女朋友?
就这匆匆几眼,她就觉得这位叫关骁的美女,似乎并不像能和郑童敏搞到一起的人。
眉眼修长、皮肤瓷白、头发乌黑,妆容打扮都清淡素净,言行举止也丝毫不见轻浮,反而很有几分文艺,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显而易见,郑童敏这一次莫名其妙的打招呼,似乎有些来显摆的意味。
等他带了关骁扬长而去,何莞尔撇了撇嘴,哼出一串评语:“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鲜花?”莫春山勾起嘴角,“狗尾巴花也是花,霸王花也是花,你说的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