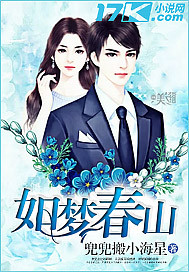李泽坤还是有几分在乎苏荷的,但这时候却不敢上前。
何莞尔刚才那一记提膝,已经打得他没了半条命,之后被她拿刀划破脸又吓得尿了裤子,哪里还敢上来?
而看她刚才把玩藏刀的动作,显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练成的。
这哪是什么桃花运,明明是朵吃人的霸王花,他怎么就眼睛瞎了撞上来?
郑治虽然毫发无损,可这时候也远远站着,对苏荷的求助无动于衷。
苏荷扭来扭去,只觉得脸上越来愈多的小伤口。
她害怕再这样下去脸上破相,也就不敢再动,只是嘴里还放着狠话:“我警告你,快放开我,要不然、要不然,我爸爸知道了,有你好看!”
何莞尔一阵好笑,干脆放开了她,拍了拍手心,好整以暇地问:“你爸爸?你爸爸是谁?”
苏荷忙退开几步,觉得自己离何莞尔够远,才觉得安全了些。
她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个性,又是个忍不了气的主,当下噼里啪啦开骂:“我爸可是市长,到时候,有你好看的!”
“这么说,他们今晚做的事,有你一份?”何莞尔又问。
“有我一份又怎么了?你不就是个出来卖的吗?我给你找生意,你该感谢我才是。”
苏荷以为何莞尔真被她所谓的家世吓到,又胆壮了几分。
别说现在没出事,就算是真有什么事,大不了拿钱摆平就是。
李泽坤和郑治两个,真是废物,连个女人都搞不定。
她越想越气,嘴里噼里啪啦骂起来,还夹杂着几句难懂的乡土俚语。
何莞尔安安静静听着,竟然一点都没动气,看起来甚至冷静异常。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无法无天,没有丝毫对法律和生命的尊重,仅仅是因为小到不能再小的口角,甚至仅仅是因为莫名其妙的嫉妒,竟然能唆使男人来强奸她?
也好在她有自保的能力,如果换成其他涉世未深的女孩子,又能不能逃脱这件事?
苏荷这种骄纵的性子,小了坑爹坑妈,大了坑社会坑国家,以为整个世界都围着她转。
“你爸的级别,可是县处级?副的?”何莞尔忽然发问。
苏荷愣了愣:“怎么?”
“果然。”何莞尔冷冷一笑。
李泽坤表情变了:“你爸不是金泽省的副市长吗?”
“你难道不懂有一种行政区划叫县级市?”
何莞尔手挽在胸前,似笑非笑。
就从的苏荷的教养来看,家里就不可能有什么大人物的长辈。
她好歹在警察大院里长大,放学时候经常拉着冯旭和含章,看院子里一堆退休的局长副局长,为了下象棋吵成爆眼子老头,其中还不乏厅局级干部。
上学那阵子,他们院的孩子还和隔壁政府家属大院干过架,被她揍过的庆州市领导的儿子孙子都不止一个,打不赢的都觉得“辱没了祖宗颜面”,哪里敢回家告状?
倒是苏荷这底气,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家里那位是国家领导人呢。
所谓的半罐水响叮当真是亘古不灭的真理,往往背景越强大的人越是低调,不需要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家世拉出来彰显存在感,即使骨子里刻着高高在上的倨傲,也习惯用谦和的外表来掩饰。
反而越是小地方的人,越对所谓人情关系迷信,也越是有一种迷之自信,就像苏荷这样的,以为有一个在县级市横着走的副处级老爹,哪怕捅出天大的篓子也有人给她兜底。
看来不给她一点教训,今天还真解不了气。
于是,何莞尔朝前走了一步。
苏荷吓了一大跳,指着何莞尔:“你敢动我一根指头,我就告你抢劫!”
说着,她急中生智,竟然将手机、钱包、包括身上的项链和首饰,扔了一地。
何莞尔笑了笑:“平时没见你多聪明,这时候倒是机灵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跨上前,反手就是一耳光。
还顺便把苏荷的扔在地上的耳环,狠狠地踩进泥里。
她扇耳光的动作实在太快,快到在场的人甚至觉得空气中留下了她的残影。
苏荷耳朵嗡嗡直叫,好一阵子脸上才有火辣辣的痛感,不敢置信的捂着脸:“你,你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何莞尔淡定地卷了卷袖子,冷笑道,“萍水相逢,我把爪子收起来而已,你们还真以为我好欺负?”
说着,又逼近两步:“两个,再加你一个,也不算什么。说到毁尸灭迹,我可是专家。”
苏荷脸蛋上已经浮现出清晰的指印,眼看着就要红肿起来,火辣辣地疼:“你!你敢……”
李泽坤倒是比刚才冷静了一些,他怕苏荷再惹出来什么事,大着胆子拉了她一把,让她离何莞尔远点。
他刚才挨了重重的一击,好半天才能爬起来,再看何莞尔手里把玩藏刀玩得如此纯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对方是霸王花就算了,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说何莞尔有胆子杀人,他也是信的。
再说了,苏荷家里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他还得下来核实一下,这几年为了讨她换新,在她身上花的钱少说也有几万,可别收不回来本。
于是拉起苏荷绕着圈走,一开始小心翼翼害怕惹恼何莞尔,之后越走越快,甚至跑了起来。
马路这边,只剩下郑治还立在原地,满脸惨白、呆若木鸡。
“听说你们认识三年?”何莞尔冷笑一声,转头看着郑治,“看到了吗?这就是你所谓的朋友。李泽坤不会和你共进退的,他只是想羞辱我,讨好苏荷。如果今晚的事按照你们的预想进行,一旦事发李泽坤必定推你出来当主犯,苏荷也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我……对不起……”郑治早已明白过来,嗓子有些干哑,但终究还是知道道歉。
何莞尔气消了些,认真看他:“我看你还有救,最好少和这对人渣厮混,对你没好处的。我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将刚才捡起来的藏刀收了起来,转身回了房间。
几分钟后,她听到了郑治离开的动静。
四周再次安静如初,惟有远处山脉上卡车经过的轰鸣声。
何莞尔靠在木门上,站立了片刻,之后稳了稳心绪,将桌子和椅子拉到墙边,抵上了门。
再一次检查了窗户没有被捅开的可能,她心里总算踏实了些,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
她摸了摸额头,果然,一头的冷汗。
明明那心怀不轨的人已经被她吓退,明明她也知道他们再没胆子来骚扰她,可是,她心里没来由地恐惧,指尖再一次凉透。
她不知道为什么但凡涉及到那两个字的犯罪,就会让她产生没来由的恐惧,如跗骨之蛆一般,平时不显山露水,一旦被什么激发,就会占据她的整个思绪,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比如,五年前的某一天,她一边颤抖着,一边把那人打得血肉模糊。
闭上眼,似乎还能看到那血肉淋漓的画面。
何莞尔捡起刚才被她扔掉的暖手器。
暖手器还有些微的温度,她将它抱在怀里,感受着那温度的渐渐扩散,渐渐地,也止住了颤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