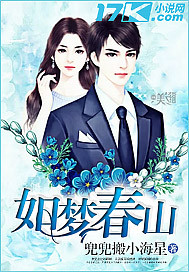阮梦琪看到莫春山,倒是有几分高兴的,兴冲冲过来喊了声表哥,接着视线朝他身后一瞟,一皱眉:“孟千阳呢?他怎么没来?”
莫春山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视线朝着何莞尔的方向,说:“梦琪,你见过的,何莞尔,我女朋友。”
阮梦琪没见到孟千阳,噘着嘴瞅了何莞尔一眼,冷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哟,我刚才就在猜是谁呢,结果还真是你?怎么,被我表哥临时抓来顶替?我表哥给你多少钱让你演一场戏。”
何莞尔淡淡一笑,并没有管她,但心里也颤了颤——阮梦琪竟然一下子就说中了,也不知道是她随便瞎猜的,还是她这假扮地真是不靠谱,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轻易看出来。
莫春山眉头微拧,声音一瞬间冷起来:“这是你准表嫂,不许没有礼貌。”
阮世东也来打圆场,微胖的面颊上带着歉意:“小何,我家梦琪小孩子脾气,你别往心里去。春山啊,小何初来乍到的,要不让你带她参观参观老宅,免得一会儿走迷了路。”
莫春山听了这句话,认真地看着阮世东:“姨夫,莞尔以后是这里的女主人,怎说得上是参观?应该是熟悉才对。”
何莞尔眼睛一亮,马上想起阮世东鸠占鹊巢的十来年的事,心情有些激动。
哇哦,不到五分钟就开始明枪暗箭了,想必今晚上会很精彩。
她本来对趟浑水这回事多少有些抗拒,但毕竟与人斗其乐无穷,更何况莫春山这种战斗力爆棚的损人和她一个阵线,能一致对外一起撕人,她一时间竟有些摩拳擦掌起来。
阮世东则是面色一变,不过转瞬便藏好了眼底的一丝阴狠。
他脸上笑呵呵的一团,附和着莫春山:“是是是,那就带小何去熟悉一下、熟悉一下。”
阮梦琪万万没想到自己随口的一句话能引出剑拔弩张的气氛,低垂着头害怕闯祸,不敢再多说一句。至于莫书毅一家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好当和事佬,也不会傻乎乎去惹金主不高兴。
莫春山巡视一圈,似乎很满意在场所有人的反应。
他后退一步走到何莞尔身边,顺势拖着她的手,说:“我带你到处看一下,你熟悉以后规划一下房间怎么用合适,看不顺眼的地方该敲的敲,该打的打,怎么高兴怎么来,可好?”
这一次,连何莞尔都能感受到他话里话外的森森寒意,掌心上却传来他手掌温热干燥的触感。
她惊了一惊,下意识想要挣脱,却看到他略带警告的眼神,忙收敛心神,答了一个字:“好。”
众目睽睽之下,何莞尔任由莫春山拖着手,从楼梯逶迤而上。
到了二楼转角,没人看见的地方,她急匆匆地想要把手从他掌心抽出来,挣了一挣,结果没挣脱。
莫春山握得更紧。
“你弄痛我的手了,”她小声地说,“现在也没人看见。”
“忍一忍,”莫春山没有丝毫要放开的意思,“走廊上是有监控的,你不要在任何地方露出马脚,懂吗?”
何莞尔抿了抿唇,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点头,当然没注意到她转过头的瞬间,莫春山的嘴角勾了勾。
这栋楼并没有大到离奇,不过二楼、三楼加起来,依旧有七八个房间,都收拾得整齐精致。
从推开第一个房间的房门开始,莫春山便放开了她的手。何莞尔一路看下来,几乎看花了眼,但赞叹之余,也能感觉到一丝的异样。
这地方是很典雅华贵,但每一个房间都像展厅般,家具和软装完美精致的搭配,却没有一丝丝有人居住过的痕迹,甚至比不放东西的空房子,显得更加地冷清。
“这里现在没人吗?”
到了三楼,何莞尔从最后一个房间里推出来,忐忑了一阵,还是问了个问题。
她听到莫春山微微的一声叹息,又看到他走到了走廊尽头的窗户边,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外。
何莞尔在他身后,顺着他视线的方向望出去,看到窗外楼下的后院里,有个旧旧的秋千。
夜色里,秋千微微泛着黄,不过连接座椅的金属部分似乎有什么特殊的涂层,亮铮铮的,不见一丝锈迹。
莫春山凝眸看着秋千,缓缓说道:“怎么会没人?这里每天都有三四个人来整理、收拾,每年都要检修一次楼体、管道,改建也有十次八次了。”
“可这里……”何莞尔欲言又止——她想说的是,这房子没有一丝丝的人气,就连楼下那帮服务的人,也像是负责派对、宴会的专业公司的专业服务人员的感觉。
这里一点都不像家,更像个对外出租的别墅酒店。
“其实你也没说错,”莫春山突然回答,“除了拿回房子的第一晚我住在这里以外,这些年我从来没在这里过夜。”
“为什么?”何莞尔十分不解,“你不是在这里长大的吗?不是有你最珍贵的回忆吗?”
“回忆?”他嗤笑了一声,“毫无用处的东西,我宁愿没有。”
何莞尔如鲠在喉——她不知道多渴望又珍惜的东西,却被莫春山视若敝履。
就像她对能住在父亲的旧居里感激涕零,莫春山却对这栋这样珍贵的小楼,抱着这样消极又疏远的态度。
莫春山又问她:“刚才每推开一扇门,你都在四下打量,是在找什么东西吗?”
何莞尔一怔,没有马上回答——她确实在找她以为这老房子里必然存在的一些东西,然而并没有找到。
他微微一侧眸,轻笑着说:“我猜,你是在找我父母的灵位,或者是照片。”
何莞尔没想到这也能被他猜中,只好点了点头,老实地承认。
“很遗憾让你失望了,这里没有设什么灵位牌坊,他们的照片,除了墓碑上模模糊糊早就看不清楚五官的两张,我都没有留。”
“这又是为什么?伤害你的,并不是他们!”何莞尔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回答,“我只会恨我爸爸留下的照片不够多,哪有你这样故意毁了的?”
“很简单,因为我懦弱,”莫春山自嘲地一笑,“我甚至懦弱到连老家具都不敢留,就怕自己一看到就想起以前,想起自己本该做另一个人。”
说着,他回眸,看着何莞尔:“你要知道,这世间比得不到的更痛苦的是,‘我本可以’四个字。”
他说得平静轻缓,语气柔和,可何莞尔能感觉到他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悲伤。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劝慰,只好默默地听着。
莫春山似乎也不需要她回答,自顾自地指着楼下:“那个秋千是唯一留下来的东西,当年我爸用了特殊的材料和特殊的涂料做成,他说这秋千能屹立到我的孩子都长大,所以我要看看,是它先倒下爽约,还是我先灰飞烟灭。”
他一如既往平淡的语气,何莞尔听在耳里,却总有些隐隐的不安。
似乎有些瘆人的冷意,在他不经意间就会从他眸子深处溢出来一般,让人颤上一颤。而他现在给她的感觉,和数个月前那个或傲娇、或毒舌、或冷漠的男人,有着天壤之别。
到底是哪里变了呢?
何莞尔不禁有些出神,莫春山微侧着头,嘴角一抹莫测的笑:“怎么了?你在害怕?”
“没有,”何莞尔回过神,忙摇头,“只是觉得以你的个性,不会随随便便把这些话说给别人听的。”
“你说得对,”他转过身,定定地看着她,“只是因为,你不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