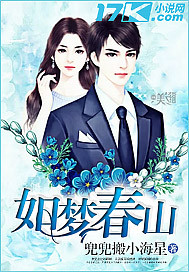一低头,何莞尔看到聂芸站在她对面的咖啡机旁,捻起一包怡口糖,撕开包装后倒入咖啡杯里,慢条斯理地搅拌。
“看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怎么,遇到了难题?听说你跟进的那篇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突发增高的系列报道进展不大顺利,有没有想过换一个难度小点的话题?”
聂芸满脸的春风得意,端起咖啡抿了口。
“多谢挂心了,小小的麻烦而已。”何莞尔并不想和聂芸多说。
她微微一颔首就打算出门,然而但聂芸显然不会轻易放过她。
她出门前,聂芸喊住了她。
“何莞尔,我警告你,离我的采访对象远一些,他不会理睬你的,你也别白费心思了。”
何莞尔愣了几秒。
采访对象,她说的是莫春山吗?
问题是现在她一想起这个名字就异常地烦躁,怎么可能故意去接近?
“放心,我一点都不感兴趣的,你别太过于敏感了。”何莞尔终于回应她。
“敏感”这两个字有些刺激到聂芸。
她声音不自觉地扬高:“是吗?那你怎么解释你出现在桐城路桥这件事?”
何莞尔回眸看她,再一次强调:“你的事我没兴趣管也没心力管,我的事,你也管不着。我言尽于此,与其在这里找我出莫春山不大搭理你的气,不如好好思考一下你的采访方案怎么引起他的兴趣。”
“你!”聂芸手里的咖啡杯重重垛在台面,有几滴液体溅在她手上,烫得她马上一缩手,人倒冷静了几分。
她忍下了气,声音比之前平静很多:“何莞尔,你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我会一点点讨回来的,你等着瞧好了。”
何莞尔再不想搭理她,径直出门,回了办公室。
小雷愁眉苦脸地凑上来,声音哭兮兮的:“老大,数据分析出来和你之前的判断相反。你看怎么调整?”
何莞尔愣了愣,从她手里接过了分析结果,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她的状态糟糕透了,似乎有很多人在她耳边说话,却一句都听不清楚,脑袋里有太多的念头和想法,却一个也抓不住。
不要说改稿这种烧脑子的事,她甚至已经有点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在现实,还是在梦境里。
如果还在做梦,是不是从大厦顶端纵身一跳,会不会就从现在这样糟糕的状况中,醒过来?
好在这样极端的想法只出现了一秒钟,就被她压了下去。
何莞尔当机立断,将那张纸塞进包里,回头对小雷说:“我出去一趟,找人分析分析,有了思路再和你说怎么改稿子。”
小雷眼睛一亮:“是要找白老师吗?很好很好,他目光如炬,肯定一眼就能看出问题在哪里。”
何莞尔出了报社,自然没有去找白廷海。
她的状况很不对劲,当前已经没有心力去思考工作的事。
当务之急是,找到能让自己睡着的办法,好好睡上一觉。
既然柯知方找不到,那她只有自救了。
一个小时候,何莞尔从药店出来,满脸的失望。
她跑了十多家药店,没有一家药店敢卖给她安眠药——即使她表示只要几颗,且愿意出高价,也没有人敢冒这个险。
这是处方药,没有医生开的单子,她根本就买不到——谁知道你是真失眠了,还是要自杀?
倒是有药师建议她去医院看看,何莞尔当时满口答应,可在最近的医院门口徘徊了一阵,她还是回了家。
她这样的情况去医院的,应该挂哪一个科呢?精神科吗?
即使处于崩溃的边缘,她也还没有准备好,向柯知方以外的医生,倾诉自己的问题所在。
她害怕再一次把伤口展示给被人看,害怕被人当成疯子一样,更害怕陌生人审视的目光。
到家已是中午时分。
何莞尔没有感觉到饿,却还是觉得应该吃点东西了。
家里什么都没有,只剩下泡面。
她烧了水泡好方便面,刚搅了一下塑料叉子就断成了两截,只好扔掉塑料叉找来了筷子。
吃到一半口渴,却发现饮水桶里都空了。好容易从冰箱里翻出最后一罐零度可乐,一拉拉环,那拉环却从接口处断掉了。
真是诸事不顺。
何莞尔分外地心烦意乱,耳鸣也越来越严重,啸音已经快盖过远处内环路上打桩机工作的轰鸣声。
她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将茶几上的东西扫落在地。
地上滚着打翻的泡面碗,带点油星的汤漫了半屋子,可乐罐倒在桌角,汽水从从拉环断掉处的小口子汩汩地漫出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层的气泡。
何莞尔喘着气,不知为何脑海中忽然又翻涌出那个梦的内容。
淡绿的涟漪、血红的眼睛、一声声的呼唤。
接着是绵密的窒息感到来,胸口似乎被压上了大石头,她快要失去呼吸的能力。
惊慌失措中,她看到阳台推拉门的玻璃上,映着自己凌乱的影子。
不是那么清晰,但她也能分辨出自己黯淡的面色、发白的嘴唇、眼角的泪痕。
憔悴到她快要认不出自己。
难道真的要朝着窗外纵身一跳,才能结束这噩梦一般的体验?
何莞尔鬼使神差地朝着阳台走去,手刚触到推拉门,身后响起一阵手机铃声。
超级玛丽背景音乐的钢琴版,是柯知方的专用铃声。
何莞尔愣了愣,马上清醒过来,只觉得那铃声成了这世界上最悦耳的音乐一般。
她转身狂奔,从沙发上一堆杂物里找到了自己的手机,忙不迭接起来。
“喂?”听筒了里传来柯知方温润的嗓音。
区区一个字,就让她持续两天一夜的耳鸣停止,有了暂时的平静。
柯知方静静地等了几秒后,说:“我回来了。”
何莞尔想要说话,却发现声音干哑到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我刚下飞机,看到你打了十几个电话,怎么了,有急事?”
没有听到何莞尔的回答,柯知方继续说。
她张了张嘴,终于艰难地说出:“我做梦了。”
“你做梦了?”电话里,柯知方重复着她话的内容,声音有几分不真实的遥远。
“是,”何莞尔几乎是哽咽着说了一个字,之后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好半晌,她听到自己的声音:“我想见你。”
无比地委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