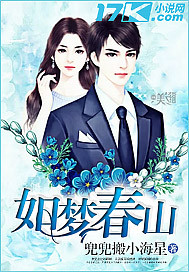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莫春山这位大佬支使个餐厅大厨而已,自然不在话下。
没过二十分钟,和晚上一模一样的安多小羊排就送到房间里,摆在露台上。
只不过比晚上那份少一些,大概一半的份量。
“吃吧,我不看。”他恢复了一贯冷漠平淡的语气,说完,起身回了房间。
何莞尔道了声谢,也顾不得什么丢脸不丢脸的事,没多久小羊排上的肉都被剔得干干净净。
刚吃完擦干净手,眼前出现装了浅浅一点葡萄酒的杯子。
“这一瓶最后一点,不给你怕你心里诅咒万恶的资本家,喝完就滚上去睡觉。”
莫春山说着,把酒杯给了她。
小半杯酒下肚,何莞尔脸上、心头微微发热。
嗯,吃饱喝足的一瞬间,世界又美好了起来,清冷的空气都是甜的,天空中的闪闪繁星,更是美丽异常。
忽然间,有什么东西飞速划破天空,拖着长长的半透明的尾巴,照亮了半边天宇。
何莞尔眨了眨眼,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她刚才,看到了什么?
“刚才是流星吗?还是我吃得太饱产生了幻觉?”她不知不觉问出声,呆呆地立在原地。
却没发现莫春山被她的话,逗得嘴角上扬,忍不住地笑。
好一阵子也没听到莫春山的回答,然而下一秒,天边再次出现几颗拖着长长尾巴的光影。
她下意识地转过头,发觉莫春山也正看着她:“你说呢?”
“果然!”她瞪大眼睛,“刚才真是流星飞过去?”
莫春山淡定地点了点头,回答:“猎户座流星雨,要不然,你以为我在吹着冷风等什么?”
“原来你不是为了……”何莞尔说了一半就捂住嘴。
“你以为我是为了开解你守几小时?别傻了,我也就是高锰酸钾而已,你迟早会想通,我只不过加速反应而已,何必多此一举?”
何莞尔:“……”
好吧,她不该自作多情的,更不该一不小心说出心里话,又被他笑话。
言语间,天空又是几道流星划过。
“天啊!好美!”何莞尔忍不住站起身,手舞足蹈,“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流星。”
“说得你以前好像见过流星似的……”
身后,又是谁讨人嫌的声音。
何莞尔气结,回头恶狠狠地说:“聪明人都是看破不说破。”
莫春山扬眉:“我不聪明,比不得你,自作聪明。”
何莞尔再忍不下去了,凶相毕露:“老实说,你是不是不想活过今晚?”
一边说,一边挥了挥拳头。
“我劝你做点应该做的事,”莫春山自然不会被她吓到,淡定了抿了口酒,说,“比如看到流星双手合十许愿什么的,比你虚张声势强。”
他话音刚落,又是数十条闪亮的尾巴从夜空中掠过,几秒钟就消失不见。
何莞尔被流星雨的壮观景象惊呆了,再也顾不得和莫春山说话,只睁大眼睛看着墨黑的天空,期待下一波的流星出现。
然而等了好一阵子,天空也平静如初。
莫春山抬腕看了眼时间,对她说:“没了,你没来得及许愿。”
何莞尔呆立良久,才感叹道:“如果对着流星许个愿就能梦想成真,那这世上哪里还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
莫春山对在她眼里看到如此沧桑的神色,有些意外,转瞬想起她早逝的父亲,顿时了然。
好像他翻过一遍的何莞尔父亲的资料里,提到过他其实出生在玖须海。
难怪,她哪怕一个人只身上路,也要回去看一看。
更难怪,在那天的星空下,她会问出那样的问题。
他一时话多起来:“我记得几天前,你在玖须海问我,说人死了会不会变成星星。这样的蠢问题想必你自己是知道答案的。”
何莞尔恨不得捂脸,很有些赧然:“能不能不要提前几天的事了?”
这些天她做得蠢事还少吗?
自从那一晚开始,发生了太多她想象不到的事,丢钱包、喝醉酒、跳锅庄、当苦力,还有其他很多很多。
她简直丢够了脸,以至于现在面对莫春山,已经有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了。
莫春山却不知怎么,有了倾诉的欲望一般:“人死后不会变成星星,而是会,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
他抬手端起酒杯,摇晃着杯中的液体:“假设有那么一个让我牵挂的人故去,从这世界上消失不见,我再没可能看到她的笑,听到她的声音。但我手里的这杯酒,可能是她的血和泪蒸发,幻化作密云,又下成一场雨。雨水滴落在地面上,被植物吸收,被果实包裹,最后酝酿、发酵,化作这杯美酒,和我重逢。”
说着,他慢慢仰头,看着银河的方向:“只要心里记得,他们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所以生或者死,在或者不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
他这番话,不像是说给何莞尔听的,似乎更像是在说给他自己听。
说服他自己,小草还在的,从没有离开过。
她已经化作这世界的一部分,一直在看着他,守着他——看她当年赌上一切信任的春山哥哥,如今成了什么模样?
还得守着他,为了逝者的心愿,再难过再艰苦,也要走下去。
他懂她,所以他才会执念于某一年的红酒——因为,那是她出生的年份,而红酒浓烈的色泽,也与她留给他最后的印象,那样相似。
十五年过去,他可以说一句他没有负了她。
只是,支持他继续走下去的信念,却越来越薄弱。
一旦崩塌,他又该怎么办?
莫春山闭上眼,忍住脑海深处一阵阵的刺痛和视线里渐渐浮起的一片血红,等着这一刻的过去。
何莞尔却因为他的话愣了好久,神情恍恍惚惚,似乎陷了进去。
好一阵子,她转过头,认真地看着莫春山:“可是,如果故去的人,是因为我的缘故故去的呢?”
莫春山睁开眼,视线落在她身上。
她身上的衣物分成了四层。
腿上裹着黑不溜秋的长裤,浴袍刚好在齐膝的长度,再上面是紫红炸眼的冲锋衣,他丢给她的毛毯,裹在上身齐腰的位置,说不出的滑稽。
毫无美感可言的打扮,却掩盖不住的天生丽质。
肤色如玉,眸子里蕴着几分朦胧的水色,唇瓣粉红柔嫩,如同最娇艳芬芳的玫瑰花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