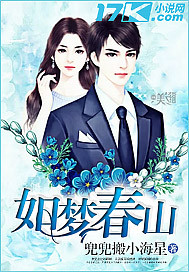莫春山回身,倚在阳台的栏杆上,视线向下:“你别老去刺书毅,他对顾小姐也算有情。再说,他好歹是我一片肝的容器,你把他气死了可不太好。”
何莞尔一开始是严阵以待的表情,等听到是莫书毅的事,忍不住狠狠地翻了一个白眼,气不打一处来:“他又是什么好人了?装得对念念款款深情,结果做了不知道多少伤害念念的事。反正我要是真爱一个人,绝对不会和另外的人结婚的。”
“是吗?”莫春山似笑非笑,“那你为什么和我结婚?”
他虽没说得太直白,可何莞尔知道他下一句必定是个反问句——“你真爱我?”
“莫春山!”她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警告,“你再惹我,我保证今晚这里再多的黑西装也救不了你。”
莫春山看着她的模样,勾起嘴角。
这一番你来我往,何莞尔已是面色薄红,漆黑的眼瞳里也有薄薄的怒意。
莫春山知道再逗下去指不定她会发火了,于是顾左而言他:“关于莫书毅的事,我觉得有必要和你解释一下。其实他之前的婚约,全是为了救莫春晖。”
有了八卦听,何莞尔倏然间忘了她和莫春山之间的新仇旧恨,不由自主竖起耳朵,想要认真听。
莫春山也不再废话了,三言两语告诉了何莞尔前因后果,惊得何莞尔连连惊叹,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狗血的剧情?
莫书毅这一次结婚,正如莫春山所言,其实是为了救莫春晖。
才嘉已经告诉过何莞尔,莫春晖常年酗酒,几年下来肝癌中晚期,能救他的唯一方法就是移植肝。
又一个需要移植肝的,他儿子莫书毅本来就是被移植的受体,自然不可能作为供体,戴招娣配型也不成功。
至于救过莫书毅一次的莫春山,已经割过一次肝,自然也不可能再给莫春晖供肝。又因为非亲属之间不能进行器官移植,所以眼看着莫春晖就是死路一条。
莫书毅缺点一大堆,但是惟有孝顺这一点,让何莞尔都自愧弗如。
恰巧,和莫书毅青梅竹马长大却一直不得莫书毅喜欢的女人,私下做了配型竟然和莫春晖相同,而那个女人开出的条件是要和莫书毅结婚,
也只有她和莫春晖有了亲属关系,才能名正言顺地移植器官。
莫书毅已然认命,结果结了婚手术做完没多久,却因为顾念的事,要和那女人闹离婚。
只是手术已经做完,肝脏已经移植了,那女人再不甘心再不依不饶,却也不能把莫春晖剖了取出自己的肝。
无意中又“骗肝”成功,莫书毅且不能像当年莫春晖那样无耻。他赔了那女人好大一笔钱,想要平息这件事。那女人也算有几分精明,知道留不住人也留不住心,那干脆留住钱也是好的。
当年莫春山一片肝换两亿,到了莫书毅这一次,是一栋房子换来的。
所以莫书毅,除去了莫春晖的医药费,他们只怕连住的地方都要卖了。”
“他现在这么惨?”何莞尔想到自己刚才那样怼莫书毅,竟然有些愧疚起来。
“也不算惨,至少不会流落到街头乞讨。我反而比较担心你。”莫春山微笑。
何莞尔愣了愣:“担心我?”
“我是怕你和莫书毅再起什么冲突,毕竟莫书毅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不会像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迁就你,这样地宽容。”
“宽容?”何莞尔瞪大眼睛,活见鬼的表情,“你是不是搞错了宽容的含义?”
莫春山抿嘴:“宽容是需要对比的,和你的记仇比起来,我当然宽容。”
何莞尔又忍不住摩拳擦掌起来:“我哪里记仇了?我要是记仇,也不会帮你了。”
“你是在帮我吗?你明明是怕连累才嘉对吧?”莫春山一语中的,身体斜倚在栏杆上,“今天早上还在说我是死人,刚才吃饭正眼都不给一个,我费尽心思帮你赢了一场牌,你却连笑都不笑一个的。这还不叫记仇吗?还是你真讨厌我了?”
他缓缓说着,笑意漫过眼眸,声音都温柔地有些不那么真切。
何莞尔本想硬着心肠说是,但终究没能说出违心的话。
她换了委婉点的语气:“你讲点道理好不好?你得罪我了我不原谅你就叫记仇?我的宽容是留给你这种自大傲娇又毒舌的人吗?那我家人朋友又分得到什么?”
“遗产啊。”莫春山不急不缓地吐出一个词。
“你!”何莞尔差点暴走。
好吧,她算是发现了,莫春山真的很懂得她的底线在哪里,还总能准确地在踩线和不踩线之间游走,惹她都惹得恰到好处。
比如此时,知道她顾忌有人在旁边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能毫不忌讳地讽刺她。
等她真生气了,这人又马上敏锐地转变态度,殷勤小意地道歉、逗她开心、说些冷得不行的笑话,要么就说些她真正感兴趣的东西,然后让她有气也发不出来。
该怎么办?怎么斗得过这只年轻的老狐狸啊?多来几次真会把自己给憋死的。
好半晌,她沮丧地捂着脸:“好吧,你是甲方粑粑,你说了算。”
“我可不是甲方,”莫春山气定神闲,“万年不变的承建方,流水的营盘铁打的乙方,经验丰富的受气包,谁都不敢得罪,包括你在内。”
何莞尔鼓着腮帮,气呼呼:“你现在就在得罪我好吗?”
他淡定自若地微笑:“你现在的表情就很好,旁人看来会觉得你是在撒娇。”
“撒娇”二字,彻底把何莞尔震住了。
她呆若木鸡之际,莫春山微弯着腰,伏在她耳边轻声说:“闹一闹别扭可以,总不能一直闹别扭,所以你先要改掉不管我说什么话你都想怼的习惯,先学着习惯我。然后,才能说去骗其他人。”
他靠得很近,何莞尔再一次闻到了他身上和大衣上一模一样的木质香。
她微微喘着气,强忍着心跳失序的慌乱,转过头认真地看着他:“好的,我明白了。今天工作状态不好,我会调整自己,保证明天正常发挥。”
说完后,便将大衣还给了他,接着沿着阳台的旋梯,一步步下到花园里去。
今晚的莫春山,让她感觉到了莫名的危险气息,她已经开始怀疑早上的决定是错是对,更加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分辨他的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所以她要靠什么撑过说好的三个月时间,陪他演出一场盛大的婚礼,还能迅速地从角色里剥离出去?
她做得到吗?
何莞尔前所未有的无助与迷茫,而此时的莫春山看着她的背影,渐渐隐去脸上的笑意,眸色如连绵的夜色,一片浓烈又炙热的黑。
人都走了,何莞尔和莫春山留在老公馆也没了意义。
孟千阳开了车来接人,车回到临江名门的时间,刚刚过了十点。
何莞尔本想换了衣服就回家,莫春山却不让她走。
他的理由冠冕堂皇,都要结婚的关系了,哪里能让她一个人住回内环路的老房子里?万一被他姨妈或者其他多嘴多舌的人知道了,他们之间假结婚的西洋镜,就会被戳穿。
另外他还建议何莞尔加一加班,多了解一些莫家相关事宜,习惯接下来的生活以方便她更快进入角色。
何莞尔听到他无理的要求,晚上让她心慌意乱的片段顿时抛到九霄云外去,只记得发火了。
客厅里,她冲着莫春山大叫:“我又没卖给你,凭什么不许我回家?”
声音极大,吓得刚好路过的小草,差点跳起来。
莫春山勾起嘴角:“八小时工作制,你算算,够了吗?”
何莞尔脑子里一默,马上理直气壮:“够了的!从中午十二点到现在,已经十个小时!”
“你换衣服梳妆打扮就用了六个小时。”莫春山好整以暇地说,“你们山城报业能允许你在卫生间停留一上午不出来工作?”
何莞尔气急:“不是陪你去那什么劳什子家宴,我用得着换衣服吗?我穿成叫花子也没人管我!”
“工作服不也归你所有了吗?我又不需要女装,我家也没人有那么大个子能穿你的码子。”莫春山微笑着回答。
何莞尔刚想回怼本姑奶奶穿2号的哪里个子大了,脑子里却忽然冒出个莫名其妙念头——莫春山要是变成女装大佬,会怎么样?
她想的得出神,不知不觉笑出了声,一抬头却看到莫春山歪着头看她。
“你在想什么?”他微眯着眼。
何莞尔忙摆手:“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想你穿女装的样子。”
莫春山脸明显得黑了黑,声音一顿:“总之,你订做工作服的时间,不能算在有效工作时间以内。”
何莞尔刚才一时说漏了嘴还在心虚莫春山算账,无心争辩工作时间的问题,无奈地想——好吧,如果这样的话,那还真的没有够的。
另外,看在衣服的份上——算了,还是她占便宜。
不过她想了想,又挑衅般开口:“那我在这里睡觉,算不算加班的?“
莫春山一扬眉:“所谓的有效工作时间包括基本工作时间、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以及辅助工作时间,并不包括必要的休息时间,除非你不睡觉。”
何莞尔气结,一口银牙几乎咬碎——他回答得这样滴水不漏,显然是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的。
万恶的资本家,想方设法剥削她的剩余价值,太无良了。
回到下午她试衣服的房间,发觉所有用品都已经准备好了,连护肤品都是全新的一套,想必是才嘉在他们离开公寓去老公馆的时候准备的。
再看到床上摆放的几套睡衣,她一时移不开眼。
其中一套某大牌的真丝睡裙,面料上乘,泛着晶莹又丝滑的光泽,她摸了又摸,却还是恋恋不舍地放下,最后选了其中最朴实无华的一套棉质的换上。
即使是最低调的一套,也舒适地令人发指,就是设计师太为厂家着想布料用得少,前胸后背稍微露得多了一点。
何莞尔也没选择的余地,只好将就穿上,然后认认真真地卸妆、洗脸、刷牙。
十几分钟后,她躺在被窝里,感受着被高档床品包裹起来的温暖和柔软,困意渐渐酝酿出来。
好舒服啊——她感叹着,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起那一夜楼上漏水,她在客厅里冷了一宿的事。
有钱真好,但这生活不是她自己的,而这一步步踩在天上的感觉,实在太虚幻。
就像那个注定不会属于她的那个人一样,如果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奢望,也便不会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