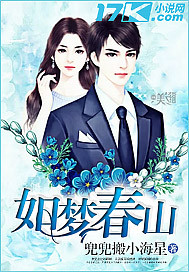何莞尔把车开走不过五分钟,警察就到了。
一部分警察留在现场处理那个半死不活的人,其余的警车和莫春山和孟千阳一道,沿着路搜寻另外一个罪犯以及何莞尔的踪迹。
警车没开出两公里,就发现村道沿着河的一段直路边,有车辆坠落的痕迹。
现场还留着大切的保险杠,路肩上轮胎的痕迹,显然也不是帕萨特的。
很有可能,何莞尔开的车从这里掉进了河沟。
孟千阳心里咯噔一下——车掉下去了,那人呢?
警察一边安排人手在河沟周围搜索何莞尔的踪迹,一边请求支援呼叫蛙人来现场,莫春山已经脱下大衣,
快到孟千阳拉都拉不住。
孟千阳也只好跟着跳下去——春山哥水性不是太好的,这些年虽然一直勉强自己学,然而由于体质不是太好的缘故,他在水下呆不了半分钟的。
孟千阳入水之后,一头扎进那黑漆漆凶险莫测的河沟,只觉得冰冷刺骨。
水深不见底,不是太湍急,但也能感觉到水底的暗流阵阵。
孟千阳忍住寒冷朝莫春山下潜的地方游去,焦急地在水里寻找人和车的踪迹。
但是光线实在太暗,一点也看不清楚。
他好容易终于在水底一块沉黑沉黑的金属边摸到了莫春山,不管不顾地拖着莫春山上了水面。。
莫春山头浮出水面,有些费力地踩着假水,第一句话就是:“她不在车里。”
其实孟千阳也看到了,那车损毁挺严重,车门半开。但是至于里面有没有人,他没看清楚。
莫春山说完那一句,又做出朝下潜的动作。
孟千阳忙拉住他:“春山哥,别去!”
莫春山水性不如他好,刚才下潜到水下五六米的深度,还找到了汽车沉河的位置,已经是体力殆尽到了极限,现在最多只能勉强保持着不下沉而已。
夜黑风高,河水说不上湍急却冰冷刺骨,莫春山要是再下去一趟,只怕就起不来了。
孟千阳自然不会让他再去犯险。
莫春山置若罔闻,奋力挣扎表明了态度。
孟千阳也有些吃力,一边拉着他,嘴里断断续续:“要是找到了她,你却被水冲走,怎么办?”
这话也让莫春山愣了愣,动作一滞。
孟千阳趁着他分神的时机,生拉硬拽,硬是把他拖上了岸,之后死死盯着他,说什么也不让他再靠近岸边。
“让开!”莫春山看着他,声音里带了明显的怒意。
“不行,”孟千阳苦笑,“你想下去,先打死我再说。”
莫春山紧抿着唇,捏紧了拳头,却始终没法对着眼前的这张脸挥下去。
一阵冷风吹过,刚从水里出来的两人,齐齐地打了个寒颤。
莫春山收回了视线,转身弯腰,捡起刚才被扔在地上的外套,掏出了手机。
听着他连打了几个电话,孟千阳才明白他要做什么。
离汽车落水点最近的桐城路桥的工地,在仅仅两公里之外,莫春山被他盯住下不去,却有的是人下去。
十几分钟后,三辆小卡车载着几十个工人浩浩荡荡而来,还有辆车拖着发电机和大大的探照灯一样的家伙,停在了河边。
卡车上下来个四十几岁的中年人,正是那项目的项目经理本人。他一溜小跑到莫春山跟前,微躬着身体:“莫总,人都到了,您要的三十吨以上的吊车也在路上了,最多二十分钟到,可以开工了吗?”
莫春山略一点头,扬高了声音:“下水、找人,一小时一万。”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水性好的工人绑着条绳子就往河里跳,水性不好的守在岸上拉住绳子,也一点都不敢马虎。
现场的警察顿时慌了,天黑水冷非常危险,可现场十个警察,哪里拦得住几十个人下水寻人?
带头的那位警官只好找到莫春山:“同志,这样不合适,这天这么黑的……”
他还没说完,发电机的轰鸣声响起。几盏两千五百瓦的囟钨灯亮起,岸边顿时亮如白昼。
“现在不黑了,”莫春山回答,“出了事,我担着。”
警察哑口无言,只好任他们折腾,自己则联系总队派专业救援队伍来。
莫春山披着条警察找来的毛巾,站在岸边,一瞬不瞬地盯着水面,等待着消息。
没几分钟,就有人冒出水面,大喊:“车在这里!”
又有人浮出水面,抹了把脸上的水,断断续续喊着:“没人,里面没人……”
河道并不宽,堪堪十几米,河水也并不深,近二十个工人下水,没多久就把河底摸了个遍。
依旧没什么发现,连最有可能卡住人的一处葫芦状的河道,也只摸了辆不知道泡了多久的共享单车出来。
莫春山攥紧的手终于松了松,嘴里喃喃念着:“没人,我没看错。”
孟千阳看了眼他紧绷着的侧脸,本想说几句的,终究于心不忍。
这是条河,可不是池塘,也就是说,这里是无边际的。
虽然水流不算湍急,但河底总归是有暗流的,所以这里没找到何莞尔,并不算什么好消息。
她可能是在坠河途中被甩出了车,但能不能逃生就说不清楚了。
保不齐几天以后,她被泡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就会在下游的某个地方浮起来。
二十分钟过去,远处长长的重型货车亮着如灯塔般的卤素大灯,浩浩荡荡地开过来,车上有一辆吊车。
吊车如约而来,消防队的蛙人也是同一时间到的,显然没想到现场会这样热闹。
不过人多力量大,哪怕是杂牌军也有用处,于是马上开始作业准备打捞汽车出水,有了专业的指导业余的队伍,半小时不到,现场就将绳索绑在了沉入河底的汽车上。
吊臂开始启动,一圈圈涟漪扩散开来,水面越来越不平静。
孟千阳身上依旧湿淋淋,被夜风一吹,嘴唇都在哆嗦。
才嘉将衣物递给他,却又被他执着地推了回来。
莫春山都没换下湿的衣服,披着那半新不旧的毯子,狼狈至极,他当然也不能换。
才嘉侧头看了眼还站在岸边一动不动看着打捞情况的莫春山,无可奈何:“这是要闹什么?大冬天的河里泡得湿透,还不换衣服?病了怎么办?”
孟千阳恰巧打了个喷嚏,也苦笑起来:“随他吧,他心里难受,就别去烦他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