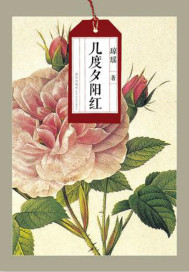这个星期天的节目是紧凑而丰富的,按照魏如峰和晓彤的计划,是:上午九点钟,晓彤到何家,见见何慕天,也参观参观魏如峰居住了多年的屋子,还有与曾有一面之缘的霜霜交交朋友,中午,则留在何家午餐。午饭后,一起去看场电影,逛逛大街,然后去晓彤家里,在晓彤家晚餐。对晓彤而言,这简直是个大日子!早晨睁开眼睛来,耀眼的阳光似乎是最好的预兆。翻身下床,为了穿什么衣服大费周章,穿制服,太不像样!除了制服,竟无一件可穿的衣服!幸好天气还很热,那唯一的一件白纱衣服又派了用场,穿上它,再披一件妈妈的白毛衣,揽镜自照,居然也亭亭玉立,雅洁温婉,像魏如峰常说的,是颗小星星。她不自禁地微笑了。
急急地吃了早餐,在母亲关怀的凝视下,在晓白抿着嘴角的笑容里,还有父亲蹙着眉装作不关心的表情中,她匆匆地走出了大门。站在门外,先来一个深呼吸,再找出魏如峰给她画的那张简图,破例地叫了一辆三轮车,到了中山北路。
车子停在何家门口,晓彤跳下车来,付了车钱,瞻望着那庭院深深的大宅子,她有些迷乱和紧张,站在这两扇阖得严严的大门前面,她才突然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寒伧!伫立片刻,她正想伸手按门铃,大门豁然而开,从里面疾驶出一辆灰色的小轿车,差点撞到她的身上,她慌忙退到一边,车子的驾驶座上,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侧头看了她一眼,给了她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她有些困惑,望着那飞驰而去的汽车开得没有影子了,才掉转头来。回过头,她发现大门仍然开着,一个黝黑得像铁塔似的彪形大汉正倚在门上注视着自己,她嗫嚅着,还没开口,那大汉已咧开大嘴,露出一口白牙,笑着说:
“我是老刘,魏少爷交代过你会来。你是杨小姐吧!”
晓彤连连点头,也对老刘微笑。老刘叫来了阿金,让她带晓彤进去。
阿金领着晓彤穿过花坛和喷水池,走进客厅。晓彤四面环顾,那么大的院子,那么讲究的客厅!站在客厅中,她竟微微有种失措的感觉。这一间房子的大小大概比她家全幢房子的面积还大,沙发是紫红色的,窗帘是同色的绒布,小茶几上铺着织锦桌布,放着一个大的花瓶台灯。另外有一张较大的长桌子,放着一盆白玫瑰,花香弥漫全室……她正浏览着,楼梯上一阵脚步声,她抬起头来,魏如峰带着一脸兴奋的笑,从楼梯上跑了下来。
“嗨,晓彤!真守时!”他叫着说。
“是不是太早了?”晓彤问,“或者你们还没起来。”
“早?”魏如峰含笑的眼睛盯紧了晓彤那张清新秀丽的脸庞,用双手握住她的胳膊,“我已经等了你十二小时。”
“十二小时?胡说!”
“怎么胡说?从昨天晚上九点钟就等起了。”
晓彤闪了一下,躲开了魏如峰想吻她而俯近的头,警告地说:
“别闹,当心给你家下女看到!”
“有什么关系?”魏如峰满不在乎地耸耸肩,“今天,我姨夫起晚了,平常他都是一清早就起来的。昨天晚上来了个客人,和姨夫谈到深更半夜。哦,或者你听说过,墨非!”
“墨非?是不是王孝城?”
“对了,你知道他?看,墙上那张《寒雁图》就是他画的,他是姨夫的老朋友,昨晚跑来不知和姨夫谈些什么,据说半夜两点钟才走。要不然,姨夫也不会睡到现在。你可别以为我们都是爱睡懒觉的。”
“好了,”晓彤笑了起来,“我也没有说什么,看你解释上这一大堆。”
“只因为——”魏如峰托起她的脸来,凝视着她的眸子说,“太希望能给你一个好印象!”说着,他放开她,转开身子说:“你想喝点什么?天气还是这么热,我去帮你调一杯柠檬汁,怎样?我自己调得比较好,阿金每次都调得太甜,你坐坐,我马上来!”转过身子,他走进餐厅里。
天气确实很热,台湾季节之分最不明朗,天气变化也最突兀,十一月了,仍然像夏季一般。晓彤脱下了那件白毛衣,站起身来,走到墙边,去看王孝城所画的那张《寒雁图》。这是一张大画,整个画面是两只雁,和几匹随风倾倒的芦苇。一只雁蹲伏在芦苇中,另一只作振翅起飞的样子,画得非*健有力。正欣赏着,她听到身后有脚步声,知道是魏如峰来了,就依然仰视着画说:
“王孝城也是我爸爸的老朋友,很巧,是不是?就是因为爸爸碰到了他,所以家里才造成低潮气氛,他鼓励爸爸画画——哦,我有没有告诉过你,爸爸是国立艺专毕业的?爸爸画工笔人物,最长于仕女。但是,他总是画不好,每次画坏了,就和妈妈发脾气。妈妈呢,也总是忍耐着……”晓彤停住了,因为身后的人一直没有说话,而诧异地转过身子来,等她一转过身子,才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身后,并不是她想像中的魏如峰,而是个中年男人,颀长的身子,温雅的面貌,皮肤比一般男人白晰,就显得眼睛特别地深而黑,有两道不淡不浓,却极英挺的眉毛。一眼看过去,这人混合着儒雅和威严的双重气质,还略带着几分忧郁。他似乎正专心地注视着她,当她一回头的那一刹那,她注意到他眼睛中光芒一闪,脸色立即显得十分苍白。她为自己那一大段自说自话而感到尴尬,嗫嚅着说:
“我——我以为是如峰,您——?”
“我是如峰的姨夫,”何慕天说,声调中带着些难以抑制的颤栗,“你——你就是——杨——杨——晓彤?”
“是的,何伯伯。”晓彤恭敬地说,点了点头,同时对何慕天展开一个温柔而宁静的微笑。
何慕天一瞬也不瞬地盯着面前这张年轻而姣好的脸,那微笑让他震动,并且绞紧了他的五脏,使他浑身都疼痛而抽搐起来。怎样的一张脸!似曾相识的脸庞,似曾相识的神韵,似曾相识的微笑!那小小的身子裹在那银白色的软纱之中,看来是那样的纯净、雅洁和灿烂!银白色的衣服!他找寻什么似的从那有着小花边的衣领,看到那宽宽的下摆。一阵眩晕感对他袭击了过来,摸索到沙发椅子,他身不由己地坐了下去。晓彤似乎有些惊惶,她走到他面前,疑惑地凝视着他,关心地问:
“您不舒服吗?何伯伯?”
“哦,没——没有什么,”何慕天挣扎着说,指指前面的沙发,“坐下来,晓——晓彤。”
晓彤顺从地坐了下去,仍然疑惑地望着何慕天。何慕天闭了闭眼睛,用颤抖的手燃起了一支烟,竭力地想放松自己过分紧张的情绪。晓彤!在昨天晚上之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如峰的小爱人竟是杨明远和梦竹的女儿!杨明远和梦竹的女儿?是吗?昨夜,王孝城把晓彤的底细揭露时曾震惊地说:“你居然不知道梦竹当年为什么去找你?”
“你居然不知道你自己做下的事情——”
是的,居然不知道!假若他知道,他不会让梦竹离开他去嫁给明远!年轻时,是多么的糊涂和容易冲动,他竟让梦竹走掉!让她去嫁给明远!而现在,坐在他面前的是杨明远和梦竹的女儿!不错,世界是太小了,小得像块豆腐干,碰来碰去还是原班人马!魏如峰谁都不爱,偏偏爱上晓彤!魏如峰,他欣赏的男孩子,他曾想将霜霜嫁给他,他看不上霜霜,却看上了晓彤!世界上的事多么不可思议!多么纷杂和零乱!
“晓彤那个女孩子,气质和长相都极像她的母亲,只是,仿佛比当年的梦竹更沉静一些!”
这是昨晚王孝城嘴中所描述的晓彤。可是,给他的印象远没有晓彤自己给他的来得鲜明深刻!她岂止是像梦竹,她那股宁静的味道简直就是当年的梦竹!只有那对黑蒙蒙的眼睛和梦竹不同,这对眼睛里盛着许多他熟悉的东西:梦、憧憬、幻想和热情!面对着这张依稀相识的脸,他感到全心灵的震荡和激动。魏如峰端着两杯柠檬汁走了过来,一眼看到晓彤和何慕天默然对坐,不禁愣了一下。接着高兴地嚷着说:
“姨夫,我来介绍一下吧——”
“不用了,”何慕天对魏如峰摆了摆手,眼睛仍然停驻在晓彤的脸上,“我们已经彼此认识了。”
“是吗?”魏如峰愉快地问,把两杯柠檬汁分别放在何慕天和晓彤的面前,“你们谈了些什么?”
晓彤抬起眼睛来望了魏如峰一眼,神情有些困惑。她奇怪何慕天为什么要这样古怪地注视着她,仿佛她是个突然从地底冒出来的人物,全身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魏如峰在晓彤身边坐了下来,看了看何慕天,后者脸上那种专注和类似严肃的表情使他诧异,有什么事让何慕天不安了?笑了笑,他说:
“姨夫,晓彤让你吃惊了?”
何慕天从遥远的思想里返回现实,抽了一口烟,他让烟雾从鼻孔里冒出来,惘然地一笑说:
“确实有些吃惊,她像颗小星星。”
“哈!”魏如峰眉飞色舞,“姨夫,你的眼力不错,我一直就叫她做小星星。又亮、又美、又高!”
晓彤的脸红了,羞涩和喜悦在她的眸子里盈盈流动,那焕发着光彩的小脸明丽动人。何慕天无法把眼光从她的脸上移开,紧紧地望着她,他问:“你在念书?”
“唔,×女中高三。”晓彤说。
“明年暑假毕业?”
晓般点点头。
“你家里有些什么人?”
“爸爸,妈妈,和一个弟弟。”
“你爸爸——”何慕天困难而艰涩地问,“喜欢你吗?”
“噢,”晓彤微笑了,“爸爸总是要比妈妈严肃一些的,是不是?妈妈脾气好,爸爸比较急躁一些。不过,爸爸也不常骂我们,他说我是女孩子,不太注意我。他对晓白很关心——晓白是我弟弟。”
“哦,是吗?”何慕天非常注意地听她说,接着又以一种迫切而过分关怀的语气说,“你妈妈——你妈妈——我是说,你们生活得很好吗?很——愉快吗?”
“哦。”晓彤又笑了,眼睛明朗而生动地望着何慕天,“我们家一直很苦,可是妈妈很会算,有时候我们全家都睡了,妈妈还在灯下算账。爸爸的薪水不多,晓白的学费很贵,不过,妈妈总是使我们维持下去,从不肯借债。只是,最近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爸爸想画画开画展,他已经有十几年没画过了,都是王伯伯——就是王孝城,你知道?”她停下来,询问地看着何慕天,后者立即点了点头,她又接下去说,“他建议爸爸画画开画展,结果,花了很多钱去买颜料、纸、和画笔,弄得我们只好天天吃素,家里也揽得乌烟瘴气——”她的眼睛变得晦暗了,眉头轻轻地锁拢。“爸爸总是画不好画,每次画不好,就拿妈妈出气,好像他画不好画全是妈妈的责任似的。妈妈也就委委屈屈地受着,当着爸爸的面前不说话,背着爸爸就淌眼泪……”她猛地住了口,怎么回事?自己竟把这些家务事啰啰嗦嗦地向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诉说?多傻多无聊!她涨红了脸,呐呐地说:“我……我……我说得太多了。”
何慕天正全神倾听着,眼睛渴切而热烈地盯着晓彤的脸,听到晓彤有停止述说的意思,他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向前俯了一些,近乎焦灼地说:“说下去!不要停止。”
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命令的味道。魏如峰再度诧异地看了何慕天一眼,姨夫今天未免有些反常,不过,看样子,他已经喜欢晓彤了。本来嘛,晓彤生来就具有使人不能不爱的气质,他早就猜到何慕天一定会喜欢她的。看到他们谈得那么投机,他感到说不出来的愉快和欣喜。
“说——什么呢?”晓彤微笑地问。
“你妈妈——和你爸爸!”何慕天急迫地说。
“爸爸是国立艺专毕业的,据说,没毕业前就和妈妈结了婚。”晓彤又继续说下去,“婚后没多久,就生了我,再一年,又有了晓白,胜利后我们就跟着艺专复员到杭州,所以爸爸也可以说是杭州艺专毕业的。接着又打起仗来了,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和晓白逃难,受了很多苦才到台湾。那时我才三四岁,晓白两岁,家里很穷,爸爸就到机关去当临时雇员,然后升到正式职员,一晃十几年,爸爸一直没有调动,他总说他学非所用,当小职员委屈了他。妈妈就很难过,常常说都是她拖累了爸爸,说爸爸应该成个大画家,所以,近来爸爸画画,妈妈也很鼓励他。但是,他没画成过一张画,他说笔生锈了。爸爸是画工笔人物的,常常画美人,但是,也常常给美人洗脸——哦,”她笑了,凝视着何慕天。
“说下去!”何慕天催促着,吐出一口烟雾。
“给美人洗脸,这句话是晓白发明的,晓白经常发明许多稀奇古怪的话。是这样的,爸爸每次画美人脸画好了总不满意,不是说韵味不好,就是说神态不对。于是,他就要把画好的美人脸洗掉重画,这样,一个美人脸洗上三四次,白脸都变成了黑脸,一张画纸也就报销,连同美人一起进了字纸篓。碰到这种时候,晓白就带着他的武侠小说溜出大门,我也得赶快钻进我的房间!只有妈妈无处可逃,赔着笑脸听爸爸发脾气。所以在我们家里,美人进字纸篓的时刻,就是最可悲的时刻。”
何慕天深深地凝视着晓彤的脸,在晓彤的述说里,明远的家庭,梦竹的生活,都清楚地勾画在他眼前。他觉得自己的心脏被绞紧,被压榨,被碾碎。痛楚、酸涩和歉疚的各种感觉一起涌上心头。他的四肢发冷,额上沁出冷汗,香烟在指缝中颤抖。连吸了好几口烟,他才能稳定自己的声调,问:
“那么,在你家里,是你爸爸操纵着全家的喜乐?”
“确实如此,”晓彤点点头,“爸爸高兴,全家都高兴,爸爸一皱眉头,全家都要遭殃。妈妈好像有些怕爸爸,被逼急了,才会说几句。”
何慕天不再说话了,他靠进了椅子里,深深地吸着烟,仿佛他只有吸烟是唯一可做的事了。他的眉头锁得很紧,一口口烟雾把他包围着,笼罩着,脸色却出奇地苍白。晓彤有些不安,她不大明白何慕天是怎么回事,她用询问的眼光望了魏如峰一眼。魏如峰也同样地困惑,望了望何慕天,他忍不住地问:
“姨夫,你没有不舒服吧?”
“没有。”何慕天悠悠地回答,心神似乎飘浮在另一个世界里。
阿金走了进来,对何慕天说:
“老爷,你的早饭都冷了。”
“收下去!”何慕天简单地说,“不吃了。”
阿金退了下去。魏如峰心中的困惑在加深,到底怎么了?何慕天和平常像是变了一个人,关键在什么地方?晓彤吗?他看看晓彤,后者纯净的脸庞上,只有温柔和宁静,应该没有原因让何慕天烦恼呀。或者是为了霜霜,见到晓彤难免想起日趋堕落的霜霜。对了,原因就在此,找到了答案后,他觉得不必让晓彤再和何慕天面面相对,于是,他站起身来说:
“晓彤,要不要到我房里来参观参观?”
“好,”晓彤说着,又不放心似的望了望何慕天,慢慢地站起身来。何慕天像是突然醒了过来,他坐正身子,把烟蒂在烟灰缸中揉灭,用充满感情的口吻说:
“过来,晓彤,让我看看你!”
晓彤微带诧异地走近何慕天,魏如峰不解地皱皱眉,他奇怪姨夫竟已直呼晓彤的名字,但,接着他就释然了,反而有份意外的惊喜。何慕天看着晓彤走近,情不自禁地用手握住了晓彤的双手,那柔若无骨的小手引起他内心一阵剧烈的激情。他目不转睛地凝视她,逐渐地,他觉得眼眶湿润,喉头哽结。久久,他才放开她的手,转头对魏如峰语重心长地说:
“如峰,珍惜你所得到的。”
“姨夫,你放心。”魏如峰说,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让何慕天放心,只感到颇被何慕天的神色所感动。
“你们去吧,”何慕天说,显得十分疲倦,“如峰,好好地带晓彤玩玩,我要去休息一下。”
魏如峰点点头,带着晓彤走上楼梯,已经到了楼梯顶,何慕天突然又叫:
“如峰,过来一下。”
魏如峰再跑下楼,何慕天深思地问:
“你今天下午要到晓彤家里去吗?”
“是的。”
何慕天默然片刻,吞吞吐吐地说:
“如果你去,最好——最好——别提到我的名字。”
“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记住就好了。”
魏如峰困惑地摇摇头,想到晓彤在楼梯上等他,他没有时间再来追究底细,匆匆地跑上了楼。
何慕天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房门,乏力地倒在床上,用手抵住疼痛欲裂的额角,自言自语地说:
“我必须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
他真的想了,从昨晚王孝城来访想起,直到刚刚见到晓彤为止。却越想越复杂,越想越纠缠不清,头里昏昏沉沉,心中迷迷离离。就这样,他一直躺着抽烟,思想。中午,阿金来请他吃饭,他理也没有理。然后,暮色来了,室内荒凉而昏暗,他无力起来开灯,如患重病般瘫软在床上,嘴里喃喃地低语:
“天哪,怎么办呢?我能怎么办呢?”
尖锐的汽车喇叭声惊动了他,摇摇头,他从床上坐了起来,是霜霜!霜霜,他都几乎忘记她了。下了床,他步履瞒跚地走出房门,刚刚走到楼梯口,就和喝得已经大醉的霜霜遇上了,霜霜摇摇摆摆地半吊在楼梯扶手上,一眼看到何慕天,就大叫了起来:
“哈!家里的一个男人在家,另外一个男人在哪儿?”
“霜霜!你又喝醉了?”何慕天沉痛地问。
霜霜走了上来,用两只手搭在何慕天的肩膀上,醉眼乜斜地望着何慕天,笑着说:
“你不喜欢我喝酒?爸爸?你不觉得喝醉了的我比清醒的我可爱吗?我还没有完全醉,”她用手指指自己的头,醉态可掬地说,“最起码这里面还有一部分是清醒的。”
“唉!”何慕天叹了口长气,把霜霜的手臂从肩膀上拿下来,想回到房里去。但,霜霜一跳就跳了过来,拦在他面前,嚷着说:
“爸爸!别走!”何慕天站住,霜霜笑着说:
“有一样东西要给你!”她打开她的手提包,一阵乱翻,把口红、手絹、指甲刀——等东西掉了一地,好不容易,找出了一个信封,递给何慕天说,“今天早上我在信箱里找到的,一封美丽的信,请你冷静地看,少批评!少发表意见!”
何慕天看看信封,是霜霜所念的中学寄来的,抽出信笺,上面大致是:
“敬启者,贵子弟何霜霜因品行不端,旷课过多,并在校外酗酒闹事者多次。故自即日起,勒令退学,并望家长严加督促云云——”
何慕天抬起头来,凝视着霜霜,霜霜立即把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警告地说:
“我讲过,少批评,少发表意见!如果你多说一句,我就放声大哭!我说到做到,你看吧!”
何慕天蹙起眉头,仍然注视着霜霜,显然霜霜的威胁并不是假的,她的大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泪珠摇摇欲坠地在睫毛上颤动,那丰满的嘴唇微张着,似乎随时准备张开来痛哭一场。何慕天咬咬牙,叹口气,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躺回床上,他用手捧住头,反复地低叫:
“天哪,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隔着一扇门,霜霜的歌声又传了过来:
香槟酒气满场飞,
舞衣人影共徘徊……
歌声带着微微的震颤,在暮色里飘摇传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