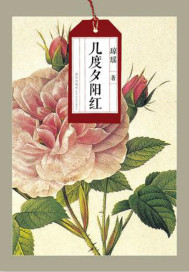夜深了,何霜霜缓缓地驾驶着车子,向中山北路的家中驶去。深夜的街道上是一片寂静,连十字路口的警察岗亭里都已空无一人,红绿灯无人操纵,冷冰冰地孤立在街头。现在,空旷的街道上没有车辆和她争前抢后了,可是,她反而不想开快车,只轻缓地让车子在夜色里向前滑行。风从开得大大的窗子里灌进来,撩起了她的短发。在车灯照射下的街道,寂寞得连小猫小狗的影子都没有。
一个星期天,又过去了。何霜霜疲倦地扶着方向盘,倦意正在她体内和四肢中流窜。想想看,一清早和顾氏三兄弟开车上阳明山,三兄弟,一个赛一个的宝气。顾德中,外表活像只大狗熊,说起话来,舌头在口腔里绕半天的圈子,才吐得出一声清楚的话:“我……我……我从小有音乐天才,学小提琴,才……才三星期,就能拉莫扎特的小步舞曲。”见他的鬼!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她就想像不出狗熊拉小提琴是副什么样子。顾德华,油头粉面,整天头发梳得光光的,衣服上还要喷点他母亲的夜巴黎香水。“我哦,我的名字是顾德华,你猜什么意思?就是照顾得了花,你就是花,哈哈!”哈哈,下你的地狱去,恶心得够受!顾德民,三兄弟中唯一看得过去的,论外表,文质彬彬、秀秀气气,鼻梁上架副近视眼镜,似乎勉强能算美男子。但是,说上一句话就要脸红,哼哼唉唉半天,也听不清他哼些什么,大概前辈子是蚊子转世来的。和这三个宝气游阳明山,就别说有多气人了,三个大男人,围在你身边,碍手碍脚,一转身,不是碰着这个的鼻子,就是挨着了那个的肩膀……到中午回台北午餐,吃完了午饭,趁早把三兄弟打发回去。然后又去找了小赵,小赵别无所长,猴儿巴唧的,就是会说笑话,做鬼脸,标准的小丑典型。和小赵去跳了场舞,赶了一场六点钟的电影,电影散场时碰到小陆那一群男男女女,又去跳舞,舞厅打烊,出来再吃点宵夜,然后赶走小赵,自己独自地开车回家。一天,就是这样,疯狂地,尽兴地,玩玩玩!“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秋天的月,是多么明亮,少年的我,是多么快乐……”快乐吗?无论如何,总是在追寻着快乐。舞厅里那些人,绿的酒,红的灯,疯狂的旋律!那个歌女唱的歌:“舞步轻燕,舞态如天仙,青春少年,欢乐无限……”欢乐无限,是吗?欢乐无限!……她猛然刹住车,有点眼花缭乱,车子仿佛碰到了什么,她向前面看看,揿揿喇叭,什么东西都没有。她甩了甩头,用手揉揉眼睛,头里昏昏然,眼睛发涩,疲倦仍然在四肢中流窜。她闭了闭眼睛,重新发动了车子。
车子停在家门口,她揿揿喇叭,没有人来应门,她再揿揿喇叭,依然没人应门,老刘一定已经睡成个死猪了。她不知道何慕天和魏如峰为什么都喜欢老刘,粗里粗气的。她把头扑在方向盘上,干脆压在喇叭上,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在夜空里播送,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附近的人家有人推开窗子诅咒,但喇叭声仍然清越地传送着。
大门开了,霜霜抬起头来,一面懒懒散散地跨下车子,一面睡意朦胧地说:
“把车子开到车房里去!”
“唔,夜游的女神终于回来了!”
霜霜抬起眼睛,这才看清面前的人,她耸耸肩说:
“原来是你!表哥,你还没睡?”
“就是睡了也被你吵醒了,你什么时候能学会不打扰别人?”
“不要说教!表哥,我今天玩了一整天,累极了。”霜霜说着,向房子走去,一面对魏如峰摆摆手,“麻烦你把车子送到车房里去!”
魏如峰皱皱眉头目送霜霜蹒跚地走进屋去,不禁深深地摇了摇头。
霜霜摇摇晃晃地走上了楼,回到自己的卧室,往床上一扑,弹簧床垫立即迎着她的身子,把她软软地包了起来。拖过一个枕头,她把脸埋在枕头里,昏昏噩噩地躺了一阵。然后,她站起身来,取了睡衣,到浴室里去。放上一缸冷水,她把自己泡在凉凉的水中,皮肤骤然接触到冷水,引起一阵痉挛和紧张,然后就松弛了下来。冷水使人清醒,她最喜欢冷水浴,每当她疲倦或烦恼的时候,她总以冷水浴来治疗自己。在水中浸了一个够,她拭干身子,穿上那件她最喜爱的鹅黄色绸睡衣,站在镜子前面,梳了梳头发,头脑清醒多了。她瞠目注视着镜子,奇怪地看着镜子里那对漂亮而困惑的眼睛,她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对镜子里的人影傻傻地问了一句:
“这是我吗?这就是我吗?多无聊的我!”
无聊!对了,就是这个词,她找了许久的名词,无聊!生活中全是无聊,阳明山,跳舞,看电影,顾氏三兄弟,小赵,小陆,吃宵夜!全是无聊!她对着镜子皱眉,突然涌上心头的空虚和落寞感使她鼻中酸楚。生活,就是这样的吗?她并不想要这种生活!可是,她要什么生活呢?镜子里的眼睛更困惑了,她对镜子挑挑眉,噘噘嘴,发出一声微喟:
“我竟然不了解自己,多可怕!”
走出浴室,她沿着宽阔的走廊向自己的卧室走去。经过魏如峰门前的时候,她看到门缝里还透着灯光,她略微迟疑了一下,就推开门走了进去。
魏如峰穿着睡衣,半躺半坐地倚在床上,床头柜上亮着一盏台灯,他手中握着本英文小说,正在看得出神。听到门响,他抬起头来,望着霜霜。霜霜顺手关上门,走到床边来,坐在床沿上。魏如峰默默地看了她一眼说:
“你知道几点了?”
霜霜噘噘嘴,眨眨眼睛,什么话都不说。
“你玩得还不累?为什么不去睡觉?”
“刚刚好像很累,现在又一点睡意都没有了。”霜霜说,倚着床栏,没来由地叹了口气。
魏如峰深深地打量着霜霜,那两道挺秀而浓密的眉毛微锁着,长睫毛半掩了那对平时充满野性,而现在充满困惑的眼睛。有什么事使这个不知忧愁的女孩烦恼了?爱情吗?他阖上看了一半的英文小说,用手托着下巴,做出一副准备长谈的姿态来,说:
“怎么了?霜霜,和谁怄气了?”
霜霜沉默地摇摇头,一绺黑发从耳边垂了下来,拂在面颊上。她用牙齿轻咬着下唇,眉头锁得更紧了。魏如峰诧异地望着她,好半天,她才甩了甩头,把那绺不听话的头发甩到脑后去,直视着魏如峰说:
“表哥,你很快乐吗?”
魏如峰愣了一下,说:
“怎么想起问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你不快乐?”
“唔,”霜霜垂下了眼睛,“疯狂地玩的时候,可以有短时间的快乐,但是玩过了,又什么都没有了。你懂吗?表哥?就像现在,想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意思,非常地……非常地……”她凝思着,想找出个适当的字眼来描写她的心情。
“空虚?”魏如峰试着代她接下去。
“对了!”霜霜高兴地拍拍床垫说,“就是这两个字!”
魏如峰坐正了身子,审视着霜霜,不由自主地微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霜霜瞪着眼睛说,“我和你谈正经的,有什么好笑?”
“我笑你觉得空虚,”魏如峰说,“大概你是生活太优越了,整天在外面疯呀闹呀玩呀,回到家里来还喊空虚,不是很有趣吗?”
“我一点也不觉得有趣!”霜霜没好气地说。
“不过,”魏如峰收住了笑,深思地说,“能感到空虚,总是一件好事。”
“好事?你是什么意思?”
“这证明你长大了,成熟了,懂得用思想了。”
霜霜困惑地望着魏如峰。
“你看,”魏如峰解释地说,“你最喜欢跳舞,和男孩子开车兜风,到小吃店大吃大闹,把人家的酱油倒到醋瓶子里,觉得很开心。现在呢,你感到空虚了,换言之,你也就是对于那种玩法不能满足了。这,充分表示你在进步。唔,”他笑嘻嘻地看着霜霜,“看样子,大小姐快要改邪归正了,可喜可贺!”
“呸!”霜霜一唬地跳起身来,站在床前面,瞪大了眼睛说,“什么改邪归正?是谁邪谁正?你也不是好东西,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好好好,你知道,”魏如峰打断了她,把她拉下来,让她仍然坐在床沿上。收起了嘻笑的态度,诚挚地说,“告诉我,霜霜,这次月考的成绩如何?”
“哼,”霜霜凝视着自己的手指甲,心不在焉地说,“谁知道!”
“准备明年不毕业了吗?”魏如峰问。
“表哥!”霜霜喊,“我不喜欢你这种冒充大人的味道!”
“冒充大人?”魏如峰失笑地说,“我已经二十七岁了,还不算大人吗?什么叫冒充大人的味道?”
“我是说,冒充长辈的态度!”
“长辈?”魏如峰笑笑,“我没有要冒充你的长辈呀,我是以一个哥哥的身份和妹妹谈话,你不是我的小妹妹吗?刚到台湾的时候,你才三四岁,话都说不清,把‘哥哥’念成‘多多’,成天跟在我后面喊‘多多’,要我背你到街上去买棒棒糖。哼,现在呀,你长大了,‘多多’只配给你送汽车进车房的了。”
“哎哟,”霜霜叫,“别那么酸溜溜的,好不好?”
“那么,听我讲几句正经话,”魏如峰说,“霜霜,这种昏天黑地胡闹胡玩的生活该结束了吧?你是真不爱念书也好,假不爱念书也好,最起码,你总应该把高中混毕业!是不是?你刚刚说不快乐,我建议你收收心,安安静静在家里过几天日子,好好地用用思想,或者会帮你找到宁静和快乐。你现在仿佛一只找不着家的小兔子,迷失在这繁华时代的浓雾里,整天尴尴惶惶,东奔西窜,自己也不知道目的何在,这样,怎么会快乐呢。……”
“我不听你讲这些!”霜霜再度跳了起来,把睡衣带子系系好,向房门口走去,“你又不是我的训导主任,谁来找你训话的?还不如睡觉去!”她走出房门,又回过头来,对魏如峰笑了笑,抛下一声,“再见!”
房门带上了,魏如峰望着那砰然阖拢的房门,发了一阵呆,才蹙着眉,摇了摇头。
重新拿起那本英文小说,他想继续看下去,可是,页数弄乱了,翻了半天,也找不到原来的那页,却从书里翻落出一张照片来,拾起照片,上面是个女子的半身照,画得很浓的眉毛,厚嘟嘟的嘴唇,和一对大而充满魅力的眼睛。他又皱皱眉,翻过照片的背面,有几行女性的笔迹:
给如峰:
别忘了那些浓情蜜意的夜晚,
更别忘了那些共同迎接的清晨。
杜妮
他凝视着这两行字,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记得这张照片是杜妮两星期前给他的,不知怎么夹到这本书里来了。望着这两行字,他感到非常地刺心。刚刚,他还义正辞严地教训霜霜:“这种昏天黑地胡闹胡玩的生活该结束了吧?”可是,自己呢?这儿就有堕落的证据!迷失,是霜霜在迷失,还是自己在迷失?把照片夹回书里,书丢在床头柜上,他关了灯,躺在床上,用手枕着头,眼睁睁地望着黑暗的空间,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或者,是该我来仔细地用用思想。”
瞪着天花板,他真的沉思了起来。
霜霜回到了自己的屋里,慢慢地走到床边,躺了下去,用手枕着头,她没有立即关灯。床头柜上是一盏浅蓝色的台灯,灯影下亭亭玉立着一座小小的维纳斯石膏像。这石膏像还是去年她过十七岁生日时魏如峰送她的,当时,魏如峰说:
“我发现这石膏像的侧影像极了你的侧影,所以买给你。”
结果,害她天天对着镜子研究自己的侧影,说真话,除了自己也有个较高的鼻子外,她可找不出自己与维纳斯有什么相像的地方。不过,无论如何,她很喜欢这座平凡的小石膏像,尤其因为,这石膏像有种沉静恬然的味道,这是霜霜一辈子也无法具有的。凝视着这石膏像,她是更加没有睡意了。
“我建议你收收心,安安静静在家里过几天日子,好好地用用思想,或者会帮你找到宁静和快乐。”
魏如峰的话在她耳边轻轻地回响,像一条小溪流般淋淋然地流过。她眩惑地瞪着石膏像,是的,昏天黑地胡闹胡玩的日子!即将来临的高中毕业和大专联考!该结束了,游荡的日子!该结束了,胡闹的岁月!魏如峰的“说教”也不是没有几分道理,只是,“改邪归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收收心,如何收法?大代数、解析几何、物理、化学……要命!生来与书本无缘,又怎么办呢?她一动也不动地望着灯光下石膏像的影子,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她始终瞪着对大大的眼睛。终于,疲倦来临了,一日的纵情游乐使她筋肉酸痛,眼皮上的铅块向下拉扯,她懒洋洋地伸手去关灯,一面轻轻地,对自己许诺似的说:
“明天,一切从明天开始。”
灯灭了,她把头深深地倚在枕头里,阖上了眼睛。
何慕天吃完了他的早餐,燃上一支烟,靠进椅子里。壁上的大钟已七点半,霜霜还没有下楼,看样子,她今天又要迟到了。深吸了一口烟,他望着烟雾扩散,心中在打着腹稿,怎样等霜霜一下楼就教训她一顿。近来,霜霜的任性、冶游、放浪形骸,已经一天比一天厉害。这样下去,这孩子非堕落不可。他只有这一个女儿,再也不能继续纵容下去了。他板了板脸,竭力使自己显得冷静和严肃。这一次,他一定要厉厉害害地骂她一顿,决不心软。虽然他从没骂过霜霜,可是,如今已经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霜霜下楼了,穿着得很整齐。白衬衫,黑裙子,头发梳得好好的,满脸带着股清新的朝气,看起来竟然一反平日的飞扬浮躁,而显得文静安详。她对父亲扬了扬眉毛,用近乎愉快的声调说:
“早,爸爸。”
何慕天咽了一口口水,尽力压制自己内心想原谅霜霜的情绪。吐出一大口烟雾,他坐正了身子,沉着脸,用自己都陌生的、冷冰冰的语气说:
“霜霜,昨晚几点钟回来的?”
霜霜愣了愣,今天父亲是怎么回事?情绪不好吗?她从阿金手上接过面包,好整以暇地抹上牛油,慢吞吞地说了一句:
“我没有看表。”
“你没有看表,我倒看了,午夜一点整。”何慕天说,口气是严厉的,责备性的。
霜霜咬了口面包,望了何慕天一眼,默默不语。看样子,今天是大不吉利,一清早就要触霉头!有谁给父亲吃了*吗?从来也不管她的行动,怎么今天大管特管起来了?
“你看,你把车子开走,事先也不告诉我一声,等我要用车子的时候找不到车子,出去一整天,到深更半夜回来,还要死命揿喇叭,弄得四邻不安!霜霜,你未免太过分了,这样下去,你准备做太妹是不是?”
霜霜停止了吃面包,瞪着一对大大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何慕天。她不相信父亲会用这种口气对她说话,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尤其在今天!今天,一清早,起来晚了,但她仍然振作精神,梳洗、穿衣,对着镜子发誓:“从今天起,何霜霜要改头换面了。”然后跑下楼梯,以为接待自己的是个光辉灿烂的、崭新的一天。但是,什么都不对劲了,没有阳光,没有朝气,没有活力,所有的,是父亲冷冰冰的脸和无情的责备!
“你出去玩玩也罢了,”何慕天一鼓作气,把要说的话都趁自己没有心软的时候全部倾出来,“你却这么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泡舞厅!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别人都念书准备考大学,你呢?糊糊涂涂地过些什么日子!我问问你,你对未来有些什么打算?你这样混下去,就是要嫁人,都没有人敢娶你!你那群不三不四的男朋友,全是些不务正业的小太保,你呢——”
“是个太妹!是吧?”沉默已久的霜霜陡地爆发了,她愤然地接了下去,一面从餐桌上跳了起来,把吃了一半的一块面包扔在桌上。受伤的自尊心,与愿望相违的这个早晨,使她又伤心,又激怒。昂着头,她直视着何慕天,叫着说:“我的朋友都是太保,你骂他们好了,你看不起他们好了,但是他们会陪我玩,会照顾我,会爱我,崇拜我!除了他们,我还有什么?这个家,从楼上跑到楼下,经常连人影都抓不到一个!你有你的事业,表哥有他的这个妮,那个妮。我就有我的太保朋友!我要他们,我喜欢他们,怎么样?你一点都不懂我。……”
何慕天愕然了,把烟从嘴里取了出来,他怔怔地望着霜霜,已经忘了要责备她的初衷,他结舌地说:
“可是,我——我并没有忽略你呀,我爱你,重视你,给你一切你需要的东西……”
“需要的东西,”霜霜垂下眼睛,突然涌上心头的伤心使她声音哽咽,“你根本不知道我需要些什么东西!”
“那么,”何慕天无助地说,霜霜泫然欲涕的样子使他心慌意乱,“你需要什么呢?”
霜霜瞪视着何慕天,冲口而出地说:
“母亲!”
像是挨了迎头一棒,何慕天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呆呆地望着霜霜,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霜霜喊出了这两个字之后,也猛地吃了一惊,却又无法收回这两个字,看着父亲的脸色转变,她心慌地低下了头。母亲,母亲在何方?这是她从小就有的疑惑。“妈妈在哪里?”小时候,攀着何慕天的脖子问。“死了!”何慕天垮下脸来,把她从膝上推下去,怫然地转身走开,但她知道母亲没有死。母亲,母亲在何方?她用手指划着桌子,低低地说:
“我希望我有妈妈,如果她已经死了,我希望知道她是什么样子,家里,连一张她的照片都没有!假若有她的照片,最起码,我可以把我心底里的话,对着她的照片诉说。”她的声音是哽塞的,她触及了自己真正的痛楚,眨了眨泪水迷蒙的眼睛,她继续说:“有许多事情,是女儿需要对母亲说的,不是父亲!如果我有个妈妈,我一定很乖,很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没有!”泪水流下了她的面颊,她用手背拭了拭眼睛。忽然间,千万种酸楚都齐涌心头,她控制不住,痛哭着转过身子,奔出了餐厅。
何慕天仍然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他听到霜霜跑过回廊的脚步声,和奔下台阶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汽车引擎的喧嚣和风驰电掣般开远的声音。他漠然地听着这一切。霜霜的话把他拖进了一圈逝去的洄漩中,他只感到思潮澎湃而情感激荡,那些久远的往事像浪潮般对他冲击翻滚过来,一个浪头又接一个浪头,打得他头脑昏沉而冷汗淋淋。他把烟塞进嘴里,吃力地从椅子里站起身,迈着不稳定的步子,走出餐厅,向楼上走去。在楼梯上,他和迎面下来的魏如峰碰了个正着,魏如峰顿时一惊,他被何慕天的脸色吓住了。
“怎么?姨夫?你不舒服吗?”
“没有什么,”何慕天很疲倦似的说,“有点头晕,你给我带个信给顾总经理,我今天不去公司了。”
“哦,好的。”魏如峰说,“不过,要不要请个医生来?”
“不,不要,什么都不要!”何慕天挥挥手,径直向楼上走去,“叫人不要来打扰我,我要好好地躺一躺。”
魏如峰狐疑地望着何慕天的背影,不解地摇摇头。下了楼,他走进餐厅,阿金送上他的早餐,他吃着包子,阿金压低了声音,报告新闻般地说:
“老爷发了脾气。”
“为什么?”魏如峰问。阿金是个十七岁的小姑娘,长得还很白净,就可惜有两颗台湾少女特有的金门牙。
“他骂小姐,小姐哭了。”
“什么?”魏如峰吓了一跳,何慕天骂霜霜已属不平常,霜霜会哭就更属不平常。
“不知道为什么,”阿金吊胃口似的说,“我只听到小姐说想她妈妈。”
魏如峰怔了怔,问:
“小姐呢?上学去了?”
“没有,”阿金摇摇头,“她没有拿书包,开了汽车走了。”
“哦。”魏如峰皱着眉。试着去思想分析,却一点眉目也想不出来。匆匆地结束了早餐,他骑着他的摩托车到公司里去,平常,他和何慕天一起去公司就坐汽车,他自己去就骑摩托车,他有一辆非常漂亮的司各脱摩托车。
骑着摩托车,他向衡阳路驰去,这正是学生上学和公务员上班的时刻,街上十分拥挤,各种不同的车辆在街上争先恐后地驰着,喇叭声此起彼落地长鸣不已。他经过火车站,在公共汽车总站上,每一路的站牌下都站满了等车的人和学生。他不经心地看了那些人一眼,摩托车从那长龙般的队伍前滑过去。忽然,他觉得有种第六感牵掣了自己一下,那队伍中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吸引了他。他掉转车子,再骑回头,于是,他发现有一对似曾相识的眼睛正悄悄地注视着他,一对迷蒙的黑眼睛,带着股超然世外的韵味。他捉住了这对眼睛,一面迅速地在记忆中搜寻,哪儿见过?猛然间,他脑中如电光一闪,他想起了!那颗小星星!那颗已被他遗忘了的小星星!他顿时有种意外的惊喜,仿佛无意间拾到了一粒被自己失落的钻石。他径直向她骑过去,她站在一大排等车的女学生中间,纤细,瘦小,而稚弱。那样沉静安详地站着,杂在吱吱喳喳的学生群中,显得那么特别和卓卓不群。自从上次舞会中见过一次,已经一个多月了,他奇怪自己怎么会忘怀了这颗小星星?在她面前停下车子,他愉快地招呼着:
“早,杨小姐!”
对方似乎有些局促和不自然,但,接着,她就还了他一个宁静的微笑,轻声地说:
“早。”
“我一直想去看你,但不知道你的地址。”他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他看到公共汽车已经来了,而他不想再放过这颗小星星,“你的地址是——?”
晓彤有些犹豫,她不知道该不该把地址告诉这个男人,而队伍已向车门口移动,许多同校的同学又用好奇的眼光望着他们,使她情绪紧张。魏如峰不等她回答,就肯定地说:
“这样吧,下午你放学的时候我到你的校门口去接你!”说完,他跳上摩托车,对晓彤笑着挥挥手,说了声“下午见!”就发动车子,向马路上直驰而去。他没有管晓彤同意与否,在他说这句话时,他敏感地觉得晓彤百分之八十会拒绝他,像她这样的女孩,一定把约会看得十分严重,因而,他必须在她可能拒绝的话出口前先跑开去。
下午,魏如峰提前回到家里,他一直惦记着下午那个约会,却又记挂着何慕天和霜霜。家中一切静悄悄的,据阿金的报告,何慕天一天没有走出他的房间,而霜霜也一天没有回家。他有些不安了,这情况未免太不寻常。上了楼,他敲敲何慕天的房门,半天,才听到何慕天的一声:
“进来!”
他推开门走进去,室内的窗帘垂着,显得暗沉沉的,何慕天坐在书桌前的安乐椅中,桌上的烟灰碟里堆满了烟蒂,整个房间都烟雾腾腾。何慕天的脸色看来憔悴而寥落,他望望魏如峰,疲倦地问:
“霜霜呢?”
“阿金说还没有回来。”
何慕天不安地蹙着眉:
“她没有去上学?”
“我想是没有。”
何慕天更加不安了。他移动了一下身子,说:
“打电话到顾家去问问看!”
魏如峰正准备去打电话,何慕天又叫住了他:
“如峰,”他沉吟地说,“我有点话想和你谈,”他指指椅子,示意魏如峰坐下。魏如峰不安地坐了下来,心中在为那颗小星星的约会而焦灼。何慕天喷了一口烟,吐了口长气,又沉思了好久,才说“今天,我想了一整天,关于霜霜。她是个失去母爱的孩子,我又不大会做父亲,我只注意到物质方面满足她,而忽略了她的精神生活。说起来,是我对不住她,我到今天才明白她内心的寂寞,而我又没有力量弥补她心底的空虚。如峰,坦白说,我一直有个愿望……”
何慕天的话没有说完,楼下的电话铃蓦地急响了起来,他们同时倾听着,接着,就听到阿金接电话和惊呼的声音:
“老爷,不好了,小姐出事了,警察局来了电话!”
何慕天和魏如峰同时跳了起来,魏如峰立即冲出房门,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楼梯,从阿金手中接过电话,问清了是第×分局打来的,他听完了,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对苍白着脸站在楼梯上的何慕天说:
“没什么严重,姨夫。只是闯红灯,超速,和没有驾驶执照,具个保就行了。”
“霜霜在哪里?”
“现在被扣在第×分局。”
“那么,你赶快去接她回来吧!”
“我现在就去!”魏如峰话才出口,就猛想起和那颗小星星的约会,看看手表,四点整。他知道晓彤大约四点半放学,他希望把霜霜接回来后还赶得及去赴约。于是,他冲出去,跳上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向第×分局赶去。
到了第×分局,一眼就看到门口那辆浅灰色的汽车,走进分局的大门,霜霜正坐在一条长椅子上,大眼睛失神地瞪着门口,头发零乱,脸色苍白,平日的张狂跋扈已一扫而空,反显得十分孤苦无告。看见了魏如峰,她就像个迷途的孩子突然找到了亲人一样,撇了撇嘴,红着眼圈,想哭又竭力忍住。魏如峰走过去,安慰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就和办案人员交涉具保的事。谁知,那些手续竟非常麻烦,办案的警员又絮絮不停地述说霜霜怎样拒捕,连闯三次红灯,出动了他们的摩托车队才把她捉住。又怎样拒绝说出父亲的名字,不肯和警员合作……讲了一大堆牢骚,最后,还愤愤地说:
“我知道何小姐是有钱人家的女儿,超速闯红灯都不在乎,反正有她父亲付罚款,我们也莫奈她何!只是,这样的年纪,整天开着汽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将来出了事,送到少年组去管训可不是好玩的!现在这些不良少年全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吃饱了没事干就在外面招摇生事,给我们找麻烦!我们费了大劲去抓,抓了来,家长一个电话,付了罚款,具个保就算了事,明天又要去抓了!我真不明白,家长为什么不好好教训一下他们呢!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狠揍一顿,关上三个月……”
魏如峰知道这警员说的也是实情,只得苦笑着不加以辩白,霜霜却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好不容易,具了保,付了罚款,魏如峰才带着霜霜走出来。把摩托车放在汽车的后座,魏如峰坐在驾驶位上,霜霜坐在他的身边。他发动了汽车,霜霜一直不说话,魏如峰知道她也受了一肚子的委屈,平常谁要对她说了一句重话,她都受不了,今天警员那样的口气,怎么是她能忍受的?何况她一早和父亲怄了气出去,本来就有满腔心事。这一来,一定更加难过了。于是,他腾出右手来,揽住霜霜,轻轻地拍拍她说:
“好了,没事了,霜霜,都过去了,别放在心里。”
谁知,他这样一说,霜霜反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把头扑在魏如峰的肩上,哭得伤心透顶。魏如峰只得揽住她,拍她,劝她,一面想把车子快些开回家里。可是,霜霜哭着喊:
“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
魏如峰把车子停在路边,用手托起霜霜的脸来,霜霜一脸的泪痕,又一脸的倔强,长睫毛上挂着泪珠,黑眼睛浸在水雾里,反有一股平日所没有的楚楚动人的劲儿。他掏出手帕来,拭去了她脸上的眼泪,安慰地低低地说:
“霜霜,你爸爸在等你,不要让他伤心,好吗?你知道他多爱你,他难得说你几句,你就要生气?”
“我不是生气,”霜霜噘着嘴,慢吞吞地说,“是——为了妈妈的事,我不好回去,我不知道对爸爸说了些什么。”
“姨夫决不会怪你的,你知道。”
“可是一”霜霜抬起睫毛来,看了魏如峰一眼,“我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爸爸骂了我,我就想要他难过,他——”她咽住了说了一半的话,望着驾驶盘发呆。然后,又突然抬起头来问:“表哥,你见过我妈妈?”
“当然了。”
“她是什么样子的?”霜霜痴痴地问。
“很美,是当时著名的美女,你长得非常像她。”魏如峰说,接着就振作了一下说,“好了,这些事就别再去管它了,现在,你好些了吗?来,擤擤鼻涕,振作起来,像你平常那种样子,看你这样眼泪鼻涕哭哭啼啼的,使我都不认得你了。”
霜霜嫣然了,真的在魏如峰的大手帕里擤了擤鼻涕,擦擦眼睛,甩了甩头。魏如峰欣赏地看着她,他喜欢她这股洒脱劲儿。他们相对注视着,都微笑了起来。魏如峰踩动油门,把车子开到马路上。霜霜一直注视着他,大眼睛里逐渐升起一团朦胧的薄雾,她定定地望着魏如峰的侧影,用手拉住他的手腕,轻声说:
“我饿了,我们先到什么地方去吃点东西,好不好?”
魏如峰望着她那泪痕犹新的脸,不忍拒绝。偷偷地看了看手表,五点半!那颗小星星不会等他了。他又失去了一个机会,看样子,和这颗小星星是没有缘分的了。暗暗地叹了口气,他把车子向中华路开去,一面说:
“好吧!不过,我们应该先打一个电话给姨夫,免得他着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