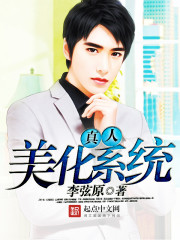明苏真想抱着郑宓永远都不松开, 可是不行,身后众多将士还跪着,殿中皇帝还在,今日发生了这样大的事, 还得善后,那些龟缩在府中的大臣, 也是时候召他们入宫来了。
接下去的事, 既多且杂,少不得耗费心力, 且她到底是逼宫篡位, 拖得越久, 便越易生变, 自然是越快定下越好。可明苏抱着郑宓真的不想放开。
郑宓拍拍她的肩, 柔声道:“去吧。”
明苏缓缓地松了手上的力道, 她退开一些, 望着郑宓, 她的脸上残余着泪水,明苏抬手替她轻轻地拭去。郑宓任由她的指腹在她面容上停留了片刻, 方抬手将她的手握在手心,又催促了一声:“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明苏点了点头, 退开一步,站到她的身旁。
郑宓便直面那数万跪地的精兵,她抬高声音,望向众人, 高声道:“众卿免礼。”
“谢娘娘!”将士们的声音整齐划一,震耳欲聋,他们一齐起身,甲胄的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
郑宓环视众人,容色庄重,带着略微悲伤,沉声说道:“贤妃与五皇子意图谋逆,贤妃在宫中劫持了陛下,屡番伪下诏令,欲与五皇子里应外合,幸而信国公主与众卿奉诏来救,解了宫中之困。”
底下的将士,不通政务的,只当自己当真是追随信国殿下平了五皇子的谋逆,唯有寥寥几名将军心知肚明,公主已是胜者,胜者岂能有污名,谋逆的罪名只能由旁人来背。这是心照不宣的话。
而这些话,除了皇帝,唯有皇后说出方最为名正言顺。
将士们伏拜,齐声道:“臣等万死不辞!”
郑宓便转向明苏,道:“陛下抱恙,不能理政,朝中大事,皆托付公主了。”
明苏领命:“儿臣必不负陛下与娘娘所托。”
话到此处,算是将大权粗粗有了个交接,与了明苏便宜行事之权,但更进一步,还需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方可。
明苏便将大事一件件委派下去,先由京防军接替禁军,守卫宫城,再分出五万大军接手京城四门,而后便是派人将五皇子捉拿,再将几位重臣请入宫来。
分派完后,数万精兵立即散了开去,只留下两队,在紫宸殿外守卫。
明苏与郑宓走入殿中。
淑妃站在大殿一侧,正愣愣地出神,不知在想什么,闻得步履声,她朝殿门望了一眼,看到明苏,先是有些恍惚,而后方有微微的少许笑意。
明苏立即行礼,上下查看她是否安好。淑妃知她担忧,拍了拍她的手,宽慰道:“我无事。在押送至北门的中途,皇后掌控了紫宸殿,命人截住了我,将我带到了这里。”
她没受什么委屈,惊险也只是虚惊一场。明苏这才安心。
淑妃却是细细地端详了她一番。明苏一向在文事上用功,于武事甚少沾染,故而今日是她头一回穿戴甲胄,佩长剑。可这一身软甲,这一柄宝剑穿戴在她身上,竟是意外的适合,使她瞧上去一身的凛然正气。
“真好看。”淑妃欣慰道。
明苏怔了一下,才发觉她在说什么,顿时面上飞红,讷讷的,不知该说什么,转头望向了郑宓。郑宓与她笑了笑,明苏心头滚烫,又觉羞涩,微微低了下头。
“好了,你与娘娘,定还有事忙,我便不添乱了。”淑妃说罢,便出去了,但也没走远,在偏殿守着,以备在她们需要人手时来帮忙。
这段时日,宫里宫外消息不通,两边无音讯往来,明苏与郑宓相互惦记着,如何行事,凭的竟是默契。明苏还有许多事要问,但她也知眼下还不是时候。
“陛下在里头?”明苏道。
郑宓点了头,举步往内殿:“你随我来。”
皇帝已被移到了内殿的软榻上,这软榻原本是他处理政务间隙休憩所用,故而绵软舒适,躺在上头,很易入眠。然而此时,他躺在上头,便似躺在针上一般,愤恨地瞪着守在榻前的无为。
明苏跟在郑宓身后入殿。
皇帝一见郑宓进来,眼中的愤恨骤然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疑惑与他自己都未发觉的惧意。
无为朝二人行了一礼,郑宓点了点头,无为便退下了。郑宓说道:“殿内我命人看守。”
明苏会意,接口道:“殿外有京防军,无你我手令,无人能靠近紫宸殿。”
这是要软禁他?皇帝盛怒,他瞪着明苏,怒斥:“无君无父的畜生!”
明苏却似听不到,镇定与郑宓商议:“大臣们很快便会到了,娘娘最好与儿臣一同去见。”
郑宓颔首。
她二人十分镇定,好似早已将今日之况在脑海中推演了无数遍,皇帝越发地心惊,方才皇后说她是郑宓,皇帝当时惊惧,但静下心来,又想人死岂能复生,必是这贱人哄骗他。
但皇帝却无分毫宽心,今日反的若是明寅或明辰,他都能端住皇帝的架子,可偏偏却是明苏。见她二人自顾商议,丝毫未将他放在眼中,皇帝按捺下暴怒,放缓了声:“明苏,你过来,朕有件事要告诉你。”说着嫌恶地瞥了眼皇后,却好歹压制住了怒意,和声和气道,“你先让她出去。”
明苏却连个眼神都懒得给他,只与皇后说话。
皇帝见哄不住她,又改了口:“你既已在此,想必宫中已是你的了,可你想要名正言顺地掌控朝堂,坐上朕的位置,却少不得朕的首肯,你叫她出去,你我父女好好谈谈,不必闹得两败俱伤的。”
他说罢,明苏仍无动于衷,郑宓却看了过来,淡淡道:“陛下不曾经过宫变吧?”
“贱人!朕不曾与你说话!”皇帝按不住火气,怒喝道。不知无为给他下了什么药,他身子一动都动不得,故而一激动,便唯有面容不住抖动,瞧上去,可笑又可怜。
郑宓不在意他的口出狂言,接着将话说完:“陛下不曾经过宫变,故而不知,到了这关头,陛下是没有发声的资格的。”
皇帝听了这话,怒不可遏,瞪着明苏道:“你便任由她羞辱朕?朕是你的父亲,你体自我出,不论朕做了什么,都是你父亲,血脉不可断!”
明苏微微垂了下眼,苦笑了一下,再抬头时,已是冷然:“她顾忌着我,已对父皇很是客气了。”依郑家与他的仇怨,能容他在此大放厥词,容他好端端地躺在这舒适的软榻上,全是看在她的面上。
皇帝一怔。
殿外隔着门帘响起玄过的声音:“娘娘、殿下,几位重臣已在垂拱殿候着了。”
明苏与郑宓便一言不发地出去了。皇帝转动眼珠,看着她们离开,看着帘子晃动,看着殿外走入两名内侍,那两名内侍也未与他行礼,各自站在门两侧守着。
他便如阶下囚一般,被看守了起来。
听闻明苏率京防军来宫时,他虽慌,更多的却是怒。待被下药,身子动弹不得时,他虽惊怒不已,但也不如何畏惧,更多的仍是暴怒。
哪怕明苏与皇后站在他面前,将他视若无物,他仍旧不如何担忧。他运道一向好得很,九岁那年,父皇驾崩,几位皇叔对皇位虎视眈眈,但郑泓却将他稳稳地扶持上了皇位。
他记得前一日还在他跟前傲慢无礼,使他畏惧的皇叔跪在他面前,称他陛下。于是畏惧,便成了沾沾自喜。
他在郑泓辅佐下读书听政,虽有皇帝之名,却不能为所欲为,他总害怕郑泓会将他取而代之,于是求娶他的女儿。他很是惶恐,因太傅之女很得太傅喜爱,且听闻贤淑博学,容貌绝艳,太傅未必肯将爱女许配。
结果,不几日,郑泓便答允了这场婚事,他又松了口气。
亲政之后,他怕郑泓只是试探,并非甘愿还政,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接触政务,每下诏令,必再三谨慎,欲韬光养晦。
结果他的政令推行得十分顺利,臣下无人阻挠,于是韬光养晦便显得十分多余。他甚是得意。
国舅那事之后,他总怕郑泓会趁机打压他,但他担惊受怕了数月,却是什么都未发生。
又是虚惊一场。
郑泓过世,他再忍耐不得,迫不及待地就对郑家下了手。他想着郑泓如此权重,他的子孙也必是弄权之辈,要拔出郑氏,怕是有一场硬仗,结果没了郑泓的郑家竟是如纸般被轻易撕得粉碎,朝堂上那些自以忠耿的大臣,除了奔走求情,拿出郑泓绝无犯心,郑家绝无二意的证据外,便再无旁的举措了。
他将他们一网打尽,直至案子了解,朝堂上空出了一大片空缺,他才发觉原来覆灭郑家竟是如此容易。
他一生经的事,再如何惊险,到头来也都是虚惊一场,他总能顺顺利利地得到想要的一切。
故而,当明苏攻入皇宫,他都未察觉多少危机,隐隐间仍相信着自己的好运道,想着不必做什么,便能化险为夷。
但听了明苏的那句话,他却突然不敢肯定了,他成了阶下囚,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皇帝突然反应过来,他往后的日子必然极为艰难,他的宫人对他将再无敬意,他会见不得大臣,碰不到政务,被幽禁在某座宫殿。
皇帝骤然心慌,但他却不后悔,也不觉自己何处错了,只是无比怨恨起来,怨恨明苏目无君上,怨恨无为辜负他信任,怨恨大臣们竟是墙头草,天子处危境,竟无一人来救。
被皇帝视作墙头草的大臣眼下正在垂拱殿中听皇后训示。
龙椅边上另设了一座,皇后便坐在此处,对着站在底下的明苏说道:“陛下抱恙,不能听政,三皇子与五皇子接连谋逆,大皇子一向不问世事,四皇子又体弱,九皇子年幼,皆指望不上,朝中大事,天下万民,只好托付公主了。”
这话看似是说给明苏的,实则是说给大臣们听的。
殿中两侧站立着持刀的京防军,殿外禁军已全部撤下,自北门入宫的大臣亲眼目睹了北门外还未来得及收拾的战场。
朝中已无人能与信国殿下相争了。众臣皆跪地道:“臣等必尽心竭力,辅佐公主。”
皇后要说的,便是这一句话,余下的皆交由明苏主持,明苏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众臣仍以民生政务为重,不得乱了日常事务,而后方命中书令审问五皇子与他的一应党羽。
众臣听她的口气,并无株连太多的意思,各自松了口气,皆是俯首听命。
这大抵是最为平稳的政权过渡。
郑宓去了后宫,留下明苏依旧在垂拱殿。
五皇子在明苏率军回京之时,就被关押了起来。他悔得肠子都青了,数日之前,他也想过,禁军与京防两头都在更换将领,他若要在京防营中发动一场兵变,而后率军攻入京城,以京防军的兵力,禁军多半无抵抗之力。
此事他寻思了多日,越发觉得可行,正要着手去做,结果,明寅下狱了。他顿觉眼前开阔了起来,突然间便不急了。明寅下狱,且还是以谋逆之罪,他再无太子的指望了。
那余下的皇子里,便唯有他能担当大任。父皇总不至于连一个有能耐的儿子都不留下。
他安了心,想着不可太过张扬,也不可过于喜悦,以免父皇以为他轻狂,他还约束了门人,要他们克制着些,立太子的诏书下来前,万事皆有变数。
如此暗喜了几日,明苏便将他想做而未做的事做了,她率领京防军攻入皇宫,幽禁了父皇,并将造反之名安到了他的头上。
五皇子被囚禁在刑部大狱中惶恐不已,每时每刻都怕会迎来一杯毒酒一条白绫。
明苏却未如何管他,她只想赶紧将朝堂恢复如常,将皇帝堆积了月余的奏疏都拿来批示。她几乎都忘了她是如何在垂拱殿坐稳的,直至她无意间听到中书令与尚书令私下里交谈她何时会即位,怎么一点动静都无,他们是否该上书恳求公主登基?
她方发觉,原来她篡位篡到一半,还没篡完。
大臣们如此上道,她不觉得欣喜,反而很慌张。宫变已过去五日,她有五日不曾见阿宓了,她知道阿宓在仁明殿,她想过好几次去见她,但总被什么事绊住。
眼见外头已天黑了,明苏忙搁下笔,匆匆地往仁明殿去。
这宫中如今已没有什么她去不得的地方了。到了仁明殿,宫人忙将她迎了进去,但她并未见到皇后。
云桑笑与她奉了茶,道:“殿下稍坐,娘娘正沐浴。”
明苏便安分坐着等。
一旁有宫人悄悄地看她,相互间交头接耳,见她望过去,又忙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明苏好不自在,只觉得如坐针毡,好不容易等到皇后出来,她忙起身行礼。
“公主免礼。”郑宓说道,坐到了她身旁。
明苏坐下了,却是目不斜视,坐得端端正正的。郑宓见她很拘束,便将宫人们都遣退了,直至殿中只剩了她们二人,方柔声道:“怎么这么晚了过来?”
明苏见没有外人了,这才慎重地将目光转到了郑宓身上,一看之下,明苏的眼睛就看直了。
郑宓刚沐浴过,因怕明苏久等,发梢还未完全擦干,只随意地绾起,寝衣外头披了件薄薄的长袍便出来了。
她身上有浅淡的香气,盈盈绕绕的,使人沉迷,她的模样在橘色的灯下,柔婉而勾人。明苏只看了一眼,便连忙转开了头,心跳噗噗直响。
郑宓哪知她这般易心动,只以为她是在前头遭受不顺了,便想安慰她,替她排解一二:“怎么不说话?”
她的声音如此温柔,明苏更是不敢看她,可心又跳得厉害。
她低着头,甚至不敢看郑宓,轻轻地唤了一声:“阿宓。”
这声阿宓唤出,明苏觉得好不一样,仁明殿不一样了,夜晚不一样了,都焕然一新,全然成了心动的背景。
郑宓原是镇定的,可被她这样一唤,也跟着紧张起来,但她于□□上到底较明苏要老练些,还能说得出话,见明苏低着头不敢看她,不由笑道:“你怎如此傻气?”
明苏慌了,忙道:“我不傻气。”她一面说,一面抬头,对上郑宓被水浸过一般的双眸,气势顿时荡然无存,她低下声,乖乖地顺着郑宓,道:“我傻气的。”
郑宓终于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她的脸颊。
作者有话要说:我又来了,又是长长的一章。
特别感谢不知名过客的5个深水鱼雷,船到桥头自然沉的2个深水鱼雷,江蓝生的2个深水鱼雷,阿树的女友粉的深水鱼雷,22461313的浅水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