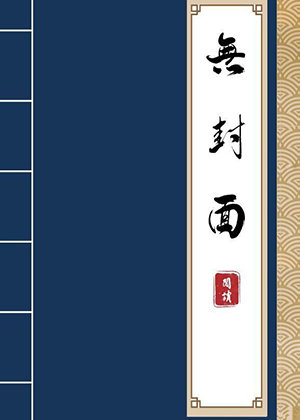韶华错付,情根错种,白山黑水一世诺,心中自定夺。
悲欢一腔,归途不望,劫缘堪破,一株清明雪。
万事从来风过耳,一生只是梦游身。
——《百灵潭·小山》
(一)
小山是百灵潭的战神。
见过她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一个文文弱弱,说话还带点傻气的小姑娘,会使得一手好铜锤,力大如牛,打遍四海无敌手,一人可抵百万师。
虽有战神之名,小山的性子却很和善,还十分古道热肠,但凡百灵潭谁有个三难五急,她都愿意拍着胸脯,提着铜锤,跳出来帮忙。
不过她的援手许多人都无福消受,甚至还避之不及,只因为这小山战神别的都好,就是有些迷糊,往往好心做了坏事,一身猛力更是恐怖得叫人胆寒,大家伙都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她那对铜锤震成个重度内伤。
这日云淡风轻,小山正在坡上练铜锤呢,半空中忽然绽开朵朵幽莲,一道身影踏风而来,墨发如瀑,眸光清冷——
是百灵潭的主人,春妖来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潭主此次而来,是要交予小山一件任务。
“尔力大无穷,在我潭中素有战神之名,此番夷云顶之行,非尔莫属。”
清泠的声音中,小山跪拜于地,受宠若惊地抬起头,接过半空中飘来的檀木匣子,潭主在她耳边接着道:“夷云顶上坐有一人,唤作朽婆,你将这匣子交到她手上便可。三月后北伏天将生异象,记住,你即刻动身,务必在那之前赶到,不得延误。”
个中细节春妖又嘱咐了一番后,拂袖翩然而去,只留下抱着匣子兴奋不已的小山。
微风拂过,郁郁葱葱的一片树林发出飒飒清响,小山头顶的一颗大树上,一袭白衣倚在树间,闭眸养神中,将方才潭主布下的任务一字不漏地听去了。
树下传来女子摩拳擦掌的动静,白衣少年长睫微颤,悠悠睁开眼,眸光深不见底,似是想到了什么。
一翻身,他轻巧跃下了树,在小山的张嘴惊愕中,猝不及防地夺过她手中的木匣,上下打量起来。
“阿七孙儿,哦不,阿七,”小山连退几步,指着少年语无伦次:“你,你又在偷看我练功!”
少年闻言一顿,淡漠抬首望向小山,俊秀的脸庞面无表情,只抛去一个“你想多了”的眼神。
“毫无美感的一对铜锤有何好看?”
还不待小山为自己的爱锤叫屈,少年已经淡淡开口:“若孙儿没记错,姑奶奶似乎曾在百灵潭里迷过路,住了几百年的地方也能走错,诚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路痴,不知潭主怎会放心让你去那夷云顶?”
陈年糗事被揭破,饶是小山一向以粗人自居,此时老脸也不禁红了一红,伸长脖子辩道:“潭主给了我地图的!”
少年一声嗤笑,眸中是毫不掩饰的怀疑:“姑奶奶确定看得懂?”
小山一噎,瞪大了眼正待反驳,少年已经挥挥手,将匣子塞入怀中,自顾自地摊手叹道:“好了,同为宗族,这趟苦差孙儿少不得要为姑奶奶担待了……”
“夷云顶是吗?只好舍命陪君子,勉强同姑奶奶走一趟了,正所谓孙儿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叹息的语气中饱含无奈,继承了父亲伶牙俐齿的孔家阿七,一番话将小山堵得哑口无言,她还未回过神来时,少年已揣着木匣往前走了,没走几步,扭过头来冲她道:
“还愣着做什么,走啊!”
(二)
孔七在百灵潭当得上八个字,家世显赫,天之骄子。
他父亲是孔雀公子孔澜,母亲是百鸟之王乌裳,干爹是上古神兽饕餮千夜,干娘是长白山莲主薛连,还有一对有间泽的神仙眷侣,古木守护者碧丞与茧儿,从小看着他长大,对他疼爱有加。
浮衣还在之时,曾摇着蛇尾笑言道,孔家阿七完全继承了父母所有的精华,一出生,灵光冲天,照亮了百灵潭的上空,他既不像母亲乌裳一样浑身乌黑,也不似父亲孔澜一样五彩斑斓,而是一只纯白的灵鸟——
生来就带有灵力,白得动人心魄,像揉碎了九重天上的祥云,雪白圣洁得纤尘不染。
孔七天资聪颖,骄傲而不自矜,性子恰到好处地综合了父母的特点,既没父亲孔澜那么自恋风骚,也没母亲乌裳那般泼辣,人前有礼有度,不骄不躁,自有一番独一无二的清贵风华。
但要小山来评价她这孙儿,就两个字,狡猾!
听到这评价时,孔七不以为意,对着小山挑眉一笑,笑得意味不明:“若没孙儿的狡猾,哪衬得出姑奶奶的朴实无华?”
说起孔七与小山的关系,活活应了一句话——
辈份这回事,简直就是用来伤人的。
初次见面时,小山笑得一脸灿烂,随手摘下自己两个耳坠,往手心一摊,变出一对铜锤,虎虎生风地朝大树一挥,哗啦啦地震下一地野果。
“阿七孙儿,这是给你的见面礼!”
彼时的孔七仍是孩童的模样,站在漫天果子雨中,却已出落得白衣胜雪,他仰头望着小山,漆黑的眼眸一眨不眨,不发一言。
等到小山席地而坐,撸起衣袖,抓起野果吃得欢快时,孔七仍是站得挺直,小小的身影在树下风姿卓然,与小山的对比颇为鲜明。
小山挠了挠头,觉得这孙子实在有些内向,不够豪爽,但孔澜既然把孩子送到她这来学艺,她就得负起责来,不然可对不起孔澜那一声表姑,虽然只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宗族关系。
于是小山绽开大大的笑容,伸出沾满果汁的手,热情地去拉孔七的衣袖,嘴里还一边套着近乎。
“阿七孙儿,我听人说,你的名字很有来头,孔七,恐妻,是说你爹很怕你娘吗?”
孔七不露痕迹地把衣袖抽出,瞥了眼染红的雪白袖口,长睫微颤,终是对着小山缓缓开口,说了见面以来的第一句话。
“关于这点,你不妨亲自去向我爹求证一番。”
说完,转身离去,一身白衣头也不回,孑然孤傲,隐隐含着莫名的愠怒。
小山坐在树下傻了眼,一张白皙秀气的小脸张大嘴,半天没合上。
她委委屈屈地去找千夜解惑,千夜接过她“孝敬”的美酒佳肴,不客气地大快朵颐起来,酒足饭饱后,红袍一甩,笑眯眯地开口指点:
“第一,你日后唤他阿七便好,什么乖孙儿就免了;”
“第二,他不喜甜食,你震下一山头的果子给他,他也不会看一眼;”
“第三,他虽不像他爹那样风骚,却到底有些洁癖,你莫随便去摸他那白衣就是;”
“第四嘛,”说到这,千夜不厚道地笑了笑,凑近小山耳边:“虽然我也觉得那骚孔雀是只恐妻的鸟,但血脉相连,当面揭人短的话,你日后还是少说为妙。”
(三)
有了孔七的相伴,夷云顶之行异常顺利。
小山这才知道,带上阿七是多么明智的选择,在那身白衣又轻而易举破了一道阵法后,她跟在后面,挥舞着铜锤笑呵呵地道:“阿七阿七,你有巧谋,我有蛮力,咱俩真是天生一对!”
前头的孔七脚步一歪,咳嗽一声后,也不去纠正小山乱用的成语,只唇角微扬道:“姑奶奶所言甚是。”
两人一路过沼泽,穿妖雾,破了九九八十一道阵法,终是到了夷云山脚下。
小山兴冲冲地就要上去,孔七却拉住了她,向来波澜不惊的一张脸微蹙了眉头,欲言又止:“当真要上去吗?”
小山眨着眼点头:“当然了,这是潭主布下的任务,咱们早点完成,就能早点回家了!”
“回家……”孔七神情有些恍惚,掏出怀中的木匣轻轻一转,发出一声似有若无的叹息,再抬头,神色已恢复如常,对着小山一笑:
“早闻北伏天景致秀丽,我们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而来,反正离三月之期还有些时日,也不急着上云顶,倒不若先在山脚住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过些寻常百姓的日子,也算一番凡尘历练,姑奶奶以为如何?”
那语气是难得的温柔,小山听得酥酥软软的,被孔七勾勒的场景迷住了,喃喃道,松花酿酒,春水煎茶,该是多美的画面啊。
她拉住孔七的衣袖,眉开眼笑道:“行,阿七说好便好。”
就这样住了下来,天地做庐,竹林为家,他们还去逛了夷云山外头的城镇,人间的夜市热闹非凡,烟花满天,处处荡漾着祥和的气息。
他们坐在摘星楼的屋顶看星星,靠着彼此饮酒沐风,小山喝的醉醺醺的,嘴里说着胡话:“阿七,为什么这场景那么熟悉?我好像曾经也经历过,只是记不清什么时候了,那时好像只有我一人……”
声如梦呓,却夹杂着莫名的哀伤,连那一向无忧无虑的眉头也皱成了一团,像是做了不好的梦。
孔七凝视着小山酡红的脸颊,许久许久,终是深吸了口气,望向皓月长空,眼眸一片漆黑。
回去的一路上,孔七背着小山,听她在耳边呼吸匀长,身上传来淡淡的酒香。
夜阑人静,空荡荡的街道,冷风呜咽,吹过孔七的白衣黑发,他忽然开了口,声音低不可闻,仿若自言自语:“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年的端阳,你也是这样背着我回去的……”
风中自然没有人回答他,天地间静悄悄的,只有月光流转,似是投下一面水镜,一点点浮现出过往云烟。
(四)
起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孔七都对小山不冷不热的,小山虽是向千夜请教过,却仍是摸不准她那古怪孙儿的脾气,更不知自己哪里得罪了他。
直到几年后的一个端阳节,那时的孔七正处于羽化期,即将褪去稚嫩的孩童模样,长成玉树翩翩的少年。
乌裳为了磨炼儿子,竟狠心将孔七抛下了魍魉渊。
那是百灵潭阴气最重的地方,鬼火万丈的深渊,封印着无数恶灵邪魂,生前全是些十恶不赦之人,死后连佛祖都超度不了,只能囚禁在渊底,相互吞噬,此消彼长,慢慢耗尽冲天怨气。
大风烈烈,孔七白衣翻飞,凌空跌下,众人赶来时,只听到乌裳冲下面喊:“害怕就哭出声叫我来救你,否则就自己张开翅膀飞上来!”
孔澜几步上前,一把推开乌裳,看着已经坠下去的那身白衣,脸色大变。
那是他顶着“恐妻”的名号,头一次冲乌裳发的雷霆怒火:“臭乌鸦,你疯了是不是?下面那么危险你把阿七丢下去,儿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有没有问过他老子,你夫君我的意见?”
千夜与薛连两口子赶紧来劝架,碧丞与茧儿也连忙拉开乌裳,一片混乱的场面中,一道人影霍霍生风,义无反顾地冲了上来,拎着两大铜锤跃下深渊。
“阿七孙儿,姑奶奶来救你!”
声音震耳欲聋,在万丈深渊久久回荡着,众人齐齐探出脑袋,惊声叫道:“小山!”
小山一向勇猛非凡,跳下去的那一刻并未想太多,只想着依她那古怪孙儿的别扭性子,就算被一群恶灵团团围住,咬死了也不见得会哭出声来求助,她不能白白地见娃送死啊。
于是下了深渊后,小山果然看见了骇人的一幕。
不计其数的恶灵如潮水般围住了孔七,贪婪地想要将他吞噬,那身小小白衣幻出一柄羽剑,奋力厮杀着,却还是禁不住一波波袭来的恶灵,浑身已是鲜血淋漓。
小山血气上涌,大吼一声,两个铜锤重重打去,瞬间打散一片恶灵,如天神降临般,护在了孔七身前。
彼时的孔七遍体鳞伤,长睫上还挂着血珠,仰头摇摇欲坠地看着小山,眼前被血雾模糊了一团,耳边只不停回响着小山跳下时那气壮山河的一句——
“阿七孙儿,姑奶奶来救你!”
无法言说那一战有多么惨烈,小山背着孔七,两个大铜锤挥舞如风,硬生生地杀出一条大道。
一步一步,深渊里绽开血莲,染出一地绝美的触目惊心。
孔七伏在那个温暖的肩头,周遭凶险万分,他半昏半醒间,一颗心却是从未有过的安定。
醒来时,床头守着父亲母亲,干爹干娘,碧叔茧姨……连潭主都来了,唯独不见那两个大铜锤。
养伤的日子中,他这才听说,魍魉渊下面,小山一战成名,杀得风云变色,引起了百灵潭的轰动,人们啧啧惊叹,都在议论她的“战神”之名。
小山却到底耗损了太多力气,把他交到众人手上,回去后就开始呼呼大睡,整整睡了十天十夜。
等到小山神清气爽地来看孔七时,孔七已在房中闷了大半月,小山背着他到院中去散风,他在她背上默然了许久,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其实白菜也不错……如果白菜一辈子都是白菜,我就考虑原谅你,怎么样?”
声音极低,像是喃喃自语,却还是叫小山听到了,好奇问道:“原谅我什么?”
背上又是一阵沉默,在小山几乎以为孔七不会回答时,他却幽幽开了口:“你明不明白那种感受?就好比春天播了一颗种子下去,你满心期待,天天跑去看,悉心照料,给它浇水,为它施肥,陪它说话,可等到了秋天,它长出来的竟不是一朵花,而是……”
“而是什么?”
那边顿了顿,终是闷声道:“而是一颗大白菜。”
小山眼睛一亮:“大白菜好啊,我最爱吃大白菜了!好吃又营养,花有什么稀罕的,又不能吃,没开几天就凋谢了,中看不中用,……”
絮絮叨叨的话语中,含了七分安慰,孔七听得嘴角抽搐,无奈又好笑,暖风迎面而来,却是吹散了积压许久的阴霾,漆黑的眼眸望着小山白皙的侧脸,终是浮现出了一抹笑意。
小山却说着说着顿住了,背上的人怎么越来越重了……
她回首一瞥,瞬间瞪大了眼,震惊莫名——
她,她,她的阿七孙儿竟然在她背上羽化成人了,不知不觉褪去了孩童模样,变成了一个翩翩少年!
而那身白衣却还浑然不觉,对上小山的眼眸,唇角一弯,声音已带了少年独有的气息,温柔得似在梦中。
“那就说好了,我的白菜,一辈子都要做我的白菜。”
(五)
见到朽婆时,她坐在霭霭云烟中,守着一道青玉门,鸡皮鹤发的脸孔望向来人,抚上了自己的白发:“该来的总是会来……”
像是对他们的到来毫不意外,朽婆平静如水,只在看到小山手中的木匣时,身子才几不可察地微颤了一下。
她转头看向身后的那道门,眼神绵长而复杂:“北伏天即变,青玉门将开……”
接过木匣前,她竟要他们先听一个故事。
孔七长睫微颤,看了一眼小山,小山却笑眯眯地望着朽婆,好奇地竖起了耳朵,只见朽婆抚着白发,一声叹息:“那是七百年前……”
说是故事,其实不过是仙界帝君,青羽农的一段情史。
青羽农在天帝赐婚下,迎娶了雪域的萧三公主,但他却不爱三公主,他爱着的,是三公主的贴身婢女,涟漪。
这场阴错阳差的婚事,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
新婚那天,三公主独守空房,青羽农来了一趟又走了,只留下一句:“我要娶的人不是你,三公主是有多怕自己嫁不出去,堂堂雪域萧家做此行径不觉可笑吗?”
是他向天帝求的赐婚,送来的新娘却不是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其中萧家动的手脚自是可想而知。
三公主却感到冤枉,黑白分明的眸子望向青羽农,在红烛摇曳间抿紧了唇:“明明是你向我萧家提的亲,你为何不认?”
青羽农冷冷一哼,转身拂袖,踏出新房,头也不回。
此后的漫长时光中,他再不曾踏入三公主的房间。
三公主性子也倔,总不肯服软,就那样看着青羽农一天天冷落自己,却对涟漪好得无微不至。
那时涟漪已不是她的婢女了,而转去伺候青羽农了。
她起初不愿放人,涟漪虽没跟她几年,情分也不深,但好歹也是她萧家带过来的人,而青羽农不仅想让她放手,更想立涟漪为二夫人,与她平起平坐。
她干脆利落地一口回绝了:“恕难从命。”
这门婚事是天帝钦赐,她是萧家的女儿,代表着萧家的颜面,青羽农向萧家提亲的那一刻起,这一生就只可能有她一位夫人,她的地位谁也不能撼动。
却还有个原因深深埋在她的心底,没有人知道,其实她很早以前就喜欢上了青羽农,那个青翼伸展,翱翔天地间,每一片羽毛都漂亮得闪闪发亮的帝君。
她此生从没见过那样美的青鸾,从雪域的上空飞过,云雾缭绕间,带起烈烈长风,高贵清傲得不可一世。
她当时惊呆了,尚是人间十来岁的小丫头模样,拉过身旁的奶娘,指着长空兴奋不已:“大鸟,大鸟飞过去了……”
奶娘吓得赶紧去捂她的嘴:“哎哟,我的三公主,可不能乱说,那是帝君,北伏天的帝君青羽农!”
她眨了眨眼,望着青鸾消失的方向,嘴里喃喃着:“青羽农,青羽农……”
像是鬼迷了心窍,隔天她就画了一张像,拿去给奶娘看,眉开眼笑地问:“像不像他,像不像他?”
未了,她叹了口气,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奶娘见她怅然若失的样子,故意打趣道:“公主你是雪域白驼,人家帝君是青鸾神鸟,一个地上跑的,一个天上飞的,八竿子打不着一块,哪还有机会再见?”
她不死心,天天跑去仰头望天,只盼那道青影能再次飞过雪域的上空,大哥二哥都笑她,说小妹情窦初开了,不仅害了单相思,还单相思上了一只鸟。
她也不恼,只娇憨地笑,才知书中写的一见倾心,原来是那般奇妙的感觉。
如此年复一年,她从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终是等来了那道青影。
却是眼睁睁看着他从空中坠下,华美的翅羽伤痕累累,巨大的身躯跌在了雪地里,奄奄一息。
她急忙奔了过去,雪地里的青鸾已幻化成了一个青衣男子,墨发薄唇,满身血污。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他的面容,比她在心中勾勒了无数遍的模样还要好看。
他被大火灼伤,眼睛也看不见了,躺在她怀里气若游丝:“送我,送我回……北伏天……”
她心跳如雷,急得眼泪都要流下,还来不及叫人,已被出来寻她的奶娘看见了,吓得大惊失色。
奶娘捂住她的嘴,叫她千万不可声张,她这才得知,原来仙界发生了那样大的事情。
大家都不忍告诉她,就在她痴痴等待的这段日子中,她心心念念的帝君青羽农叛离了仙界,做了人人不齿的叛徒。
他投入魔道,不知与魔道少主达成了怎样不可告人的交易,助魔道一路杀上南天门,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
瞧青羽农如今这遍体鳞伤之状,定是在此番仙魔两界大战中受了重伤,飞过雪域上空时,支撑不住坠落下来。
这烫手山芋萧家怎么敢管?不交到天帝手上已是仁慈,怎么可能还放虎归山,将他送回北伏天?
奶娘对她道,只将青羽农送出雪域,不牵扯到萧家,自生自灭就是了,万万不可惹祸上身。
她抱着彼时已昏迷过去的男子,心乱如麻,咬咬牙,做了生平第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定。
(六)
青羽农终是将涟漪要了过去。
三公主从没想过,为了从她手中要走涟漪,那身青裳竟会对她扬起利剑。
他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冷得直透人心底:“若未记错,你先祖乃武将出身,神勇非凡,你萧家世代也是骁勇善战,我们不妨来比试一场。”
“你赢了,我二话不说,从此绝口不再提要人之事;若我赢了,你也二话不说,立刻放人,如何?”
三公主脸色一点点煞白,青羽农却一拂袖,露出身后一排兵器。“这里的神兵利器任你挑选,我也可让你三招,怎样?”
满室冷凝的气氛中,涟漪站在一旁,与青羽农四目相接,眸光盈盈若水,我见犹怜。
三公主别过头,紧咬下唇,不愿再看。
袖风疾扫间,她越过那道青影,利落地挑起一杆长枪,转过身手腕一个漂亮的翻转,对准他,竟是笑了。
“你当知我萧家风骨,即便你是我夫君,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他也冷冷一笑:“如此甚好。”
长枪利剑,白衣青影,就此一触即发。
底下的仙仆们看得目瞪口呆,叫一声帝君,又叫一声夫人,却终究无人敢出口阻止。
半空缠斗间,三公主心神却恍惚起来,仿佛还是那年的冰天雪地中,她变回白驼之身,驮着昏迷不醒的他一步一艰难,在大风里踽踽前行。
她到底舍不下他,她不忍看他自生自灭,趁奶娘转头回去放药箱,她咬咬牙一把背起了他,现出了原形。
前路茫茫,不管如何艰辛,她也要倾一人之力,送他回北伏天。
那段路是从未有过的漫长,风雪中,她温暖着他,源源不断地为他灌输着真气。
他时醒时昏,一双眼看不见,只能下意识地抓紧她的皮毛,在她背上迷糊呓语。
两颗心贴紧彼此,那他们此生靠得最近的距离。
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她好不容易护送着他抵达了北伏天的边界,却被大哥二哥追了上来,一片混乱间,她连句道别都来不及和他说,只能匆匆放下他,被大哥二哥强扭了回去。
回到雪域后她被关了禁足,不久就听说了青羽农为仙界立下大功的事情。
原来一切只是一场局,青羽农并未背叛仙界,投入魔道只是卧底,只为将他们引上九重天,助天帝一网打尽。
他那日受伤坠下,其实是因为在仙魔大战中倒戈,为狂怒的魔道少主所伤。
等到大战结束后,天帝才发现青羽农已回到北伏天养伤。
中间这一段插曲却是谁也不知。
恐怕连青羽农也是稀里糊涂的,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她救过他,不知道她驮着他一步一步走出大风雪,不知道她是以怎样的一颗心爱着他……
他通通不知道,而她,也再没有机会问出口。
嫁过来时她满心憧憬,原本想告诉他的,可一腔柔情还来不及出口,已被他冷入骨髓的一番话打下深渊。
她其实多想对他说,她喜欢他很久了,从懵懂的少女时期就开始喜欢了。
她千里迢迢嫁到北伏天,有好多话想和他说,她想和他好好过日子,她会努力学着做个贤妻良母,她还想和他开玩笑,谁说地上跑的和天上飞的就不能在一起……
可一切都像个荒唐的噩梦。
他那样待她,视她如蛇蝎毒妇,比待陌生人还不如,她所有幻想顷刻间破灭,所有话也都不能说出口。
她的心不是铁做的,不是任他刺上千百刀也不会痛,她也有自己的傲气,即使她再喜欢他,也容不得他肆意践踏她的尊严。
于是外人见到的他们,便是针锋相对,相看两厌的一对怨侣。
他嘲讽她无一丝女子温柔,她冷冷回敬:“只是你没看见而已。”
他说她舞剑招招毒辣,对敌时一定像个女阎罗,她面无表情:“彼此彼此。”
日子就在这样的唇枪舌战中度过,谁也不甘示弱。
可这一次,她却败了,败得彻彻底底。
当手中的长枪携风刺出时,青羽农不及闪避,她瞳孔皱缩,手一偏赶紧收势,她知道他那有处旧伤,是当年仙魔大战留下来的,可还是为时已晚,一道人影凌空飞出,堪堪挡在了青羽农面前——
竟是满脸急色的涟漪!
长枪刺入肩头三分,鲜血四溅,青羽农脸色大变,一掌击开震住的她。
还未回过神来,她已如断线风筝,直直坠地。
先落地者输,他胜了。
可却胜得咬牙切齿:“萧家多悍妇,此话果真不假。”
她眼睁睁看着他抱着昏迷过去的涟漪头也不回地走了,只手撑地间,她喉头翻滚,终是再也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不知伤了经脉……还是伤了心。
她独自在院里养伤,听闻青羽农天天守在涟漪床边,不眠不休地照顾她。
她心头酸涩,却对身边人强颜欢笑:“不过才三分力,哪伤得那么重?”
无心的一句话传了出去,青羽农隔天就来找她了,眸中恨意汹涌:“竟不料你狠毒至此!”
她反应过来后,冷笑不止:“我连说句实话的地位也没了吗?”
青羽农一下目眦欲裂,像是下一瞬就要扑上来掐死她:“你往那长枪上抹了何种奇毒?圣医昨日才查出,难怪涟漪总醒不来,你原是想毒死我的罢,可怜涟漪无辜受累,你这毒妇快交出解药!”
她瞬间如坠冰窟,懵在了原地。
此后不管她如何否认,如何辩解,青羽农乃至整个北伏天的人都不信她没有下毒。
她恶名昭著,死也不肯交出解药,青羽农差点让她为涟漪殉葬,所幸最后妙手圣医研制出解药,才治好了涟漪。
而她的恶毒名声却是甩不掉了,在北伏天被传成了连自己夫君都想加害的毒妇。
没有人相信她,她最后也不争了,只看着躲在青羽农身后瑟瑟发抖的涟漪笑,笑得残忍至极:“你最好祈求帝君日日夜夜带着你,否则难保我寻得一丝机会下毒,也不枉费我白担了个虚名。”
说完她转过身,神似癫狂,大笑着扬长而去。
(七)
故事听到这,孔七沉默不语,小山却已气得挥舞着铜锤大叫:“我要是那三公主,一定把他们两个捶飞到天边去!”
朽婆笑了笑,浑浊的眼眸望向长空:“谁说不是呢,可那时的三公主那么傻,孤零零地一个人远嫁到北伏天,没有人待她好,她有苦也无处说,直到那一次……”
那是三公主最不愿想起的惨痛回忆,她接到消息,雪域遭宿敌寻仇,外族入侵,战火纷飞,向北伏天发来求援。
她惊惶失措地去找青羽农,放下所有身段,急得眼泪都要流出,求青羽农带着人马与她一同去增援雪域,救救她的父兄族人。
事关紧急,青羽农虽不喜她,也不敢怠慢,当即便要动身。
却在这时,涟漪那边传来喜讯,她怀上了青羽农的孩子。
她那时虽还有三公主压着,得不到名分,但实际地位已俨然是北伏天之母。
帝君有后这般的大事简直是普天同庆,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三公主却是心急如焚,她不断催促青羽农动身,甚至不惜低下头去求涟漪。
就是这一次相求,求出了意外。
三公主本是好言好语劝说,却到底被涟漪不愠不火的态度惹恼了,争执拉扯间,不知怎么,竟把涟漪的孩子撞没了,青羽农赶来时,只看见地上一摊血,触目惊心。
涟漪哭得昏死过去,三公主脸色煞白,不停摆手:“我没有推她,我没有推她,是她……”
话还未完,却被震怒之下的青羽农一记耳光打去,红了半边脸。
“你萧家的命是命,我孩子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嘶声怒吼中,青羽农抱紧涟漪,再不看三公主一眼。
战事越来越急,三公主什么也顾不上了,连夜跪在门前磕头认错,磕得额头鲜血渗出,斑驳了门前玉转。
她哭着求他,不再连名带姓地叫他,而是第一次叫他“夫君”,叫得撕心裂肺:“夫君,求求你,求求你带兵同我去救人,求求你……”
从来没有人听过那样凄厉的哭喊,她哭得嗓子都哑了:“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是十恶不赦的毒妇,我该千刀万剐,等救了人回来我任你处置……”
直到最后一刻,那扇门也没有打开。
在北伏天所有人复杂万分的目光中,她血红了眼,终是绝望地仰天一声长啸,跌跌撞撞地奔回去换上戎装,束了发别了银枪,以遇神杀神遇佛*的姿态,一人一马地奔出北伏天,赶往雪域战场。
她不会再哭了,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既然他不肯出手相助,那么她的族人就由她自己来救,哪怕死在战场上!
可她连浴血奋战的机会都没有——
等日夜兼程地赶到雪域时,她只见到断壁残垣,尸横遍野,昔日繁华的城池一片死寂,她萧氏全族已尽数被灭!
她几近虚脱,却疯狂地去白骨堆里找寻她父亲母亲,大哥二哥的尸首,她最先看到了一具女尸,那个从小疼她到大的奶娘血肉模糊地躺在尸堆里,惨不忍睹。
她心头狂跳,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知道机械地把族人们的尸体拖出来,一具具摆好,摆到满身血污,指甲里全是血泥也浑然不觉。
直到一只手把她拉开,回首望去,只看见青羽农沉痛的一张脸,他铠甲森然,身后是一片黑压压的大军。
他终究赶来了,却来得太晚。
她眨了眨眼,眼前蒙了层血雾,看不清他的身影,但那麻木的痛感却是一点点迟钝地复苏。
她甩开他的手,转身摇摇欲坠地继续去拖尸体,嘴里一边念叨着:“我要找我爹娘,找我大哥二哥……”
风雪中她的身影单薄不已,一袭戎装已血渍斑驳,几缕乱发贴在脸颊边,是从未有过的凄惨模样。
青羽农终于看不下去,喉头哽咽,大手强硬地拉住了她,用力地将她搂入怀中。
那是他第一次抱她,下巴抵在她头顶,是心与心贴得最近的时候。
可她只安静了一瞬,下一刻,彷如狂风暴雨来袭,她疯了似地一把推开他,目呲欲裂。
长发被大风吹散,死寂的战场响起了歇斯底里的哭声,她不管不顾地扬起银枪刺向他,凄厉的哭喊划破天际。
“我当年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不让你死了才好!”
那些积压在心底不敢说出来的话,那些被岁月长河掩埋的过往,那些经年累积刻入骨髓的恨意……在这个血染的大风雪中,统统彻底剥落揭开,化作无数利箭,齐刷刷地刺向青羽农。
他无力招架她的猛烈攻势,越听手越抖,直到煞白了一张脸,踉跄地跌跪在地,被她一枪横在脖子上,身后大军失色。
他终于开了口,仰头望向她,浑身抖得不成样子:“当年救我的……不是涟漪吗?”
(八)
那年在北伏天边界放下青羽农后发生的事情,三公主可能永远不会想到。
她前脚刚跟着大哥二哥一走,后脚半空就跃出了一道人影——
正是在暗处跟踪了他们一路的涟漪。
那时的涟漪才进雪域为婢不久,柔弱温婉的面容下,谁也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她其实是个探子,是个外族派去埋伏的探子,从一开始被安插在雪域中,就处心积虑地只为覆灭雪域的那一天。
她等三公主一走便现出身形,眸光深不见底地停在了青羽农面前。
她将他安置在一处山洞中,悉心照料,为他养好了眼伤。
青羽农睁开眼的那一天,只看到一团光晕中,涟漪温柔的笑脸。
他只道她冒着重重危险,一路护送他来到北伏天,对她感激不尽,情根深种。
他们相拥在一起,定下了终生,他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抿嘴浅笑,并不回答,只从怀中掏出了一对耳坠。
“我来自雪域萧家,帝君日后可携此信物前来提亲。”
耳坠是三公主掉落在途中的,涟漪收了去,心生一计。
而后来事情的演变,也的确如她所料,天帝赐婚,她服侍着三公主远嫁北伏天,开始一段纠缠不清的局。
青羽农成功地相信是萧家仗势欺人,从中做了手脚,硬将三公主塞给了他。
于是她看着他们日日冷战,针锋相对,误会越滚越大,打成了死结,解也解不开。
三公主孤立无援,心思又实在,没那么多弯弯绕绕,怎会是涟漪的对手?
她一边将三公主逼至绝境,一边与本族私通密函,只等着雪域覆灭的一天。
终于,万事俱备,战争一触即发。
当三公主去求青羽农出兵相助时,涟漪也恰好地“怀孕”了。
青羽农根本不知道,所谓的孩子,所谓的流产,其实统统都是假的,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小小术法,却将三公主最后的希望,将雪域唯一的生机利落斩断,毫不留情。
但涟漪的败露也来得那么快。
当她听到青羽农抱着三公主的尸体去了百灵潭,找潭主春妖借昆仑镜一窥往昔时,她心跳如雷,明明应该是功成身退,及时抽身的时候,她脑中却尽是青羽农那张俊美的脸,她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连夜赶赴了百灵潭。
高台之上,昆仑镜浮于半空,那身青裳抱着死去的三公主情难自已,悔恨莫及。
涟漪赶到时,一下捂住了嘴,身子委顿在地,泪水夺眶而出。
她从没见过青羽农那样绝望的神色,那双漆黑的眼眸望着她悲痛欲绝:
“涟漪,百年夫妻,你骗得我好惨!”
(九)
三公主是死在青羽农怀中的。
这些年的心力交瘁,满族被灭的惨重打击,陈年旧事的荒谬揭开……种种不可承受之重,终是将她逼至了生命的尽头,她口吐鲜血,倒在青羽农怀中,长发散了一地,是凄美到哀凉的场景。
她在大风雪中伸出手,颤抖着抚上青羽农泣不成声的脸,她虚弱地笑着,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再也不要遇见你……”
百灵潭,风声飒飒。
三公主的鲜血滴上了昆仑镜,缓缓开启了前尘往事,那些青羽农曾经错失过的画面。
白驼背着他穿过风雪,跋山涉水,他们紧紧挨着彼此,她在他耳边不停念叨着:“别怕,我会送你回去的,我会送你回北伏天的……”
声音那样温柔,和她后来对他的冷冰冰截然不同。
他忽然想起,他曾嘲讽她无一丝女子温柔,她只是冷冷回敬:“只是你没看见而已。”
是啊,只是他不曾看见,她曾缩在空无一人的新房里,泪湿了枕巾,死死咬住唇,是用怎样一颗心爱着他。
赶来的涟漪惨白了脸,一下委顿在地,再也无从抵赖。
她哭着求青羽农的原谅,泪如雨下中,迟来了多年的真相终于大白,包括三公主遭受的那些算计陷害。
原来涟漪也早已不知不觉假戏真做,同三公主一样爱上了青羽农。
纠缠不清的一场局,绕进了别人,也绕进了自己,纷纷扰扰直到此刻才彻底了结。
青羽农怒吼着抬起手,欲自涟漪头顶毙下,浑身却止不住地颤抖,红了双眼,如何也下不去手。
无数情感汹涌漫上他的心头,这些年的花前月下,这些年的朝夕相伴,即使是一段不应存在的错位岁月,可他却早已付出了整颗真心,视涟漪为妻,爱入骨髓。
命运弄人,他本该爱着的是三公主,可却在一开始就爱错了人,这一错……就再也回不了头。
“这一世我们都对不住她,纵然你欺我骗我负我,无情践踏我拱手送出的真心,我却仍要为你,为她……做这最后一件事。”
像是心灰意冷了,又像是放下一切了,青羽农竟在涟漪婆娑的泪眼中笑了起来,他抱住三公主的尸体,仿若自言自语。
我辜负了你那么多年,如今唯一能做的也只有那一件事了。
上穷碧落,还救命之恩,还冷落之愧,还他与涟漪这一世的累累亏欠。
“不!”
涟漪满脸泪痕,惊觉出声,却已来不及了,只见漫天荧光间,青羽农义无反顾地剥落下了自己的羽衣,在撕心裂肺的痛楚中,将毕生神元汇入了三公主的体内。
三公主被青色的光晕包裹着,缓缓飘进了青羽农剥落下的羽衣中。
她将开始一段漫长的凝魂重生之路。
青羽农在将三公主托付给春妖前,亲手为她戴上了那对耳坠,低沉的声音满怀歉意地开口:
“今生蒙你错爱,伤你体无完肤,愿你结魄新生后,忘却一切,彻底解脱,重遇相守相依之人,白头到老,一世平安喜乐,永不再被辜负。”
涟漪哭得撕心裂肺,疯狂地想冲破结界,却只得青羽农最后深深的一眼。
那一眼,墨眸如许,是浓烈到极致的复杂情意。
大风烈烈中,他说,涟漪,珍重。
(十)
青羽农的魂魄归往了北伏天,封于青玉门后,等待着休养千百年后的神元复苏。
这千百年来,有一道身影守在青玉门外,从不曾离开过。
烟海缭绕的夷云顶,朽婆泪湿衣襟,拂袖一抛,将木匣抛上半空,打开了青羽农那留在百灵潭守候三公主的最后一缕魂。
风云变色间,天地间大风烈烈,北伏天生异象,青玉门即开——
沉睡了千百年的青鸾帝君就要复苏。
一片地动山摇间,小山头痛欲裂,拼命捂住耳朵,但朽婆的声音仍直直穿透她的心间,前尘往事纷沓而来,像将灵魂生生撕裂一般的痛楚。
“三公主,你全都想起来了吗?你不是百灵潭的小山,你是萧山,雪域萧家的三公主。”
而她也不是朽婆,她是涟漪,那个守在青玉门外,守过最美好的年华青春,用一生来忏悔的涟漪。
伴随着阵阵轰隆之声,大门缓缓打开,青光四射……
没有人注意到,孔七痛苦地闭上眼眸,且叹且退,白袍凄然转身,悄无声息地离去了。
这一路相伴终是结束了,即使他如何不舍,如何不愿,如何不想登上云顶,她也终是要离开她了。
她不属于他,他连故事里的配角也不算,他充其量不过是她生命中的一道流星,稍纵即逝后就要黯然退场。
如果不是当年在百灵潭的青鸾羽衣中多看了一眼,也许他就不会和她生出日后那诸多牵绊。
那时他尚年幼,家中忽然多了一团散发着青光的羽衣,高高地悬浮于花房中央,如有间泽的灵茧一般,层层密密,里面不知包裹着什么。
他好奇不已,问父亲里面是什么?
父亲想了想,摸着下巴笑得神秘,凑到他耳边道,是花,是世上最好看的花。
父亲无心的一句玩笑却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从此他天天跑来看“花”,陪“花”说话,等“花”长大。
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他的花是开在羽衣里的花,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花。
是只属于他一人的花。
带着这样的小心思,他满怀憧憬地等着花儿绽放,可有一天他再去看时,那团羽衣却不见了,他的花儿不见了!
他急得不行,跑去找父亲,父亲告诉他花儿没有消失,只是被潭主取走了,因为时辰到了,羽衣中的人要出来了。
父亲说得很隐晦,他似懂非懂,问那是花儿要绽放了吗?
父亲顿了一下,摸着下巴缓缓道:“要这样说也行。”
于是他又欢天喜地地跑走了,他想着等花开后,潭主就会把花还给他。
可等啊等,不知等过了多少春秋,他望眼欲穿,等到的却不是世上最好看的花,而是——
挥舞着两个大铜锤,能吃能喝,力大如牛的小山……姑奶奶!
当父亲指着那道凶猛捶树的身影对他道:“喏,那就是羽衣里的人,也就是你小时候养的花花。”
他如晴天霹雳,天旋地转间,瞬间被劈焦在了原地。
她怎么可能是他的花?绝对搞错了!
直到被父亲送去小山姑奶奶身边学艺很久后,他还是不能接受那个事实。
他对她冷言冷语,厌恶不已,在他幼时的心中,她就是棵粗鄙不堪的大白菜,破坏了他童年所有的美好幻想。
但就是这棵大白菜,率真地一点点打动了他的心,更是在他身陷魍魉渊下时,奋不顾身地扑下来救了他。
“阿七孙儿,姑奶奶来救你!”
她背着他,两个大铜锤挥舞如风,硬生生地杀出一条大道。
一步一步,深渊里绽开血莲,染出一地绝美的触目惊心。
他伏在那个温暖的肩头,周遭凶险万分,他半昏半醒间,一颗心却是从未有过的安定。
后来她来看他,背着他到院中散风,他在她背上默然了许久,忽然想通了。
“其实白菜也不错……如果白菜一辈子都是白菜,我就考虑原谅你,怎么样?”
他听她说白菜的好处,听得闷笑不已,却像一阵暖风迎面吹来,吹散了他积压许久的阴霾。
他浑然不觉地在她背上羽化成人了,对上她惊愕的眼眸,唇角一弯,声音已带了少年独有的气息,温柔得似在梦中。
“那就说好了,我的白菜,一辈子都要做我的白菜。”
可那时多傻呀,一心以为不会有人和他抢白菜,他能一辈子守着白菜。
直到无意间翻看到了阁楼的宗族史册,他才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要叫小山表姑了。
原来她竟是帝君青羽农的妻子,青鸾神鸟,与他父亲的孔雀一脉是同根,按辈分来,青羽农是他父亲的表叔,所以小山才是他的表姑奶奶。
他这才知道,原来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山是不属于百灵潭的,甚至……根本不属于他。
她有自己的故事,有那样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故事里没有他,过往里没有他,她此后的生命里也不会有他。
他合上卷宗,滑坐在地,生平第一次落下了泪。
真是不划算的买卖呐,他不过陪她一程,她却在他心里霸占一生。
(十一)
孔七在黯然行至半山腰时,忽然听到身后一声叫唤:“阿七阿七,等等我,我们说好一起回家的!”
猛然转过身,他瞪大了眼,竟看见小山拎着两个大铜锤,眉开眼笑地朝他奔来。
“你,你不是……”孔七指着小山结巴起来。
小山一把勾过他的肩,笑眯眯地道:“不是什么?咱们不是说好送了木匣一起回百灵潭吗?”
长风掠过浮云,小山长发飞扬,喃喃道:“终归是帝君说得对,前尘往事,纷纷扰扰,爱着他的是萧山,被他辜负的也是萧山,而重获新生的小山却不必记挂……”
到底是放下了执念,前尘太痛,痛得她只想忘却,在青玉门大开的那一瞬间,无数记忆闪过她的脑海,她第一个想到的人不是青羽农,竟是与她在百灵潭朝夕相处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孔七!
她想起了她还在羽衣中的时候,曾有个傻瓜,把她当成了一朵花,每天都来陪她说话,一陪就是好多年;
她想起了他们初次见面时,风吹林间,一地野果的树下,他白衣墨发,薄唇紧抿,一身纤尘不染,好看得不像话;
她想起了他时常伶牙俐齿地堵得她说不出话,却会在半夜提着灯踏入丛林深处,没好气地捞出她这百年不变的路痴;
那年端阳节的魍魉渊下,她背着他一步一步杀出重围,早已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付出,而那时不谙情事的她却还浑然不知……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许多东西不知不觉地生了根,在她尚懵懂不察时便已牢牢霸占了她整颗心,再不能挥去,只待那迟钝的心在有朝一日被重新唤醒。
和风轻拂,小山深吸了口气,拉着孔七,眉眼间竟多了几分小女儿的娇态。
“咳咳,阿七啊,既然我和那青鸾帝君再无瓜葛了,那么咱们婆孙关系是不是也得从头开始?”
从哪开始呢?就从自我介绍开始吧。
蓝天白云下,两人望着对方傻笑,四目相接间竟都绯红了脸颊。
还是小山挠挠头,笑呵呵地先开口:
“小山,我叫小山,力气很大,会使铜锤,打架很厉害的小山。”
孔七弯了唇角,漆黑的眼眸粲然若星,一袭白袍纤尘不染,一字一句的话语久久回荡在风中,他说的是——
孔七,我叫孔七,不羡鲜花,只爱大白菜的孔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