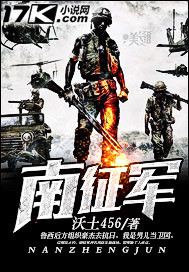好在张野还有自制力,做贼般悄悄地退出了舞伴的客厅,给她悄悄关上了门。
张野昏昏沉沉地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开门的时候,平儿一眼就看到了张野颓废的样子,埋怨说:“心里不高兴,散散心就算了,别这么晚回来。”
张野把脚伸进平儿端过来的洗脚水里,耷拉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平儿说:“人生哪里没有沟沟坎坎,使使劲也就迈过去了。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像个男子汉,亏着是临时下岗,要是长期下岗,还不把你愁煞。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把心放宽点!”
张野钻进了平儿舒适的被窝里,满脑子还是旋转着刚才在吴皎洁家里,看着躺在旁边的平儿,对着她的耳朵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真对不起你。”
平儿回过头来,劝着他:“这不是你的错,哪个单位不是这样。领导不是说了么,下个月就安排你的岗,不要这么想不开!”
张野回过头去,背对平儿,再也难以入睡,总觉得自己是个贼,而且是个可耻、可恶、可恨的家贼。张野回过头去,看了看平儿,平儿也没睡,她埋怨着张野:“我看你今晚上是睡不着了,睡吧,睡吧!”伸出手来,像哄孩子似地拍打着张野。
可是张野哪能睡得着,他想着,自己和平儿是在当知青时恋爱的,有一次耪地,自己只顾倒退着走,扑通一声掉到了井里,是平儿伸出了锄,把自己拉出了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以后在小县城里和平儿结了婚,在产房里,自己亲眼目睹了平儿在呼天抢地,与死神搏斗中,在即将分娩的那一时刻的痛苦表情,女人是以生命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家庭。
为了能从小县城里调回老家,两口子一次次商量,一次次实施,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努力,耗费了多少心血和体力,才在城市安了一个小小的窝……
琢磨过来琢磨过去,现在的平儿是什么,已经是自己的一根腿或者一条胳膊,平时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一旦割去,那将是难以忍受的痛苦,终生的残疾,整个家庭会瞬间崩坍。
张野觉得再也不能跳舞了,进了舞场,吴皎洁就像一股魅力无穷的抗拒不了的巨大漩涡,非把自己漩进去不可。一天,两天,三天,张野坚持着不去,可是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在骨头缝里跳着,跑着,咬着,钻着,非要寻找跳舞的感觉不可。
一到晚上8点,电视剧看不下去,书也不愿意读,和妻子孩子说话也少心无肝。平儿说:“看你难受的,这几天怎么不去跳舞了。”
“跳舞跳烦了,老想陪陪你说说话。”
“老夫老妻的,哪有这么些话,有什么悄悄话,跳舞回来再说也不晚。要是不锻炼,又要长肉的。”
张野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那我就去了,早去早回来。”
张野害怕碰到吴皎洁,多走了几步,到明星歌舞厅去跳。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扫了一圈,并没有看到吴皎洁的影子,这才放了心,随便邀了个没伴儿的女人跳舞。由于心里没有任何负担,舞能放得开,优美的舞姿使不少跳舞的人刮目相看,啧啧称赞。
张野接连和她跳了四个舞曲,直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舞伴问:“你的舞领得真好。我姓李,叫李莉,先生贵姓?”
“瞎跳,瞎跳,免贵姓张。”
“先生在哪里上班?以前没来过这里。”
“胡混呗,下岗职工。”张野和她跳到舞厅角落的时候,忽然看到吴皎洁脸色苍白地站在一边,浑身气得直打哆嗦。张野心里一颤,她怎么找到了这里?
舞曲一停,张野不好意思地坐到了吴皎洁身边。吴皎洁也不说话,紧咬着嘴唇,眼里含着泪。舞曲响起来的时候,张野一伸手邀她,吴皎洁还是纹丝不动,张野拉住她的手,把她拉起来。在缓慢而低沉的舞曲中,吴皎洁瞪着张野的眼睛问:“她是谁?你是这样对待感情的吗?我看到她想勾引你,而你却在想着如何把她抱上床。”
张野解释说:“和她刚认识,怎么会呢。”
“你为什么好几天没去飞天?”
“我不是有事吗!”
“有事为什么今天能来?不在老地方跳,为什么又换到这个地方跳?”
“我……我……换个地方新鲜。”
“分明是你在和她约会。男人的花花肠子,我算是又一次领教过了。”
张野没有向她再解释什么,吴皎洁也没有再问什么,两个人就这么别别扭扭地舞着。
舞会结束了,人们纷纷往外走去,张野自作聪明地对跟着的李莉说:“你对象怎么没来?”
李莉说:“嗯,没来,他没来。”张野又对跟着的吴皎洁说:“我什么时候能再和你跳个舞呀?”
吴皎洁鼻子哼了一声,没言语。走出了老远,吴皎洁看着没有别人才说:“张野呀,我又一次看到了你的卓越表演。你对她说,你对象怎么没来啊,是说给我听的。意思是她对象天天来,你和她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耍这些小聪明,也露出了你的马脚,你和她跳了不是一天的舞了。你说什么时候能和我跳个舞呀!是说给她听的,表白我们之间是初交,没什么关系。你呀你,我算真正地认识了你!”
张野心里觉得,和吴皎洁做舞伴儿,太累!这个人,太精!这个舞是不能跳了。
张野竞争上岗后,从此不跳舞了,停了十多天,吴皎洁把电话打到了张野单位上,说有事要和张野谈谈,张野说:“下了班,我还有酒局,实在没有时间,对不起了!”以后吴皎洁又打来几次电话,都让张野婉转地推辞了。
有一天,下起了雨雪,张野穿着雨披,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往家奔,刚出厂不远,见吴皎洁打着雨伞挡在那儿。张野只好下了车推着走,吴皎洁和张野并排走着,讥诮地说:“你成天忙,今天又是雨又是雪,我看你还忙吧!”
张野看着她瘦俏的身子几分发抖,苍白的脸在刺骨的寒风中吹得有些发红,心里真有几分感动。吴皎洁喃喃地说:“你这是玩弄感情。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你,我什么都没了。你也知道,我对象的心不在家里,不在我身上,我还能指望谁呢?”
张野叹了一口气:“我同情你,但我帮不了你的忙,我想,得维护好家庭。”
“那……你为什么上我家里去呢?我男人不在家,那就说明你有这个想法!”
“对不起,真……对不起,我只是一种好奇,想上你家里看看!”
“真是的,真不懂得人的感情。这么着吧,咱们以后交往,我发誓绝不会破坏你的家庭。”
“以后咱们很危险,早早晚晚有惹事的时候。这个舞我不想跳了!”吴皎洁听了张野的话,默默无语,眼角里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一串串地淌了下来。
分别的时候,吴皎洁一句道别的话儿也没说,打着雨伞孤独地向一边走去。雨雪完全变成了雪粒子,在劲风的狂吹下,无情地向人们扫去。吴皎洁的伞被刮得歪歪斜斜,脖子上的一条花丝巾也被吹落到远处的地上,可她像没有感觉到一样,晃晃悠悠地继续往前走去。
张野调转了自行车把,想把花丝巾给她拾起来送过去,但想了想,没往前走。
张野一个多月再也没有去跳舞。可是交谊舞的诱惑却不让张野的心里安生,人一旦有了舞癖,就像抽上了海洛因,要想戒掉非常难的。张野又到了明星歌舞厅,刚坐了一会儿,李莉迎上来,相邀跳舞,两个人手握着手,搂着腰按着肩,李莉捏了一下张野的手说:
“张先生,怎么好久没来了,和你在一起,我的舞跳得特别顺。你平常都在哪儿跳,能不能给我个电话号码?”
“我平常没时间跳,家里也没安电话。”
“没……电话,”李莉有点不大相信,“我告诉你我的电话号码。”李莉说了一个七位数。
张野摇了摇头:“我的记性不好,电话号码又难记。”
“一会儿,我给你写一下……”
两个人正在跳着舞说着话,突然,吴皎洁怒气冲冲地来到了张野面前,恨恨地说:“你还不走!我找你有事。”
张野大吃一惊,她是从哪里钻出来的,打乱别人的跳舞,确实不是舞场的规矩。好多人都往这里看,弄得张野有些下不了台。张野看了一眼李莉对吴皎洁说:“跳完这个舞,就走。”
“你不走,我可走了。”吴皎洁转身就走。
李莉推了一把张野,小声说:“快和她跳去吧!你朋友吃醋了。”
张野感激地看了李莉一眼,几步撵上了吴皎洁,拉住了她,和她一块儿跳起了舞。
紧接着是慢三步舞曲。三步舞把俩人组成了一条小船,在感情的大海里荡来荡去,一会儿抛上了感情的巅峰,一会儿又沉到了无底的深渊。吴皎洁觉得,丈夫的岸靠不上,以前的舞伴没靠上,张野的岸也靠不上,坚定执著地寻找了一辈子,一辈子也没有寻找到可以停泊的港湾。
女人为了寻找这个理想中的圣地,可以为他死,为他生,为他付出一切,而男人却没这么可靠,他们计较家庭、名利、种种的厉害关系……彩灯在旋转,天地在倒转,一切都是神鬼莫测。吴皎洁一边跳着舞,一边流着眼泪,泪水洇湿了胸前的一小片衣襟。
从这以后,张野在舞场里再也见不到了吴皎洁的身影。
十年后的一天,张野在舞场里突然见到了像是吴皎洁的一个老太太,满脸憔悴,头发花白,在默默地注视着自己优美的舞姿。张野十分吃惊,过去礼貌地邀她跳舞。那个女人说:“先生,我不会跳舞。早就不会跳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