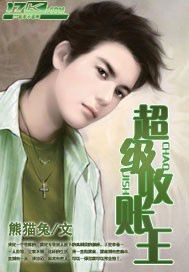这句话说完后,蚊子盯着我,看得我一阵发毛,让我怀疑我脸上是不是很难看。
看了一会儿,蚊子摇摇头:“屠哥,你受伤了,没伤到脑子吧?去蹲监狱?还是自愿的?”
我这才记起来,当时和犯罪调查科的黄建兴——黄科长谈的时候,蚊子他们几个都在外面忙,没进来,不知道这事儿。
我笑了笑:“还记得那天来的三个警察吗?我和他们说好了,事情一完,他们安排,我进监狱。”
蚊子眼睛瞪得老大:“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吗?他不会还找你那些毒品的麻烦吧?”
我摇摇头:“不是这个,为了保险起见,我自愿的。你想一想,这次所有相关的人都遭到了或大或小的损失,就我一个好好的,没人怀疑这其中是我做的手脚?所以,我进监狱,就是给他们一个讯号——我也是受害者。这么一来,估计就没人能怀疑到我们身上了……”
说到这儿,左肩在座位上蹭了下,我倒吸一口凉气。
蚊子点点头,看着我的左肩:“你的肩膀怎么了?刀伤?”
我小心翼翼地转了个方向,把左肩翘在空气中:“不是,枪伤……朱立明有枪……”
三炮和蚊子都震惊了,连前面开车的墨镜,好像也有一丝波动,方向盘打歪了下,不过他马上调整过来了,依旧一副酷酷的样子。不过我知道,他一直在很认真地听着,思考着,为我担心着。
心里一股暖流流过,这三个兄弟,值了!
我把所有的情况讲明白了:“朱立明没死,就在我要结果他的时候,他拿出一把手枪开枪了。我没事,贯穿伤,不打紧。”
“朱立明没死?”蚊子已经快要崩溃了,这一晚上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太多了。
三炮眼睛瞪得铜铃大小,大张着嘴,口水不知不觉中流出来了,吊在嘴边,震荡来震荡去……“
不过,就算他不死,估计也废了。这个不用我们担心,我们只是给他一个教训而已,现在已经达到效果了,不是吗?”
蚊子点点头:“这些都不重要,屠哥,枪伤还是赶紧去医院处理的好,不然发炎了就麻烦了!”
我擦擦额头上的冷汗:“不用了,没时间了,我现在直接联系黄科长,你们记住,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公司的生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安定!不要和外面的人,尤其是道上的,起冲突,能忍则忍,不能忍,把牙给我咽下肚子忍!”
蚊子默然,和三炮一起点点头。“不是说不让你们有表现的机会,现在田叔在外面,我马上也不在了,外面可能有人会打公司的注意,另外,强家辉也是公司的人,朱雀的人少不了会来找麻烦,所以一定要忍住。我们不反抗,他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强家辉这么做,又不是公司指使的。估计他们气出了,也就没事了。还有,我在里面的这段时间,你们三个要看好田蓓蓓!别让她一天到晚乱跑!还有,我进去这件事,别跟她讲……”
蚊子再次点头,抠鼻屎……
三炮结结巴巴地:“屠……哥,那你……进去多……多长……时间?”
我叹口气:“这个说不来,就要看什么时候事情有转机了,或者田叔来了,他会想办法弄我出去。你们别担心,大家要做的,就在在公司协助叶姐把公司打理好,下班了,给我看好田蓓蓓,别让她惹事,这样就行了!放心,虽然出了点差错,不过一切都在预料内。这次行动,我们赚到了,说不定唐阳,会因为我们几个无意识的举动,大变天!”
说到这儿,我看到了三炮和蚊子眼睛里跳动的火焰,那种感觉,很熟悉,也很亲切。都是年轻人,谁不想有一些作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掏出手机,我拨通了黄科长的电话,接电话的那头是个女的,听声音应该很年轻:“喂?您找谁?”
我汗了一个,我在这儿拼命呢,黄科长估计都醉死在美人乡了!
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老黄谈,
那个女人,恩,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你等等,我去叫人。”
然后对面就听不见声音了,应该不是去叫人了,而是捂住了电话筒。黄科长很可能也在边上,只不过不知道是我。
很快,黄科长充满睡意的声音传过来:“喂?你是?”
我没时间兜圈子:“黄大哥,我是屠亮亮!”
对面的人愣了下,声音马上热情起来:“原来是屠老弟啊,怎么样,事情成功了?”
能听到我的声音,估计就差不了了,所以他声音里从里到外都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我笑了笑:“出了点偏差,不过问题不大,见面细说。黄哥啊,你先把我送进去吧,不然拖到明天就不方便了……”
黄科长听说事情成功了,他也算是没暴露,不用担心朱雀的问题了,声音立马高了一个八度:“行!兄弟你在哪儿,我马上过来接你!咱哥俩见面了细谈!”
我看看外面,已经快到公司了,墨镜一直把车往公司开。
我答道:“就来公司吧,我在办公室等你。”
黄科长寒暄了一番,满心欢喜地挂断电话。
车停在了公司门口,蚊子和三炮两个一人一边,把我搀扶了进去。墨镜关掉引擎,锁上车,走在前面。
上楼,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我才轻轻松松地舒了口气。
我忍着痛,让蚊子一层一层地把左肩的临时绷带解开,露出了伤口——一片翻起的皮肉中间,是一个黑魆魆的洞,这就是子弹打穿的地方,边上的肉已经变成了炭黑色,血还是像小溪一样汩汩流出,不过小多了。胳膊上全是干了的和没干的血渍,散发着原始的、屠戮的腥味。
蚊子还好,估计是长时间咀嚼鼻屎具有的免疫力吧,还在很镇定地看。三炮已经不行了,想转过头去,却又怕我对他有意见,脖子就那么拧着,我都难受。
不过让我有些意外的是,墨镜好像对这么恶心的伤口,不是特别感冒,还是老样子,一言不发,看着我的伤口,黑乎乎的墨镜遮住了他的视线,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未完待续)